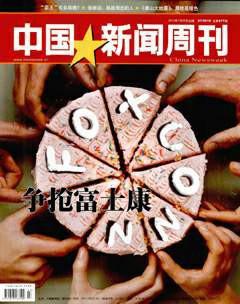在美國“孟母三遷”
薛 涌
如今中國的“小升初”,和高考一樣成為最重要的教育話題。孩子們在考場拼得精疲力盡,家長們叫苦不迭。我在美國長大的女兒剛剛過了11歲生日,今年正好也是“小升初”。看看她的經歷,頗有些幸運的感覺。這里不妨把她的“美國經驗”分片段寫出來,意圖不在于強加給中國一個“照搬”的范本,而是為當下的教育改革盡可能提供多元的參照系統,以擴寬公眾的思路。
中國“小升初”的一個關鍵在于“擇校”。上了好的中學,離名牌大學就近了。在美國的公立學校體系中,一般沒有“擇校”之必要。每個學區的居民,都可以把孩子送到本學區的學校就讀,不需要考試。哪怕你租間小屋住在這里,孩子就自動獲得了入學資格。學區的單位,一般是鎮,大都市則在內部分成若干學區。你無論買房還是租房,都可以事先問明孩子是屬于哪個學區。
但是,這種表面上的一視同仁,并無法掩蓋教育的不公平。“擇校”往往還是必要的。美國公立學校的主要財政來源是本地的房地產稅。學校的質量難免和房價掛鉤。比如,波士頓周圍幾個富鎮,平均房價超過百萬美元。百萬價值的住房,每年房地產稅至少一萬多美元。美國的中小學教育費用,平均一個孩子大致在一萬美元左右。如果某鎮平均一個家庭不到一個孩子,平均房價又在百萬以上,那么一家的房地產稅就遠超過一家不到一個孩子的教育經費。相反,如果鎮里平均房價僅二十萬,其他因素不變,那么一家支付的房地產稅僅為兩千多塊,對政府來說這筆錢怎么支付一個孩子一萬元的教育費用?盡管學校還有其他財政來源,房價還是最大的決定性因素。所以,波士頓周圍地區幾個最好的學區,大多集中在房價最高的地區。
那么,像我們這等買不起百萬豪宅的普通百姓怎么辦?最佳的戰略是在富鎮里買便宜房子。俗話說“皇帝還有幾門窮親戚”呢。如果你在百萬豪宅之間買下一棟寒酸的住宅,花了四十幾萬,你一年僅交不足五千的房地產稅,這筆稅金也遠遠不抵一個孩子的教育費用。而如果你有兩個孩子的話,這不足五千的稅金就更微不足道了。你的孩子靠著周圍的百萬豪宅所支付的高額稅金享受一流的教育,實在是一本萬利。當然,有些富裕的鎮,則采取了對付這種“搭便車”戰略的政策,制定嚴格的區域規劃法,比如每棟房子占用的地皮至少一英畝(將近一個足球場那么大)。這么大的地,自然價錢高。如果地價三十萬以上,房子的造價至少也要三十萬,這樣房價最低也要六十萬了。這無疑鼓勵開發商造大房子,抑制廉價住房的發展。你如果太窮,這些富鎮很難擠得進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波士頓郊區的幾個頂尖學區,除了極少的例外,三十幾萬的房子還是有一些,甚至不時有二十幾萬的。如果三口之家肯擠在六七十平方米的公寓中,十幾萬的也有。再不行還可以租房呢。
我們一開始就選擇了這樣的戰略。2004年搬到波士頓地區,女兒才五歲,開始上幼兒園,我們選擇了一個中上等學區。我們的哲學是,在幼兒園和小學,孩子的快樂是首位,家庭影響也比較大,學校差不多即可,所以我們不太挑剔。但是,中學以后競爭激烈,功課也難了。老師是否稱職,對孩子學業影響太大。另外,孩子長大成人,會面臨著毒品、性等等問題,環境好壞日益重要。于是,我們準備好積蓄,為“小升初”關頭的“擇校”做準備。
我為此列出了十幾個首選的鎮,按照學區排名、房價水平等等指標綜合打分,哪里劃算就去哪里,最后在2009年趁著房市猛跌到一個富鎮“兜底”,搬進一棟相對便宜的房子,女兒由此進了麻省一個頂尖學區。我們翻閱鎮上的財政文件,發現她的班主任一年年薪達八萬美元,幾乎是一般中小學教師的一倍。用我們家庭的房地產稅,肯定是雇不起這么昂貴的教師的。這大概也說明我們戰略對頭吧。女兒在新環境中讀小學五年級,有了一年的適應時間,今年“小升初”無論是從心理上還是學業上都順利多了。
我無意把美國的制度理想化。事實上,當今美國教育的許多問題,都是上述描述的體制所帶來的,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富不公:窮人面臨房價門檻,很難擠進好的學區。但是,對于一般的中產階級來說,在這種制度中的選擇要多得多。在這種制度下“擇校”,如同“孟母三遷”,責任在家長那里,孩子本身沒有特別的負擔。最重要的是,這種制度保存了一個基本的原則:教育的選擇權掌握在家長手里,不在學校手里。學校必須對本地區的孩子一視同仁地提供教育,沒有“招生”一說。在我看來,中國的義務教育改革的細節可以有許多討論的空間,但基本原則必須堅持,即學校無“招生”的權力,孩子有就近上學的權利。否則,“小升初”的惡性競爭永遠無法杜絕。★
(作者為美國薩福克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