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起點上認識西方
○漢 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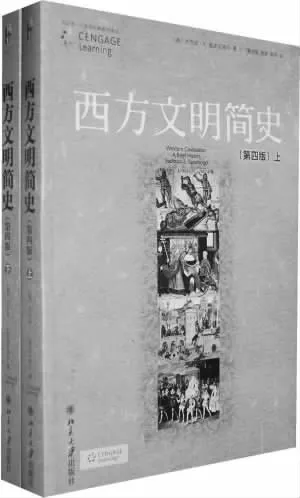
《西方文明簡史》(上下冊)(第四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109.00元
經歷過后現代歷史理論橫掃史壇之后,書寫一部篇幅不大卻能令讀者比較信服、樂于接受的西方文明通史著作,對于當代史學家來說,意味著更大挑戰。首先,歷史事實的甄別與挑選必須更加嚴格,必須堅定地傳達出某些確鑿無疑的歷史現象(人物、事件、歷史變化等)和某些無可否認的歷史見解,否則便會給人以“沒有歷史客觀性”的印象。其次,在結構安排上必須呈現完整的體系和清晰的歷史主線,又不失去主干之外的無限多樣的豐富性,既保證“宏大敘事”,又必須展示紛繁多樣的歷史“碎片”,開掘相當的思想深度。講述的歷史不僅僅有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還必須同時囊括社會史、文化史、科技史。它不僅僅是上層、白人、男子、成功者的歷史,它還應當包含有色人種、女性、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史。再者,在撰寫方式上,歷史“文本”必須滿足敘事內容生動、引人入勝的標準,或者至少包括開端-經過-結局這樣的情節變化,“文本”的歷史再現形式也絕不能單一:流暢的歷史敘事、清晰明確的歷史時空坐標,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肖像、鮮活真實的歷史插圖以及歷史參與者發出的不同“聲音”等等都應盡可能呈現在讀者面前。
杰克遜·斯皮瓦格爾的《西方文明簡史》一書正是應對上述新挑戰的大膽嘗試,作者以專業史學家特有的嚴謹,輔之以深入淺出的表述、生動活潑的語言,通過內容完整、邏輯連貫、分配均衡的歷史敘事,向讀者展現了一幅豐姿多彩的畫卷。歷史敘事之“事”涵蓋寬廣,“敘”之策略靈活多樣,充分體現出史學家深厚的修養和技藝。從《十二銅表法》、《大憲章》、《帝國法令》以及《解放黑人奴隸宣言》之類官方文獻檔案,到馬克·吐溫的小說、愛倫坡的浪漫主義文學作品和撒切爾夫人傳記中的點滴記錄,告訴人們,歷史是人們曾經經歷過的真實不妄的存在,真實的歷史是不容抹殺、無法否定的。這本書不僅從女性史、全球史、環境史等多種新視角出現,重新發掘歷史的新面相;其呈現歷史的“文本”形式也不一而足:文字敘述、圖片顯示、年代記、文獻記錄、地圖標示等,既為同一事件的發生和作者的解說提供多方佐證,也為讀者全方位多層次地透視同一事件提供了便利。該書成為常春藤名校的經典教科書也就不難理解了。
一部西方的歷史就是西方社會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也是西方各族人民生產生活勞動不斷發展變化向前推進的歷史。面對特定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西方各個民族在自己的生產生活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崇尚競爭、自由的價值觀念和文化特色,這使得它迥然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同時也是它率先完成現代社會轉型的原因之一。無疑,西方文明在近代以來在推動人類文明的整體進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西方文明的進步不是線性的,西方文明的“復調”中不僅有進步、自由的旋律,也夾雜著對于人的自由和理性的可怕否定:種族主義、世界大戰、極權主義等等。20世紀以來,西方文明屢屢陷入危機,雖然以往的經驗顯示,每一次危機之后它總還能獲得不同程度的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西方文明的未來總是“樂觀的”,至少當下西方文明的命運堪憂:是面臨一個更公正的世界新秩序獲得更好的發展,抑或墮入一個恐怖主義時代的無盡深淵?作者未下斷言,其隱忍之語是,這取決于身處十字路口西方的選擇。
一部西方的歷史也是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碰撞、融合、交匯的歷史。斯皮瓦格爾筆下的西方歷史構圖就表現為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互相影響的人類文明交互網絡。無論是文明的起源還是近代的崛興,西方世界都離不開東方文明的滋養和灌溉,把西方文明視為人類文明一直的中心的觀點注定是站不住腳的。但批判“西方中心論”也當謹防錯誤地否定歐美在世界史中的特殊作用。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看來,那種做法只是枉然。“歐洲中心論”和“歐洲歷史的作用”是當有區別的。如同西方有過后進變先進的崛興一樣,當代西方的危機似乎暗示其未來由先進變落后的趨勢,但絕不可低估西方文明學習借鑒其他文明之上自我修正、自我揚棄的能力。后9.11時代以來,“全球問題”不斷涌現,非西方文明對于西方文明發展方向的影響作用漸增,這在作者屢次修訂不斷添加的史實中都可洞見。
鑒于西方部分學者近年來對于“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幾近逢迎式的夸耀,鑒于當初曾經欺侮中國的國家正陸續被中國“趕超”,曾經作為重要學習和借鑒對象的某些西方國家深陷危機如今卻要靠中國施以援手,當此之時,國人是否還能保持寬廣的胸懷和清醒的頭腦去了解西方,是否還要閱讀它們的歷史?回答是肯定的。“在一個危機重重、混亂不堪的時代里,理解西方的遺產及其教訓可以幫助我們為未來創造新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文明簡史》正好充當新時期學習西方歷史的絕佳入門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