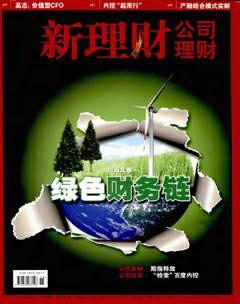股神的捐贈
縹 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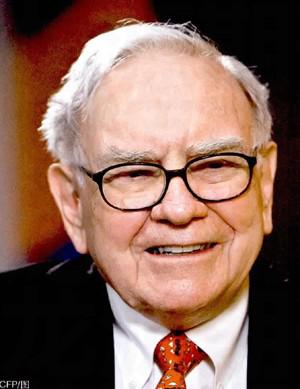
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日。當天各大報刊的頭條新聞是:股票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先生宣布,他于7月1日再次向5家慈善機構捐贈股票,依當前市值計算相當于19.3億美元。
相關報道稱,SEC(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于7月2日收到的備案文件顯示,巴菲特所捐贈的是他旗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特別股(B類)股票2454萬股。不過,在完成本年度的捐贈后,“股神”巴菲特依然持有不少哈撒韋公司的股票,從數量上看相當于其流通股總數的23.3%,市值大約為439億美元。
財富與公平
以《美利堅三部曲》(《美國的民主歷程》、《美國人殖民地歷程》及《美國人》)而聞名的丹尼爾?布魯斯汀,曾經總結了美國前三代富人階層的產生與衰落。
現代美國首先是商業的世界:第一代富人是所謂的壟斷型大資本家,比如洛克菲勒、安德魯?卡內基和J?P?摩根等,他們從19世紀中后期出發,在一片荒原上建造了現代意義上的商業帝國,創造了大眾市場,并使美國的生產力量超過了英國。
第二代富人的代表是消費型產業主,比如汽車業巨子亨利?福特、IBM創始人托馬斯?沃森、通用汽車的管理者阿爾弗雷德?斯隆、時代出版公司創辦人亨利?盧斯等,這一代商業領袖在前人的基礎上,使公司的資產完全資本化,并隨著美國逐漸演變成世界第一強國與單極世界的全過程,締造了“美元的世紀”。
第三代富人則以英特爾的創造者羅伯特?諾伊斯、IBM第二代繼承人小托馬斯?沃森、花旗銀行的精神領袖沃爾特?瑞斯頓、《紐約時報》的發行人阿瑟?蘇茲伯格等人為代表,他們不但繼續著前人的“夢想”,更將美國帶入到了當前的信息時代。
相比之下,以比爾?蓋茨、邁克?戴爾、沃倫?巴菲特等“世界級富豪”為代表的第四代商業精英,則大多出身于平民。然而,這并沒有阻礙他們去創造并推動新的經濟力量,從而使全球財富迅速增值,更沒有阻礙其個人的財力與權力達到前人所無法想象的高度。
第四代富人的經歷告訴我們,如果窮人不能改變自己的人生,或者人的尊貴僅僅取決于其不可選擇的血統,那么,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擁有“公平”。改革的正義在于,它必須能夠改進窮人的處境,讓窮人有機會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
“財產收入”與“權利收入”
前不久,曾有學者給眼下呼聲甚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潑了一盆冷水-他說:“目前還找不到數據”能夠得出某種“城鄉差距擴大或縮小”的結論;也沒有數據表明,中國收入分配狀況正在“繼續惡化”之中。
而事實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沒有“公平的起點”所造成的貧富差踞,已經達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程度。據統計,當今排名“前100”的中國富豪的資產,已經相當于8億個中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而排名前100萬的富豪的資產,已經超過GDP的80%。
就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而言,占國民經濟主體的大型國有企業,已經對強勢壟斷形成了嚴重的“依賴”。在政府主導的模式中,尤其是在大型國有企業的壟斷式經營過程中,已經形成了“發展”模式之下的“尋租”體系,且這一體系有著超級穩定的基礎,于是,一個全國性的、由上而下的、從東到西的收入階梯便形成了。正所謂“靠近權力部門,收入則高,高了還能再高,直到九天之上;遠離權力部門,收入則低,低了還能再低,直到九地之下” 。
眾所周知,社會分配并非只有物質所得。僅以物質所得而言,至少也應包括資本所得、資源效率所得以及生產資料所得等三個剩余部分。
而在我國當前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無所不在的政府調控,始終將政府稅賦收入維持在越來越高的占比及增率之下(當前個別行業的高利潤,無一不是源于該行業的壟斷利潤,或政府的權利轉移),根據歷年國民經濟核算統計,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代表勞動者所得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50%以上,2001年后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
當權利成為財產
有關收入分配的討論,在理論上,我只想問一個相當原始的問題:什么是財產?
在農業社會,財產必須是有形體的,可見的,可測的。
在商業社會,財產必須是有穩定的價格的,并且可以用于交換其它財產的,無論有形或者無形。
在資本社會,財產必須得到政府的特許,受到法律的保護。大量的政府產品流入商品市場,財產徹底無形化了。
在眼下,全球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就業、言論自由、養老金、原始股權、政府特許牌照,成為新的有形的財產;在此階段,新財產(new property,弗里德曼定義)出現了,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權利成為財產!
權利,是分配資源的主要工具,但它卻是體制的產品。所以,無論其合理甚或不合理,其后必定需要暴烈的力量,給予其有力的保障。當然,有形的財產,更易被公眾所認知。慘的是那些“不動聲色”但卻始終“存在”的“權利之手”,比如匯率與利率,比如繁榮過后的滯脹。
今天,當我們力求回歸問題的本原時,絕不能僅僅局限在教科書上那些陳舊的概念,而應當關注“新財產”;如果我們不解構財產的來源,僅僅在口頭上提倡對于國民收入分配的個別結構進行改革,又如何能解決社會分配體制的公平?
無疑,“權利成為財產”才是人類社會無法達到共富的主要障礙,因為在權利面前,任何沒有防衛手段的財產,包括不動產,都已不再是財產。
還富于民
最后,讓我們再次回到卡內基和巴菲特。
1900年,卡內基65歲時,他將全部資產賣給了摩根家族,退出了企業經營。他說:“對金錢執迷的人,是品格卑賤的人。如果將來我能夠獲得某種程度的財富,就要把它用在社會福利上面??在財富中死去,是人生的最大恥辱。”
此后20年,他用這筆錢,逐漸回饋社會。今天的人們知道,是他捐資創立了價值不菲的、面向公眾全面開放的藝術中心、圖書館、音樂廳、大學,以及慈善基金會。后人評價他說:“他以一已之力,最終完成了這難以想象的一切。”
巴菲特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巴菲特個人所捐股票市值分別為21.3億美元、21.7億美元和15.1億美元。而且,他呼吁《福布斯》上的富豪們,至少捐出個人財產的一半,以增進社會的公平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