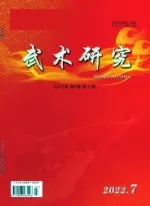試論洋務運動時期的武術
——兼論武術在工業近代化中的境遇
龍行年
(武漢體育學院武術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試論洋務運動時期的武術
——兼論武術在工業近代化中的境遇
龍行年
(武漢體育學院武術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列強入侵粉碎了中華天朝的神話,武術在現代戰爭中的失利使洋務派重視洋槍洋炮。洋務派對傳統武術的再認識為傳統武術的存在與發展創造了契機。習武者把傳統武術中的道德文化帶進了早期的軍事工業,與傳統行會中的師徒關系結合起來,形成了中國近代工業中特有的道德文化。
武術 洋務運動 近代化 調適
傳統武術指中華民族自己創造的并吸收其他民族及外國有關內容而逐漸演化而來的武術。內容應包括兵刃、射箭、摔跤、氣功、各類拳術。從用途上劃分,應分為軍事武術、健身武術、娛樂武術。后兩項分類則是以軍事武術為基礎的。根據明代戚繼光的《紀效新書》記載,軍事武術在現代武器未進入中國前,曾在軍隊訓練和作戰中發揮極大的作用。
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英法以堅船利炮粉碎了中華天朝的迷夢。“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的思想上就有一個從重視傳統武術的軍事作用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轉變過程。從《林文忠公政書》查知,林則徐在1837年春任湖廣總督時,從4月到9月“閱過湖北十五標營,湖南卅二標營及道標各屯員弁兵勇,……長矛刀棍多有可觀”。后來又在廣東、云南任上還多次考閱官兵“刀矛雜技、擊刺跳舞”。從以上事實可看出鴉片戰爭前的林則徐是提倡軍備、注重軍事的督撫大員。另外也看得出來林則徐對傳統武術在軍事中的作用非常重視。但在鴉片戰爭后,林則徐已認識到“我不及人者器械也”,從而開始否定傳統武術在軍事上的作用。并完全贊同“師夷長技以制夷”即學習西方技術來制服西方。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八里橋一戰,僧格林沁率領的蒙古銳騎以其不畏死的精神讓英法聯軍震撼。但也徹底的宣告了裝備劣勢的軍隊在先進技術裝備的軍隊面前是難以取得勝利的。這為林則徐的見解作了一個悲壯的注解——師夷長技才能制夷。因此在一段時間朝野之內對傳統武術在軍事上的運用做了徹底的否定。有趣的是,對傳統武術在軍事上的運用否定得最徹底的洋務派,又在否定中重新承認傳統武術的軍事價值。
1 傳統武術在早期軍事工業中的作用
同治三年(1864年),曾國藩在南京尚未攻下時已在籌措安慶軍械所,委派楊國棟負責,派容閎到外洋采購機械。用人不疑,曾國藩對兩人掌管的事務從不過問,唯獨對楊國棟作了這樣的指示:“技師、工匠爾所帶回者當任之以信,唯在當地所聘之人,身世當清白,當有擔保。然若有習技擊者當當面驗之,不可輕忽。”[1]曾國藩在這里不光同意了招募習技擊者,而且要求重視這些人。楊國棟在招募了這些人后,除安排這些人參加生產外,并逐漸讓其中某些人擔任了維持紀律、執行保衛的工作[2]。這就開了習武者進軍事工業的先河。李鴻章在觀看安慶軍械所時看到了習武者在現代軍事工業企業中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在創辦江南制造總局時也加以仿效。創建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又在曾、李的基礎上,把軍隊制度、安慶軍械所形成的師徒制度、江南制造總局的頭佬制度和福建當地的地域家族關系捆綁在一起,形成獨有的企業制度。在湖北創辦漢陽鐵廠的張之洞也有所增益地利用了曾、李、左形成的制度。而且張之洞在1906年建立武普通中學堂規定:“一般課程大體同于文普通,軍事科目則有典、范、令和操練、技擊、馬術、射擊等。”[3]傳統武術被張之洞推進了現代教育的課堂中。
以上所列舉的史實足以表明洋務派并不是對傳統武術進行排斥,而是經重新認識后對傳統武術加以使用。
是什么使洋務派對武術重視起來的呢?
筆者認為有這樣幾點原因:(1)傳統武術在軍事上的作用雖因西洋武器的進入有所削弱,但依然在軍事上有特殊的作用存在,這是曾氏兄弟在實際的軍事斗爭中認識到的;(2)曾氏兄弟認識到傳統武術的道德并沒有違背其堅持的封建道德,只要稍加引導就可以更好地維護封建道德;(3)習武者個人所表現的素質也成為洋務派重視傳統武術的原因。
傳統武術進入現代軍事工業企業中后短期表現為維持紀律、執行保衛,但從較長的時間角度來觀察其作用不容輕視。
其一,習武者把傳統武術的師徒傳承關系帶進早期的軍事工業企業,與傳統行會中的師徒關系結合起來,形成了中國早期現代工業中特有的道德規范。直到新中國建立后這種師徒關系還有所表現。盡管有所改變,但“師徒如父子”這種傳統說法一直存在。
其二,江南制造總局地處上海,當地江淮漕幫一向以青幫形式存在。當習武者進入現代軍事企業后,傳統武術道德中的師道和義氣作為基礎,通過青幫香堂的傳承模式,形成了頭佬這一不被官方承認,但被官方利用且行之有效的制度。
其三,傳統武術中的道德通過習武者進入現代軍事工業企業,為有識之士改造后與儒學相結合形成了中下層社會的道德主流規范。例如,武術家經常強調的寬厚,常用“攆人不上百步”來形容。現在,在實際生活中還經常被用來作給別人留一點余地的勸告語言。
其四,傳統武術中的幫派在進入現代軍事工業企業后,義氣就成為門派不同的人互相溝通的道德準則。嚴格地說,義氣屬于流氓無產者特有的一種道德規范,但進入企業之后演變成互助、互濟的品德,有利于工人之間的團結。
其五,早期洋務企業中的幾次工人罷工(進行是經濟斗爭),其領導者、組織者、中堅力量大多數是練武者。甚至二七大罷工的主要領導之一,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及其弟林元成也是習武者。林祥謙,福建閩侯人,1892年生。貧農家庭的艱苦生活,形成了他勇敢倔強、吃苦耐勞的性格。13歲時他一人敢與3個偷吃他家龍眼的財主仔搏斗,14歲進馬尾造船廠當徒工。[4]1912年,到漢口京漢鐵路江岸機廠當工人。馬尾造船廠為左宗棠創立,該廠所實行的在曾、李的基礎上把軍隊制度、安慶軍械所形成的師徒制度、江南制造總局的頭佬制度和福建當地的地域家族關系捆綁在一起的獨有的企業制度,其中就有傳統武術的道德因素在內。由于林祥謙是習武者,傳統武術的道德觀念很強,因而為人很講義氣,“樂于助人,同鄉有困難他以家中僅有的十幾斤米相送,福建籍工人擁護他,推舉他為福建幫首領之一。”[5]后來林祥謙正是由于得到工人擁護,又能以義氣消除湖北幫和福建幫工人的隔閡,才成為江岸分會委員長。
為什么從早期工人經濟斗爭一直到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的工人罷工中,能充當領導者和中堅力量的以習武者居多呢?這與習武者在習武中接受的道德教育和養成的個人素質有關。習武者大多具有見義勇為、打抱不平的個性特征。
當然這些作用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應該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進行認識。
2 傳統武術能在早期的現代軍事工業中站住腳的原因
北宋一代開重文輕武之風氣,明清兩代把這種風氣推行到極致。所以在清代才會發生左宗棠敢以舉人之身份辱罵總兵的故事,武術的社會地位低下也可以從這件事中看出。本來社會地位就低下的武術由于在軍事中作用的下降,更加被人輕視。武術為什么沒有消亡,武術為什么能進入洋務派所興辦的企業,武術文化為什么能融進主流文化,傳統武術靠什么在現代企業中站住腳?這些問題實際上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傳統武術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傳統,經過一段調適過程,它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因而也為自身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條件。
傳統武術從源而言是古代勞動生產、狩獵等活動中具有防衛性和攻擊性動作的結合,從流而言則有發展之流和吸收學習之流。發展之流是指這些動作在發展過程中被習武者按不同的取舍標準進行新的編排,并研究出使這些編排更符合人的肌體運動能力。吸收之流則是指在發展過程中通過對自然的模仿,對不同民族類似動作的吸收改造。從源流來看,傳統武術自始至終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關。因此,與社會生活緊密的相關性使傳統武術在接受社會道德時又以社會道德為基礎,形成了獨特的武術道德。以戰國時期為例,三國分晉時的豫讓刺殺趙簡子,豫讓就表現出“人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人”[6]的道德觀念。在這之后刺殺韓隗的聶政則說出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樂己者容”[7]的道德箴言,并且為了不連累其姊,毀容而掩其名。這是習武之士把獻身與全家這兩種儒家道德的結合。而聶政的姐姐冒生命危險認弟,則表明在習武家庭已出現了道德標準共有。至漢代,劇孟、郭解等俠士則以睦鄰鄉里、急公好義作為道德標準。[8]發展至大詩人李白從小就學習劍術,而且從道家中的自然放任、曠達瀟灑的角度對習武者進行了這樣的贊揚,“千里不留行,十步殺一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9]這里傳統武術的道德除急公好義、急人之難外還上升到不求名利的崇高境界。明末清初的魏禧在《秦士傳》中記載了一位有一身好武藝卻報國無門的武士。他的道德標準已上升到“羞于私斗而勇于攻戰”。[10]從以上所列舉的例子可以看出傳統武術所蘊涵的道德一方面隨時代發展吸收同時期的主流道德,另一方面始終表現出武術道德的特性——不恃強凌弱。
正由于傳統武術具有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關和隨道德主流而進行道德調整的特點,所以傳統武術的根扎得太深、布得太寬,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就是傳統武術在近代遇到沖擊后,在社會地位極其低下的狀況下能自救的文化基礎。
傳統武術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吸收了儒、道、釋、陰陽家、醫等多方面的文化內涵。當然,其中也有一些迷信成分。因而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迄今為止,從傳統武術中發展而來的中國式按摩、跌打損傷的治療方法依然在西方醫學的擠壓下生存。這種不可替代性是傳統武術能自救的物質基礎。
傳統武術經千百年流傳,經無數代武術家和習武者的傳播,其普及性使傳統武術既能進入皇家,也能深入百姓。這種普及性是傳統武術能自救的群眾基礎。另外,傳統武術的軍事實用性則為傳統武術進入早期軍事工業企業創造了契機。利用這個契機,傳統武術用其不違背封建道德的道德規范及習武者獨特的組織紀律性(對師長的服從性發展為對上的服從性)打動了洋務派中的實力人物,從而在洋務企業中站住腳。之后傳統武術又通過其道德中講義氣、重承諾贏得了企業中一般工人的尊重。就這樣,傳統武術被現代化推進了現代企業,站住腳后又通過自身努力創造了存在和發展的條件。
3 傳統武術在現代軍工企業中的調適過程
有關洋務派所辦軍工企業的歷史資料多側重于創辦狀況、管理狀況、經營狀況及人事變動狀況,對習武者在現代軍事工業企業中的個人活動從未涉及。這就為研究者留下困難。筆者在查閱了大量洋務派所辦軍工企業的史料后,從其管理制度上得到了啟發。并據此對傳統武術在現代軍工企業的調適過程有以下見解:
其一,當時洋務派所辦軍工企業實行的管理制度是官本位制。封建等級制度在這些企業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如楊國棟在安慶軍械所時工匠、技師見了他都要行禮,“技師長揖,匠人打千”[11],與軍營并無二致。習武者對這一點應該可以接受,一來當時社會的禮節就是如此,二來習武者不少都從過軍。
其二,傳統武術歷來有門派之別,因而有門派之爭。習武者進入洋務派所辦軍工企業后,現代工業的協作意識和共同的經濟利益逐漸消融了這種門派意識。同時也消融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地域意識。加上軍工企業的軍事管理制度容不得門派之爭的存在,企業管理的統一規范使門派之爭不可能大規模在洋務企業出現。
其三,盡管洋務派在企業中采用的還是“以官管民”這一人治形式,但終究接受了一些西方工廠的管理經驗。這就形成了洋務企業中早期的規章制度。這些規章制度徹底地否定了傳統武術的作息時間表。例如,傳統武術原來是在自然經濟的條件下傳播,必須適應自然經濟的要求,因此有農閑時練得多,農忙時練得少,甚至不練。查看一下農村的拳房多活動于秋末至春初就可知道這個規律。另外習武者在自然經濟狀況下時間是由自己支配。進入企業后,必須適應企業的作息時間。這種作息時間上的改變從深層次而言實質上是對自然經濟狀況下個人活動自由的否定。進入洋務企業的習武者為生存只得順應這種變化。
其四,現代企業決不會容忍工人在企業中弄刀舞矛,因此習武者也必須由相應改變。這種改變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重拳腳而輕兵刃;二是把兵刃的用法融會進平時所使用的工具中,如漢陽鐵廠的工人(搬運工)在發生斗毆時就曾將搭布用水打濕后作甩棍使用;三是根據工廠的條件自己創造兵刃并創造新的使用方法。這一點在后來的上海第三次工人起義(1927年)表現得非常充分,工人將廢棄的齒輪當鏢使用。這種兵刃上的變化實質上是適應工廠制度并適應物質條件而產生的。
其五,現代企業對進入洋務企業習武者最大的改造應該是意識形態上的改變。傳統武術本身對于生產并無作用,因此,崇尚技術在工廠形成風氣。技術的高低又往往成為工資差異的原因。習武者在這一時期不得不從瞧不起技術到逼得自己學習技術。這一逼使習武者更為廣泛地融入社會性活動。“一招鮮,吃遍天”的武術格言被習武者轉用到學習技術上,而學習技術又使習武者擴大了眼界。
其六,習武者成為靠工資養家糊口的勞動者。對工資的看重迫使習武者努力捧牢飯碗。這就決定了習武者再不可能憑仗血氣之勇去打抱不平,而企業對工人的束縛也決定了習武者不可能再擁有以前那么廣闊的江湖天地。現代企業的道德、文化,在產生時已在改變企業習武者的道德文化,從而影響傳統武術的道德文化。
總之,“勞動產品的分配權決定了個人在企業的地位”,馬克思的這一論斷形象地說明了勞動者在企業的地位。習武者盡管學會傳統武術,但不擁有生產資料,因此只能根據自身的經濟地位來調整自己的活動、調整自己的思想。在這種調整中,傳統武術是出于弱勢地位,不調整就得丟掉飯碗。因此屬于被動的、非自覺的調整。經過了這一被動的、非自覺的調整之后,企業的道德文化逐漸與傳統武術文化互相調適。因而出現了主動的、自覺的調整。
不管是被動的、非自覺的調整還是主動的、自覺的調整,都意味著傳統武術并沒有被剛起步的現代化淘汰,這表明傳統武術的生命力,更表明傳統武術的生命力具有強大的適應性。
4 洋務派對傳統武術再認識留下的啟示
任何發展都不是單純的否定和肯定,而是黑格爾所說的否定之否定,即揚棄。洋務派對傳統武術的再認識就是這種揚棄過程的表現。
洋務派在中央的代表奕訴說過:“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12]奕訢所說的“練兵”指練習洋操的新軍,這就把傳統武術徹底排除在軍事應用之外。曾氏兄弟開始也有這種觀點。這一時期傳統武術本來就不高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在對太平天國作戰中曾氏兄弟從戰爭的實踐中即從太平天國將領對武術的重視中認識到傳統武術在近戰、接敵戰中的特殊作用,不能被洋槍所代替,同時認識到傳統武術的道德文化在社會群體組織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對原觀點進行了又一次否定。除了在軍事訓練中采用技擊訓練外,并且在洋務派所辦的軍工企業中改造和利用了傳統武術的道德文化。因此中國現代工業最早的企業文化應包括傳統武術道德。張之洞后來在興辦武普通學堂時也強調積極科目。證明了傳統武術不光自身經歷了一場蛻變,贏得了自身存在和發展的機遇,也證明了洋務派對武術的再認識的過程是一個提高的過程。
回溯這一時期傳統武術的歷史,我們可以得出:其一,傳統武術不單純是技擊或是體育活動,而是一個傳統文化的綜合體。其二,傳統武術的發展表現著傳統道德的發展。其三,洋務派對傳統武術的再認識為傳統武術的存在、發展創造了契機。其四,傳統武術的存在、發展是民族文化生命力強大的表現。其五,任何傳統的文化只有隨社會進步進行自我調適才能得到發展。
[1]李瀚章編纂.曾國藩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1741.
[2][11]安徽文史資料文庫編委會編.安徽文史資料文庫(第三卷)[M].合肥:安徽出版社,1999.
[3]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編[M].武漢文史資料文庫(第一卷)[M].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9.
[4][5]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文庫(第七卷)[M].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
[7]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
[8]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
[9]李 白.李太白全集·俠客行[M].北京:中華書局,1956.
[10]魏 禧.魏叔子集·秦士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4.
[12]谷世權.中國體育史[M].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83.
On Wushu i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Conditions of Wushu in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Long Xingnian
(Wushu Schoolof 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Hubei430079)
Powers invasion broke the myth of China paradise,function failure of Wushu in modern wars make westernization faction pay more attention on western guns and rifles.The reconsideration of westernization fact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created chances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Wushu.Wushu practitioners took moral culture into original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industry,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s of Master and prentice,formed the modern industrial morality.
Wushu west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adjustment
G85
A
1004—5643(2010)10—0003—03
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研究院院管課題,編號:WSH2010C020。
龍行年(196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傳統體育理論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