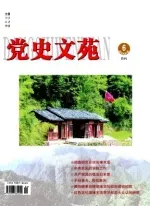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的知識產權
喬 磊
(東北大學 遼寧沈陽 110004)
知識產權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發展動力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關注并持續爭議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1]只有回到知識產權背后的物質生活中去,才能認清知識產權的本質及其歷史正當性。這種 “物質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因此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深入分析科技發展與知識產權的辯證關系,把握知識產權的發展動力及其在不同時期對科技進步的作用,有利于我們歷史地看待知識產權的社會功能,認識到知識產權僅僅是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在與科學技術的矛盾運動中發展、完善,乃至最終消滅。
一、科學技術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推動作用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科學技術是一種直接的生產力,科學技術的發展會通過勞動方式的變革把生產力的發展傳遞到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層面,從而影響和推動生產方式、政治、法律、意識形態乃至整個社會關系的變革,其中就包括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知識產權制度。馬克思曾指出:“工藝發達的研究,會把人類對于自然的能動關系,把人類生活的直接過程,由此也把人類社會生活關系的直接生產過程揭露出來。”[2]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作為直接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對作為上層建筑的知識產權制度具有直接的推動作用。這種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科學技術商品化催生知識產權制度
馬克思在論述私有財產制度的產生時曾指出:“私有財產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是獲得財產的新方式。”[3]“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起來的。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4]可見,作為具有私有財產權性質的知識產權制度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漸產生的。
學術界通說認為,英國于1623年制定的第一部專利法,1709年制定的第一部著作權法,法國于1857年制定第一部商標法是具有近代意義的知識產權制度的開端。這是當時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科技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不斷加強的必然結果。“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5]“生產過程成了科學的應用,而科學反過來成了生產過程中的因素即所謂職能。每一項發現都成了新的發明或生產方法的新的改進的基礎。”[6]專利權的產生源于技術的廣泛應用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客觀上需要推動技術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以鞏固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利益,需要以“懸賞”的方式來激發人們進行技術發明。著作權的產生源于印刷技術和造紙技術的發展。圖書印刷告別了手抄時代,大量翻印圖書成為可能,使圖書出版業成為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興行業,在利益的驅動下,更多人涉足印刷出版業,著作者與出版商的之間的利益矛盾日益凸顯。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議會1709年通過了第一部關于保護作者權利的法律—安娜法(StatuteofAnne)。第一次技術革命后,先進技術的運用使得大規模的技術產品的生產和分配成為可能,客觀上需要提供技術產品購買者可以鑒別不同制造者生產的同一類技術產品的標志,在這樣的技術背景下,商標法就進入了立法者的視野,法國于1857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關于商標保護的法律—關于工廠、制造場和作坊的法律,也標志著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完整建立。
(二)科學技術發展推動知識產權變革
“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7]這是馬克思關于法律制度的經典表述。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法律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結構不斷變化,知識產權制度也需要做出必要的調整和變革,以適應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從世界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史來看,十八世紀中葉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即兩次技術革命時期,是近代知識產權制度建立和健全的時期。但由于科學技術體系尚不完備,知識產權制度也尚處于初始階段,尚未體系化。自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迅猛發展,導致了新興的“知識工業”部門的產生和大量高技術含量的知識產品的涌現,使得世界范圍內的知識產權制度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各國立法者不斷探索對高新技術產品保護的法律途徑,傳統的知識產權制度面臨巨大的沖擊與挑戰。其中尤以網絡技術和基因技術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影響最大,網絡知識產權、基因技術專利等問題迅速成為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熱點問題。縱觀世界各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與知識產權制度可以發現,凡是科學技術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無一不是知識產權制度健全與完善的國家。這充分說明了科學技術發展對一國知識產權制度發展和完善的推動作用。
(三)科學技術社會化決定知識產權的消滅
馬克思從社會基本矛盾的辯證運動出發,有力的證明了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終將被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代替。而知識產權制度這種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形式,也終將隨著私有制社會的終結而歸于消滅。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歷史地位的評價可以看到,馬克思對包括知識產權制度在內的私有財產制度保持著科學的頌揚和理性的批判。知識產權制度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無疑對鼓勵科技創新、激發創造性勞動、提高社會生產力有著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從本質上講,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知識產權制度,雖然名義上的目的是為了鼓勵發明和創造,而實質上知識產權成為資本將創造性勞動整合進入生產過程的制度基礎,并逐漸淪為資本控制科學技術以獲取高額利潤的工具。因此知識產權既不具有制度上的永恒存在性,也不具有道德上的永恒合理性。在未來社會,生產資料歸全社會共有,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勞動不再是人謀生的手段,而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成為人們全面發展的途徑。那時,作為創造性勞動結果的“知識”的歸屬問題就將不再成為問題,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制度也將不會也沒有必要繼續存在。
二、知識產權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反作用
(一)知識產權對科技發展的促進作用
知識產權制度是科技與法律相結合的產物,它在實質上解決“知識”作為資源的歸屬問題,是一種激勵和調節的利益機制。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經濟時代同時也是一個知識產權的時代。知識經濟是以科學技術為第一生產要素的智力經濟。知識經濟發展的動力在于科技創新,而科技創新離不開產權制度創新。英國是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發源地,也是歐洲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由于英國較早建立了知識產權制度,大大推動了紡織、冶煉、采礦、機械加工、交通運輸等產業的迅猛發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其創造的財富超過了以往歷史年代的總和。英國實行專利制度后,專利數量呈現出一種幾何級數增長的態勢。在專利法剛剛頒布的1621年至1677年的56年間,英國的年均專利增量只有3.21;而到了1797年至1801年的3年間,年均專利增量達到了82.77。[8]其間技術發明熱潮日益高漲,這與專利制度密不可分。在英國之后,法國、荷蘭、德國、美國、日本等國也紛紛建立了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世界著名的德國西門子、美國貝爾、英國鄧祿普公司的創始人,都是得益于知識產權制度的發明家。可以說,如果沒有近代知識產權制度,近代兩次科技革命就不會掀起如此巨大的技術變革浪潮。
(二)知識產權對科技發展的阻礙作用
當一定時期的知識產權制度能夠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就能夠起到促進科技發展的作用。相反,如果一定時期的知識產權制度不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就會對科技的發展產生阻礙的作用,表現為知識產權制度落后于科技發展的需要和超越科技發展階段的要求兩個方面。從知識產權制度與科學技術的關系來看,知識產權制度的根本目的和內在要求是促進科技的發展,手段則是對特定的知識權利給予私有保護,以起到知識創造的激勵作用。因此,知識產權制度是徘徊在對科技發展的“激勵”和對科學技術的“壟斷”之間的一種制度。退一步(即知識產權制度落后于科技發展的需要)就會損害“激勵”,進一步(即知識產權制度超越科技發展階段的要求)就會走向“科技壟斷”。從第一個方面來看,經濟史家在論及為何中國在技術高度積累的條件下未能出現工業革命這一問題時,提出中國缺乏一個企業家階層。“在作為工來革命發生前提出的充分條件中,恰好被古代中國所遺漏掉的正是一種催生企業家階層的產權制度創新。”[9]無論這種回答是否全面,但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知識產權制度建設落后于科技發展的需要時,就會因損害“激勵”而對科技的發展形成阻礙。相反,如果知識產權制度建設超越了科技發展的需要和水平,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知識產權制度所要實現的公共利益,增加反競爭行為的可能性,從而加劇“科技壟斷”和知識產權濫用,不利于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阻礙科學技術的發展。
(三)知識產權對科學技術的控制作用
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既能通過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造福人類,同時也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消極后果。馬克思在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的作用時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徑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置疑的事實。”[10]在利用科學技術的進步作用的同時,避免其帶來的負面效應,就必須充分發揮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增強人們合理控制各種生產活動和消費活動的能力和手段;如果問題是由社會制度造成的,就需要變革和建構合理的社會制度來對科學技術加以控制,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知識產權制度。21世紀最偉大的、同時也是最飽受爭議的技術之一,就是基因技術。因此,許多國家都通過知識產權立法,規范基因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其中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界定基因專利保護范圍,包括基因方法、基因產品、轉基因動植物新品種、轉基因微生物以及脫離人體或通過技術方法獲得的基因本身;二是明確基因專利的排除領域,特別是克隆人的方法、對胚胎商業利用的方法以及基因序列的簡單發現等。[11]從而在利用基因技術為人類創造利益的同時,嚴格控制基因技術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
三、知識產權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及其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一)科學技術與知識產權制度是一個相互作用、相互促動的協調機制
在科技—知識產權協調機制當中,科技發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就深入分析了依賴科技的發展所進行的現代化大生產對現代社會的革命性改造作用。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把提高科技水平,發展現代生產力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而知識產權制度應當服從和服務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反過來,判斷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優劣,首要的標準應當是其能否能夠促進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二)知識產權制度建設必須適應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
一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在客觀上反映出這個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因此,應當根據我國不同的發展階段的不同發展需求,對知識產權制度做出選擇性建構。一方面,我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我們推動科技進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融入世界工業文明與制度文明的內在要求。尤其是我國現階段仍然存在法律與科技不相適應、不相協調的諸多問題,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等部門法仍然存在相對滯后的條款,沒有根據科技與社會的發展及時進行修改。另一方面,應當堅持知識產權領域的“漸進式”改革。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來看,在知識產權制度發展史上,發達國家都有一個從“選擇保護”到“全部保護”,從“弱保護”到“強保護”的過渡期。[12]而這個“過渡期”恰恰是發展中國家科技發展的溫床。因此,我們應當正確處理外部壓力與基本國情之間的矛盾,正確處理“保護”和“發展”之間的矛盾。
(三)應當正確處理知識產權制度的“私益性”與“公益性”的關系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知識產權制度經歷了從“公益性”到“私益性”的否定過程,未來還將完成從“私益性”到“公益性”的否定之否的過程。根據馬克思的劃分,人類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擁有人身強制的人對人的依賴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在物質條件不豐富情況下以追求物質利益為基本目的的人對物的依賴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人既不依賴于人,也不依賴于物的自由的全面發展的階段。而要達到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第三階段”,應當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二是人的素質極大提高。這就決定了作為人類走向全面自由的過渡性制度的知識產權制度,應當肩負起兩大任務:一是在現階段物質條件不豐富、社會以追求物質利益為基本目的的情況下,擔負起保障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建立促進知識創造的激勵機制的短期任務,即“私益性”任務;同時,也要擔負起促進知識和信息的傳播,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科技、文化進步,促進全體人民綜合素質提高任務,即“公益性”任務,并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發展,不斷動態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達到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統一。○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2]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48.
[3][4][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1—135、177、775.
[5][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6、12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70.
[8]金海軍.16—18世紀英國知識產權的歷史與功能:一種社會結構整體觀[A].劉春田.中國知識產權評論(第 1 卷)[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20.
[9]柳適等編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演講集[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1]吳漢東.科技、經濟、法律協調機制中的知識產權法[J].法學研究,2001,(6).
[12]吳漢東.知識產權制度運作:他國經驗分析與中國路徑探索[J].中國版權,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