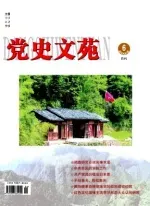羅坊會(huì)議若干史實(shí)新探
湯靜濤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江西南昌 330006)
羅坊會(huì)議若干史實(shí)新探
湯靜濤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江西南昌 330006)
羅坊會(huì)議是紅一方面軍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會(huì)議,它標(biāo)志著紅一方面軍由游擊戰(zhàn)向運(yùn)動(dòng)戰(zhàn)、由戰(zhàn)略進(jìn)攻向戰(zhàn)略退卻的傳大轉(zhuǎn)折。本文根據(jù)原始文獻(xiàn)和權(quán)威史料,擬對(duì)羅坊會(huì)議戰(zhàn)略決策作一簡(jiǎn)要回顧,對(duì)羅坊會(huì)議爭(zhēng)論問(wèn)題作一概括疏理并對(duì)羅坊會(huì)議爭(zhēng)議人物作些分析評(píng)述。
羅坊會(huì)議 戰(zhàn)略決策 重要人物 評(píng)價(jià)
一、科學(xué)地把握羅坊會(huì)議
從紅一方面軍撤圍長(zhǎng)沙到羅坊聯(lián)席會(huì)議,紅一方面軍經(jīng)過(guò)了袁州會(huì)議、峽江會(huì)議、太平圩會(huì)議、羅坊聯(lián)席會(huì)議以及其后的前委會(huì)議。在紅一方面軍內(nèi)部,逐步擺脫立三錯(cuò)誤的影響,逐步走向統(tǒng)一,把紅軍的行動(dòng)逐步轉(zhuǎn)向正確方面,完成紅一方面軍由游擊戰(zhàn)向運(yùn)動(dòng)戰(zhàn)、戰(zhàn)略進(jìn)攻向戰(zhàn)略退卻態(tài)勢(shì)的轉(zhuǎn)折,絕非一次羅坊會(huì)議就能一蹴而就。
袁州會(huì)議實(shí)現(xiàn)了最初的轉(zhuǎn)變。盡管撤圍了中心城市長(zhǎng)沙,紅一軍團(tuán)于1930年9月13日在株洲發(fā)布《攻取吉安的命令》,這是在反對(duì)立三錯(cuò)誤上邁出的有決定意義的第一步,但從整個(gè)戰(zhàn)略口號(hào)上來(lái)看,還是進(jìn)攻大城市,同黨中央提出的進(jìn)攻口號(hào)仍然是一致的。9月28日,當(dāng)紅一方面軍總部機(jī)關(guān)、部隊(duì)到達(dá)袁州(宜春)地區(qū)時(shí),紅一方面軍前委立即在這里召開(kāi)會(huì)議,就紅軍究竟是先打吉安還是先打南昌的問(wèn)題展開(kāi)討論。對(duì)于這個(gè)問(wèn)題,自撤圍長(zhǎng)沙以來(lái),雖然在株洲、萍鄉(xiāng)以一軍團(tuán)的名義下發(fā)了進(jìn)攻吉安的命令,但在紅一方面軍高級(jí)干部中并沒(méi)有統(tǒng)一認(rèn)識(shí)。袁州會(huì)議對(duì)此進(jìn)行了激烈爭(zhēng)論,有些干部還是反對(duì)先打吉安。他們的理由是:先打吉安后打南昌,就是不執(zhí)行中央的指示,就是斷送中國(guó)革命高潮。通過(guò)爭(zhēng)論,會(huì)議最后還是確定按原來(lái)的決定先打吉安,并以一軍團(tuán)的名義于9月29日下午發(fā)出“照原計(jì)劃擬于明(30)日由此地(宜春城)出動(dòng),經(jīng)分宜向吉安前進(jìn)”的命令。袁州會(huì)議,堅(jiān)持了攻打吉安的計(jì)劃,這是實(shí)際糾正立三錯(cuò)誤的一個(gè)重要成果,也是進(jìn)一步說(shuō)服教育干部擺脫“左”傾錯(cuò)誤的一個(gè)重要步驟。
峽江會(huì)議從思想更前進(jìn)一步。10月4日,紅軍攻占了吉安,紅一軍團(tuán)及紅一方面軍總部各機(jī)關(guān)在吉安工作了10天。雖然黨中央已經(jīng)在9月24日于上海召開(kāi)了六屆三中全會(huì),作出了紅軍停止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xiǎn)行動(dòng)的決定,但是,由于國(guó)民黨對(duì)根據(jù)地的封鎖和交通不便,三中全會(huì)精神并沒(méi)有傳達(dá)到紅軍中來(lái)。從10月13日的命令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出,紅軍的軍事行動(dòng)還是要進(jìn)攻中心城市。10月17日,紅一方面軍前委抵達(dá)峽江召開(kāi)全體會(huì)議。會(huì)上,毛澤東敏銳地指出了國(guó)內(nèi)形勢(shì)的變化,正確地判斷蔣介石要集中兵力對(duì)付紅軍。會(huì)議對(duì)時(shí)局問(wèn)題作出了階級(jí)矛盾超過(guò)統(tǒng)治階級(jí)內(nèi)部矛盾時(shí),反動(dòng)統(tǒng)治階級(jí)必然聯(lián)合起來(lái)進(jìn)攻革命的估計(jì),指出紅軍的任務(wù)必須為打敗敵人的進(jìn)攻作好準(zhǔn)備。毛澤東強(qiáng)調(diào):“我們的任務(wù)是要在反動(dòng)統(tǒng)治階級(jí)爭(zhēng)取改良主義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未解決之前,來(lái)一個(gè)一省首先勝利,繼續(xù)此勝利的發(fā)生與擴(kuò)大,來(lái)沖破消滅反革命聯(lián)合的進(jìn)攻。”毛澤東在峽江會(huì)議上的這些分析,從根本上否定了李立三認(rèn)為軍閥混戰(zhàn)是越打越大,最后自己滅亡的錯(cuò)誤估計(jì)。因此,峽江會(huì)議對(duì)于糾正立三錯(cuò)誤對(duì)形勢(shì)冒險(xiǎn)主義的估計(jì),克服其在紅一方面軍的影響,從思想上轉(zhuǎn)到正確路線(xiàn)上來(lái)又向前進(jìn)了一步。
太平圩會(huì)議出現(xiàn)反復(fù)和波折。10月20日,紅一方面軍總部機(jī)關(guān)及一軍團(tuán)繼續(xù)向袁水流域推進(jìn),22日到達(dá)峽江太平圩。為了繼續(xù)討論紅軍的軍事行動(dòng)問(wèn)題,前委于10月23日又召開(kāi)了會(huì)議,這就是太平圩會(huì)議。根據(jù)敵情通報(bào),國(guó)民黨軍閥戰(zhàn)爭(zhēng)暫時(shí)緩和,正調(diào)兵遣將準(zhǔn)備大肆進(jìn)攻紅軍。敵譚道源師全部開(kāi)到了南昌,許克祥師已到了九江,金漢鼎、毛炳文兩個(gè)師都開(kāi)來(lái)江西,公秉藩師扎在撫州,袁州有湘敵羅霖的部隊(duì)。根據(jù)敵情嚴(yán)重的變化,太平圩會(huì)議立即改變了峽江會(huì)議進(jìn)攻南昌、九江先占領(lǐng)高安的行動(dòng)計(jì)劃,決定用7天時(shí)間(即從10月24日到30日),將主力部隊(duì)靠新余、清江的袁水兩岸配置,發(fā)動(dòng)群眾,籌措給養(yǎng),準(zhǔn)備在這一帶擺開(kāi)架勢(shì),創(chuàng)造戰(zhàn)勝敵人的條件。太平圩會(huì)議對(duì)敵軍將要進(jìn)攻我軍的形勢(shì),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看得比較清楚了。但是,太平圩會(huì)議面對(duì)敵人的進(jìn)攻,對(duì)紅軍是繼續(xù)前進(jìn)還是后退、到底在什么地方反“圍剿”等問(wèn)題并沒(méi)有得到徹底解決,甚至發(fā)生激烈爭(zhēng)論,有些高級(jí)干部仍極力主張前進(jìn)打進(jìn)攻之?dāng)常^續(xù)采取攻打南昌、九江的軍事行動(dòng)。
羅坊聯(lián)席會(huì)議及其后紅軍前委會(huì)議完成偉大戰(zhàn)略轉(zhuǎn)折。10月25日,紅一方面軍總部移師羅坊。毛澤東主持召開(kāi)了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和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聯(lián)席會(huì)議,出席會(huì)議的有長(zhǎng)江局代表周以栗、前委委員和省行委領(lǐng)導(dǎo)人。在討論中,大家通過(guò)對(duì)形勢(shì)的分析和對(duì)兩次攻打長(zhǎng)沙的教訓(xùn)以及占領(lǐng)吉安的成功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認(rèn)識(shí)到在敵人對(duì)南昌、九江大量增兵,加強(qiáng)固守,一步步向我紅軍、江西蘇區(qū)進(jìn)攻的情況下,紅軍必須改變?cè)瓉?lái)的進(jìn)攻計(jì)劃。對(duì)這些問(wèn)題的討論,取得一致共識(shí)。因此,10月26日,會(huì)議正式形成了會(huì)議決議案(即《目前政治形勢(shì)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wù)》)。決議案明確指出:“目前在敵人大舉增兵與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勢(shì)之下,單憑紅軍輕襲南昌、九江,而且紅軍相當(dāng)給養(yǎng)都不具備,運(yùn)輸條件十分缺乏,這無(wú)疑的要成為游擊式的進(jìn)攻,結(jié)果攻不下又轉(zhuǎn)而他往,反使一省勝利延期實(shí)現(xiàn)。所以這一輕裝襲取的游擊觀點(diǎn)與爭(zhēng)取一省首先勝利有計(jì)劃的有布置的戰(zhàn)略絕不相容,應(yīng)加以嚴(yán)重的糾正。”[1]P194
10月30日,紅軍前敵委員會(huì)在羅坊決定了誘敵深入的方針。[2]P24611月1日,朱德、毛澤東下達(dá)《紅一方面軍移師贛江東岸分散工作籌款的命令》,表示“方面軍以原任務(wù)擬誘敵深入赤色區(qū)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這樣,紅一方面軍主力正式移師贛江東岸,拉開(kāi)第一次反“圍剿”戰(zhàn)爭(zhēng)序幕。
從歷史發(fā)展看,紅一方面軍前委自撤圍長(zhǎng)沙至羅坊的這幾次會(huì)議是緊密相聯(lián)的,目的都是為了克服立三“左”傾軍事冒險(xiǎn)主義錯(cuò)誤。紅軍撤圍長(zhǎng)沙至袁州會(huì)議是反立三錯(cuò)誤的良好開(kāi)端,峽江會(huì)議開(kāi)始了轉(zhuǎn)變,太平圩會(huì)議停止了紅軍進(jìn)攻但認(rèn)識(shí)并不一致,羅坊聯(lián)席會(huì)議及其后前委會(huì)議是這幾次會(huì)議的繼續(xù)。羅坊聯(lián)席會(huì)議及其后前委會(huì)議所作出的重大決策,使紅一方面軍完全轉(zhuǎn)到正確路線(xiàn)上來(lái)。羅坊聯(lián)席會(huì)議及前委會(huì)議并非孤立的、突兀的,而是發(fā)展的、前進(jìn)的必然。羅坊聯(lián)席會(huì)議決定了戰(zhàn)略目標(biāo)、戰(zhàn)略方向,紅軍前委會(huì)議決定了戰(zhàn)略方針、戰(zhàn)略方法。至此,紅一方面軍真正開(kāi)始了由戰(zhàn)略進(jìn)攻到戰(zhàn)略退卻,由游擊戰(zhàn)到運(yùn)動(dòng)戰(zhàn)的偉大轉(zhuǎn)折。
二、理性地分析羅坊爭(zhēng)論
羅坊會(huì)議,名曰中共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和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聯(lián)席會(huì)議。參加者,自然就是這兩個(gè)委員會(huì)的成員。遍查史料,我們未能發(fā)現(xiàn)羅坊會(huì)議參加者的直接文獻(xiàn)依據(jù)。眾多文獻(xiàn)中,亦無(wú)諸如羅坊會(huì)議紀(jì)錄或羅坊會(huì)議紀(jì)要等核心材料。《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毛澤東自述》以至權(quán)威部門(mén)所著《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亦未披露完整參會(huì)人員名單。《朱德選集》《朱德年譜》《朱德自述》也不曾披露參會(huì)名單。最新出版的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朱德傳》稱(chēng):“毛澤東、朱德、周以栗、彭德懷、滕代遠(yuǎn)、袁國(guó)平、李文林(江西省行委書(shū)記)、曾山(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等出席了會(huì)議。”這與同樣權(quán)威的中國(guó)工農(nóng)紅軍第三軍團(tuán)史編委會(huì)編的《中國(guó)工農(nóng)紅軍第三軍團(tuán)史》中指出的“紅三軍團(tuán)領(lǐng)導(dǎo)人彭德懷、滕代遠(yuǎn)、袁國(guó)平、何長(zhǎng)工等參加了會(huì)議”似乎不太一致。與親歷者何長(zhǎng)回憶錄亦有差別。何數(shù)部回憶錄均稱(chēng)親自參加了羅坊會(huì)議。在1987年解放軍出版社版的《何長(zhǎng)工回憶錄》還說(shuō):“記得峽江會(huì)議的參加者均出席會(huì)議,彭德懷同志沒(méi)有參加。”我們所見(jiàn)最早一位親歷者1962年1月的回憶錄稱(chēng):“1930年10月間,在毛主席的領(lǐng)導(dǎo)下,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委(原是贛西南特委,立三路線(xiàn)時(shí)改為中共江西省行委的)在峽江縣羅坊舉行過(guò)重要會(huì)議。到會(huì)的人,除由毛主席主持會(huì)議外,有彭德懷、袁國(guó)平二同志,軍隊(duì)還有其他同志(忘記了姓名)參加,江西省行委有李文林、曾山、陳正人三人,還有長(zhǎng)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也參加了會(huì)議。”[1]P249該親歷者在“文革”中的回憶錄,又有新的說(shuō)法:“羅坊會(huì)議是毛主席主持召開(kāi)的,出席會(huì)議的有朱德,一軍團(tuán)有林彪、羅榮桓、黃公略、羅炳輝,三軍團(tuán)有滕代遠(yuǎn)、彭德懷、袁國(guó)平、何長(zhǎng)工,地方上是李文林、陳正人和我,中央長(zhǎng)江局代表周以栗也參加了這次會(huì)議,總共是10多個(gè)人。”[1]P256由此可見(jiàn),羅坊會(huì)議出席者似乎成為需要考證的問(wèn)題。
紅一、三軍團(tuán)永和市會(huì)師后,成立紅一方面軍和中共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毛澤東任中共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書(shū)記和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朱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但前委成員有何人氏,《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不曾公布;《朱德傳》僅稱(chēng):“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huì),毛澤東為書(shū)記,朱德、彭德懷等為委員。”綜合分析,羅坊會(huì)議的參加者,一種可能應(yīng)是中共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的委員和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的委員,或是這兩個(gè)委員會(huì)的主要成員和中共中央長(zhǎng)江局代表周以栗。第二種可能,應(yīng)是紅一方面軍第一、第三軍團(tuán)領(lǐng)導(dǎo)人和所屬第四、第三、第十二、第五、第八軍的主要軍政領(lǐng)導(dǎo),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領(lǐng)導(dǎo)人及中共長(zhǎng)江局代表周以栗。其名單如下:主持人紅一方面軍前委書(shū)記、紅一方面軍兼紅一軍團(tuán)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參加者:中共中央長(zhǎng)江局代表周以栗,紅一方面軍兼紅一軍團(tuán)總司令朱德,紅一方面軍兼紅一軍團(tuán)參謀長(zhǎng)朱云卿,紅一方面軍兼紅一軍團(tuán)政治部主任楊岳彬,紅三軍團(tuán)總指揮彭德懷,紅三軍團(tuán)總政治委員滕代遠(yuǎn),紅三軍團(tuán)政治部主任兼紅八軍政治委員袁國(guó)平,紅三軍團(tuán)參謀長(zhǎng)兼紅五軍軍長(zhǎng)鄧萍,紅四軍軍長(zhǎng)林彪、政治委員羅榮桓,紅三軍軍長(zhǎng)黃公略、政治委員蔡會(huì)文,紅十二軍軍長(zhǎng)羅炳輝、政治委員譚震林,紅五軍政治委員張純清,紅八軍軍長(zhǎng)何長(zhǎng)工。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書(shū)記李文林,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常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常委、宣傳部長(zhǎng)陳正人等。
羅坊會(huì)議文獻(xiàn),目前我們只看到一份聯(lián)席會(huì)議決議,即《目前政治形勢(shì)與紅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wù)》。同樣具有文獻(xiàn)價(jià)值的毛澤東的有關(guān)論述,散見(jiàn)于《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的一些文章中,這些文章,只是零星地、偶爾地提及羅坊會(huì)議,并無(wú)專(zhuān)門(mén)論述。朱德的論述,新版的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朱德詩(shī)詞集》偶爾提到,還將羅坊自注為峽江,而非新余。[3]P350然而,我們卻看到大量老同志文革時(shí)期的回憶錄。權(quán)威部門(mén)的領(lǐng)袖傳記稱(chēng):“毛澤東在會(huì)上明確提出紅軍絕不能冒險(xiǎn)攻打南昌,必須采取誘敵深入作戰(zhàn)方針。開(kāi)始討論時(shí),少數(shù)人不贊成這個(gè)主張,李文林、袁國(guó)平提出,‘不打南昌,會(huì)師武漢,就是違背中央精神,就會(huì)斷送中國(guó)革命’”。[4]P238羅坊會(huì)上是否有過(guò)激烈爭(zhēng)議爭(zhēng)論,是否少數(shù)人不贊成毛澤東主張,是否有人提出言辭過(guò)激以至立三路線(xiàn)的主張,我們不掌握第一手史料,不敢冒然下結(jié)論。一位親歷的紅軍高級(jí)將領(lǐng)回憶說(shuō):“會(huì)議不象峽江會(huì)議爭(zhēng)議得如此激烈。”而峽江會(huì)議,“地方上的幾位同志很少發(fā)言,主要是‘看會(huì)’,看軍隊(duì)同志的態(tài)度”。[5]P290-291這顯然與權(quán)威部門(mén)傳記所引回憶針?shù)h相對(duì)、大相徑庭。然而,客觀理性分析考察一下羅坊會(huì)議前后真實(shí)情形卻是非常有意義的。
羅坊會(huì)議前不到20天,即10月7日,江西省工農(nóng)兵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在《宣布本府成立及政綱》的《布告》中稱(chēng):“消滅軍閥制度,完成全省總暴動(dòng),爭(zhēng)取武漢及附近各省首先勝利,完成蘇維埃的勝利。”[6]P200同一天,江西省蘇維埃大會(huì)通過(guò)的《堅(jiān)決進(jìn)攻南昌九江決議案》指出:“當(dāng)前的偉大任務(wù)就是怎樣完成奪取江西全省爭(zhēng)取武裝首先勝利去促成全國(guó)暴動(dòng),吉安暴動(dòng)之勝利是江西全省勝利的開(kāi)臺(tái),緊接著就是南昌九江的奪取,中間決不容有一刻的停留……一刻不停的堅(jiān)決進(jìn)攻南昌九江是全江西工農(nóng)革命群眾緊迫的實(shí)際任務(wù)。”[6]P202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并非僅僅山溝里的江西地方黨,其委員包括張國(guó)燾、毛澤東、彭德懷、羅炳輝、滕代遠(yuǎn)、陳毅、黃公略、楊岳彬、朱德等53人。羅坊聯(lián)席會(huì)議決議開(kāi)宗明義指出:“吉安的勝利就是江西一省勝利的開(kāi)始……不僅號(hào)召全江西革命群眾最近期間完成江西總暴動(dòng),對(duì)于爭(zhēng)取全國(guó)革命勝利,同時(shí)是有偉大意義的。”[1]P187決議特別強(qiáng)調(diào),“反對(duì)爭(zhēng)取一省政權(quán)的游擊路線(xiàn)”[1]P193、“爭(zhēng)取江西首先勝利是一方面軍與江西黨部的當(dāng)前任務(wù)”[1]P195、“堅(jiān)決以階級(jí)決戰(zhàn)答復(fù)敵人的進(jìn)攻,爭(zhēng)取江西首先勝利,在革命高潮之前加緊反對(duì)一切改良主義、改組派、第三黨、AB團(tuán)取消派及最近蔣介石之國(guó)民會(huì)議欺騙政策”[1]P196。決議規(guī)定一方面軍“目前的戰(zhàn)略是在占領(lǐng)南潯占領(lǐng)南昌九江的總目標(biāo)下,繼續(xù)吉安勝利,爭(zhēng)取進(jìn)一步的勝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間一帶發(fā)動(dòng)群眾、籌措給養(yǎng)、準(zhǔn)備與敵人作大規(guī)模的決戰(zhàn)”[1]P201。前引權(quán)威部門(mén)領(lǐng)袖傳記稱(chēng)毛“明確提出紅軍決不能冒險(xiǎn)攻打南昌”,“少數(shù)人不贊成”,不知此結(jié)論如何下得?一位方面軍領(lǐng)導(dǎo)人的回憶似乎透露了一些真實(shí)情況:“經(jīng)過(guò)充分討論和毛主席以及長(zhǎng)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說(shuō)服,我們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確意見(jiàn),當(dāng)然我們的轉(zhuǎn)變并不是開(kāi)一次會(huì)議解決問(wèn)題的。而是毛主席費(fèi)了很大的功夫,費(fèi)了最大的耐心,開(kāi)了許多次會(huì),我們的思想才通。”[4]P238羅坊紅一方面軍前委會(huì)后,朱毛頒布《紅一方面軍移師贛江東岸分散工作籌款的命令》,仍有人思想不通。毛澤東1936年12月在《中國(guó)革命戰(zhàn)爭(zhēng)的戰(zhàn)略問(wèn)題》第五章第二節(jié)“戰(zhàn)略退卻”中指出:“人們由于沒(méi)有經(jīng)驗(yàn)而不相信戰(zhàn)略退卻的必要,莫過(guò)于第一次反對(duì)‘圍剿’的時(shí)候。當(dāng)時(shí)吉安、興國(guó)、永豐等縣的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無(wú)不反對(duì)紅軍的退卻。但是有了這一次經(jīng)驗(yàn)之后,在后來(lái)的幾次以對(duì)‘圍剿’時(shí),就完全沒(méi)有這個(gè)問(wèn)題了。”[7]P214在紅軍高級(jí)干部中,仍有人主張不過(guò)贛江,一、三軍團(tuán)分家、夾江而陣。[8]P160朱德在1944年編寫(xiě)紅軍一軍團(tuán)史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huà)時(shí)說(shuō):“長(zhǎng)沙打不下,準(zhǔn)備折回江西。但中央不準(zhǔn),有些干部也反對(duì)回江西,還要我們?nèi)ゴ蛭錆h、打九江。紅三軍團(tuán)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9]P68毛澤東也感慨:“戰(zhàn)略退卻,在干部和人民還沒(méi)有經(jīng)驗(yàn)時(shí)在軍事領(lǐng)導(dǎo)的權(quán)威還沒(méi)有達(dá)到把戰(zhàn)略退卻的決定權(quán)集中到少數(shù)人乃至一個(gè)人的手里而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時(shí),說(shuō)服干部和人民的問(wèn)題是一個(gè)十分困難的問(wèn)題。”[7]P213
上引權(quán)威文獻(xiàn)表明,羅坊會(huì)議前后,攻打長(zhǎng)沙、武漢、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中心城市,不僅是中共中央的指令,而且也是紅一方面軍和江西黨內(nèi)普遍的認(rèn)識(shí),毛澤東、朱德也概莫能外。羅坊之前,太平圩、峽江、袁州諸次會(huì)議,黨內(nèi)紅軍中反反復(fù)復(fù)已爭(zhēng)論了一路,要客觀地理性地分析羅坊的爭(zhēng)論,不必過(guò)度渲染和夸張。在革命隊(duì)伍內(nèi)部,在共產(chǎn)黨內(nèi),在紅軍高級(jí)領(lǐng)導(dǎo)人之間,出現(xiàn)任何不同意見(jiàn)或這樣那樣的爭(zhēng)論都是正常的,都是可以允許的,這種爭(zhēng)論是不同認(rèn)識(shí)的爭(zhēng)論,是不同觀點(diǎn)乃至觀念的碰撞,不必上綱上線(xiàn)更不必稱(chēng)之謂路線(xiàn)之爭(zhēng)。相反,通過(guò)不同觀點(diǎn)的交鋒、撞擊,最終達(dá)成了思想認(rèn)識(shí)的統(tǒng)一,避免了黨內(nèi)及紅軍內(nèi)部原則分歧乃至分裂,這是一件值得大書(shū)特書(shū)的好事。因此,羅坊會(huì)議開(kāi)成了一個(gè)團(tuán)結(jié)的會(huì)、共同對(duì)敵的會(huì)。會(huì)議的成功召開(kāi)及其后戰(zhàn)爭(zhēng)實(shí)踐,無(wú)論在對(duì)敵斗爭(zhēng)還是正確解決黨內(nèi)不同認(rèn)識(shí),都提供了一個(gè)很好的成功范例。
三、公正地評(píng)價(jià)羅坊會(huì)議爭(zhēng)議人物
長(zhǎng)期以來(lái),學(xué)術(shù)界對(duì)袁國(guó)平、李文林似乎評(píng)價(jià)不高、頗具爭(zhēng)議,固然與歷史上的恩恩怨怨有關(guān),羅坊會(huì)議“持不同政見(jiàn)”或倍受詬病的態(tài)度,或許也是重要原因?其實(shí)袁的態(tài)度并非代表個(gè)人,前文已述此處不再重復(fù)。李文林作為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書(shū)記、江西地方黨組織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即便有自己觀點(diǎn),甚至有與前委不一致的觀點(diǎn),也無(wú)可厚非,更不必過(guò)分苛責(zé)。相反,從毛澤東、朱德有關(guān)論述中,我們看不出李文林與前委的原則分歧或根本對(duì)立,彭德懷、滕代遠(yuǎn)等紅軍高級(jí)領(lǐng)導(dǎo)人也不曾描述過(guò)李文林在會(huì)上的態(tài)度言論。前委與行委聯(lián)席會(huì)議第二天,行委就與前委共同署名發(fā)布《目前政治形勢(shì)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wù)》。半月之后,11月11日,又與前委共同署名發(fā)布《紅軍第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通告》。11月20日,毛澤東又以總前委代表身份致信江西省行委,通報(bào)水南情況,近期敵情,“并望省行委……每天各有一個(gè)信送到總前委,務(wù)使消息靈通為要”[6]P210-211。倘李文林固執(zhí)己見(jiàn)或與前委原則分歧,又如何解釋迅速聯(lián)合署名發(fā)文?毛澤東又如何一如既往地信任與尊重?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致林彪著名的通信《對(duì)時(shí)局估量和紅軍行動(dòng)問(wèn)題》中,對(duì)李文林及其“李文林式”根據(jù)地非常推崇。毛澤東指出:“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jù)地的,有計(jì)劃地建設(shè)政權(quán)的,紅軍游擊隊(duì)與廣大農(nóng)民群眾緊密配合著從斗爭(zhēng)中訓(xùn)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kuò)大武裝從鄉(xiāng)暴動(dòng)隊(duì)、區(qū)赤衛(wèi)隊(duì)、地方紅軍以致于超地方紅軍的,政權(quán)發(fā)展是波浪式向前擴(kuò)大的政策,無(wú)疑義地是正確的。”[10]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書(shū)記處編印《六大以來(lái)》時(shí)全文刊印了此信。建國(guó)后編入《毛澤東選集》時(shí),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píng)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也刪去了“賀龍式、李文林式”。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談話(huà)時(shí)兩度談到李文林。在《蘇維埃運(yùn)動(dòng)》中稱(chēng):“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領(lǐng)導(dǎo)的游擊隊(duì),開(kāi)始在江西的興國(guó)和東固活躍起來(lái)。這個(gè)運(yùn)動(dòng)以吉安一帶為根據(jù)地,這些游擊隊(duì)后來(lái)成為第三軍的核心,而這個(gè)地區(qū)本身則成為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根據(jù)地。”[11]P57《紅軍的成長(zhǎng)》則說(shuō):“1930年春,李文林、李韶九領(lǐng)導(dǎo)的幾支游擊隊(duì)改編為紅軍第三軍,由黃公略任指揮,陳毅任政委。”[11]P62
這些收入《六大以來(lái)》《毛澤東自述》的文字,再清楚不過(guò)地說(shuō)明了毛澤東對(duì)李文林的真實(shí)評(píng)價(jià)和態(tài)度。按照慣例,黨和國(guó)家領(lǐng)導(dǎo)人或軍隊(duì)高級(jí)將領(lǐng)或根據(jù)地、紅軍創(chuàng)始人誕辰百年之際,都要舉行相應(yīng)規(guī)模的百年誕辰紀(jì)念活動(dòng)。2000年、2006年分別是李文林和袁國(guó)平誕辰100周年,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沒(méi)有看到對(duì)“贛南紅軍和蘇區(qū)創(chuàng)建人”和“中國(guó)工農(nóng)紅軍和新四軍高級(jí)指揮員”的李袁二位革命先輩的任何紀(jì)念活動(dòng)。正如雖然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遵義會(huì)議后仍指責(zé)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抗戰(zhàn)初期對(duì)日作戰(zhàn)與毛澤東方針相左,并不影響林彪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元帥和人民解放軍軍事家一樣,我們對(duì)于英勇?tīng)奚母锩攘以瑖?guó)平、李文林能否更寬容一些,能否更客觀公正一些,能否盡可能少些個(gè)人恩怨?在羅坊會(huì)議過(guò)去80周年,即將迎來(lái)建黨90周年的今天,我們史學(xué)界、理論界應(yīng)當(dāng)具備這種氣度和膽識(shí)。
注 釋?zhuān)?/p>
①1930年10月26日的 《目前政治形勢(shì)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wù)》,署名“紅軍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其后11月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通告》,11月10日的《宣傳動(dòng)員令》均稱(chēng)“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或“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紅軍第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故本文尊重歷史文獻(xiàn),稱(chēng)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而不稱(chēng)紅一方面軍總前委。
[1]江西黨史資料(第6輯),中共江西省委黨史委、中共江西省委黨史室編,1988年版。
[2]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朱德詩(shī)詞集,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7年版。
[4]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6年版。
[5]何長(zhǎng)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6]江西黨史資料(第7輯),中共江西省委黨史委、中共江西省委黨史室編,1988年版。
[7]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c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
[11]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湯靜濤,男,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宣教處處長(zhǎng)。
1930年10月25日,中共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huì)和江西省行動(dòng)委員會(huì)在江西新余羅坊舉行聯(lián)席會(huì)議①,史稱(chēng)羅坊會(huì)議。羅坊會(huì)議是紅一方面軍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會(huì)議,它奠定了紅一方面軍粉碎國(guó)民黨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的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標(biāo)志著紅一方面軍由游擊戰(zhàn)向運(yùn)動(dòng)戰(zhàn)、由戰(zhàn)略進(jìn)攻向戰(zhàn)略退卻的重大轉(zhuǎn)折。因此,羅坊會(huì)議在紅一方面軍反“圍剿”作戰(zhàn)史、毛澤東軍事思想發(fā)展史、第二次國(guó)內(nèi)革命戰(zhàn)爭(zhēng)史上都具有相當(dāng)重要的地位。本文根據(jù)原始文獻(xiàn)和權(quán)威史料,擬對(duì)羅坊會(huì)議戰(zhàn)略決策作一簡(jiǎn)要回顧,對(duì)羅坊會(huì)議爭(zhēng)論問(wèn)題作一疏理和概括,并對(duì)羅坊會(huì)議的爭(zhēng)議人物作些分析述評(píng)。
責(zé)任編輯 張榮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