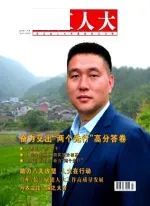權力謊言不能承受之重
■ 單士兵
權力謊言不能承受之重
■ 單士兵
“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這句話打動過無數人的內心。只不過,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要真正打通被民意苦苦訴求的那條“講真話”的路徑,似乎仍有重重的阻礙。
“講真話”,這樣一件本屬常識范圍內的事情,近來卻不斷被捧場熱議。人們不禁要問,這三個看似直白平淡,卻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種內涵的文字,在我們社會的變遷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嬗變?又折射出怎樣的社會生態、官場規則?
前不久,《南都周刊》一篇名為《誰在講真話》的深度報道清晰地盤點了近來有關“講真話”的尷尬情境,讓人們看到中國各個階層在各種領域內,圍繞“講真話”這樣的訴求,曾進行過太多的努力與試探,但最后往往還是會陷入令人失望的境地。在這篇報道中,有這樣的建議,比如白巖松說,“當你不畏懼的時候,就會說真話”;六六說,“希望我們的人格能統一”。
問題是,誰能輕易說自己真的無所畏懼?老子曾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句話說得不僅是勇氣,更有悲情。悲情就是緣于代價的沉重。過多寄望于以“民不畏死”的代價來實踐講真話的訴求,太奢侈,也不現實。在貴州省甕安事件發生后,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痛定思痛:“甕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講真話,是我們的責任。”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讓權力制造出強大的壓抑與緊張,導致人們不敢說真話呢?
在權利與權力的博弈中,權力曾經制造出重重的障礙,讓真話與真相無法展示于公眾面前,在公眾內心植入強大的無力感。比如,3個月前在江蘇省東海發生的父子自焚阻止強拆事件中,連自焚者的遺體都被權力部門移走,連當事人的親屬都被送至野外看管。對真相的回避,對公民話語權的剝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可以讓謊言擁有自由生長的空間。
在稀薄的講真話的土壤之中,在頻繁為一句真話支付過多代價之后,麻木中庸也就成為一種重要的個體生存姿態,人們越來越像是“聯系松散的土豆”,這也使個體維權經常處于尷尬的地位。這種民眾“說真話”的逼仄空間,其實寓意著空話、套話、謊話已經形成了極其強大的話語霸權。
繼年初《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及報社公開挑戰山西省衛生廳的權力公信之后,前不久昆明市五華區政府就“城管部門在執法中與違法占道經營者發生糾紛事件”召開新聞發布會,由于一些說法與記者表述的內容不符,也招致出席發布會的《生活新報》編委當即表示強烈抗議。這種挑戰與抗議,意味著權力謊言已經成為社會無法容忍之痛,全社會對“講真話”的訴求已處于空前激烈的階段。
一個充斥著謊言的社會是可悲的。在今年“兩會”期間,連全國政協常委張維慶都感嘆,當高官20年“覺得講真話越來越難”,而倪萍委員則干脆說:“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這樣的現實與邏輯,其實也直接揭示了現在很多權力階層處于六六所說的“人格分裂”狀態。當社會把大量關乎民生福祉與公共利益的責任,托付給很多“人格分裂”的群體,這本身就是一種可怕的警示,誰也無法預期這樣的權力何時會溫順,何時會暴蠻,何時能守規矩,何時會變得瘋狂。
巴金曾說:“只有講真話,才能認真地活下去。”的確,人人都需要講真話。但政府官員更需要講真話,因為講真話是權力的底線。太多的權力不說真話,其實就是最大的社會不理性。特別是在那些涉及公共安全與權利福祉的問題上,如果沒有講真話與聽真話構建起的制度通道,一邊是民意得不到應有的尊敬,一邊是公眾的知情權得不到及時的滿足;在這樣的情況下,權力就只是活在自己的任性中,隨意踐踏公民權利的現象就會時常發生,導致公眾內心聚攏起的濃厚積怨無法得到及時釋放。在近些年發生的許多群體性事件中,之所以會出現那么多“幫閑”與“不明真相的群眾”,說到底,是因為權力在一次次講述“狼來了”的謊言之后,招致強烈的信任危機,成為了民意仇視的對象。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古人早就闡述過的道理,只是今天依舊未能成為權力普遍信奉的真理。當一些權力在謊言的“人格分裂”中慢慢淪陷于人性與法治的黑洞,再去簡單訴求那種說真話的道德回歸,顯然已是無力回天。
如果對那些不能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下運行的權力繼續姑息縱容,任由他們依據編織的謊言去維護自身利益,那么整個世界就會因為缺少真話和充斥謊言變得讓人無所適從。如此這般不能活在真實中,恐怕誰也不敢說自己不會成為謊言的受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