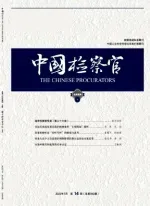商業機會可否認定為受賄罪中的財物
文◎陳新民*
商業機會可否認定為受賄罪中的財物
文◎陳新民*
一句話導讀
商業機會不能等同于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不是我國刑法規定的受賄罪的犯罪對象,對索取商業機會的行為不能認定為受賄罪。
基本案情:2002年12月,某房地產開發公司在某市市北區開發一住宅小區,該市北區房地產管理局綜合計劃科科長王某(負責全區新建住宅配套費征收、管理、返回及空調外機設置審核等),主動找到該房地產公司索要該住宅小區的門窗制作業務。由于王某對轄區內區樓盤開發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約關系,該公司被迫將該小區門窗制作業務交給王某。王某讓其朋友劉某安排承攬單位。業務完成后劉某從承攬單位取得回扣24萬元,將其中12萬元給了王某。公訴機關以王某構成受賄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對于本案中王某的行為屬于索取財物還是屬于索取了商業機會?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王某利用職務便利,索取的門窗制作業務本身是一種經濟利益,目的就是想從中獲利。王某及其朋友劉某在無任何投入的情況下,由承攬方完成門窗制作加工,并從承攬方取得回扣款人民幣24萬元,王某分得12萬元,王某的行為本質上就是在索取賄賂,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第385條之規定,構成受賄罪;第二種觀點認為:王某利用職務便利,謀取的只是商業機會,而商業機會不能等同于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故不是我國刑法規定的受賄罪的犯罪對象,所以對其行為不能認定為受賄罪。本文認為第二種觀點具有合理性,也更具有實踐價值。
一、我國刑法理論界關于賄賂范圍的研究
關于賄賂范圍,在我國刑法學界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財物說。主張賄賂就是財物,即金錢和物品。從中國古代對賄賂的界定及字義解釋,以及新中國刑事立法、現行刑法條文都堅持這一主張。二是物質利益說。這種觀點認為賄賂的內涵應隨著社會發展而有所改變,當前形勢下,以財產性利益賄賂國家工作人員的現象大量存在,其危害與傳統的財物賄賂相比,并無本質區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主張賄賂包括財物和財產性利益。三是利益說。認為賄賂犯罪的本質是權與利的交易,因此賄賂應指能滿足受賄人各種生活需要及精神欲望的一切財產性和非財產性利益,包括財物及其他物質性利益,還包括各種非物質性利益,如性賄賂、提供住房權、提升職務、遷移戶口、安置工作等。前兩種觀點已經或正在被我國刑事法律有條件地采納和接受,但對于利益說中的非財產性利益仍然不認為可以構成賄賂犯罪。本案所體現的不同于傳統觀念中的財物,也不同于一般的財產性利益,王某索取的該商業機會應屬于非財產性利益。
二、賄賂范圍在司法實踐中的發展變化
根據刑法規定,賄賂的范圍限于財物。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賄賂犯罪的手段也呈現出不斷翻新的趨勢,一些人為了規避法律,采用貨幣、物品之外的方式行賄、受賄,如提供房屋裝修、含有一定金額的會員卡、代幣卡(券)、旅游服務等。特別是近年來隨著賄賂犯罪由權錢交易發展到權利交易、權色交易,用設立債權、無償勞務、免費旅游等財物以外的財產性利益以及提供女色、晉職、招工、遷移戶口等非財產性利益進行賄賂的案件頻繁發生。對此類案件特別是采用非財產性利益進行賄賂的案件能否認定為賄賂犯罪,理論上和實踐中均存在不同的認識。從我國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規定看,賄賂可以是任何不正當好處,其字面含義明顯要寬于刑法規定中的財物。對此我國有關法律也有類似的規定,如《招投標法》表述為“財物或者其他好處”,《反不正當競爭法》表述為“財物或者其他手段”,《政府采購法》表述為“賄賂或者獲取其他不正當利益”。將賄賂范圍局限于財物,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打擊各類賄賂犯罪的現實需要,因而有必要擴大其范圍。從司法層面看,在原則上堅持賄賂為財物的同時,當前對于賄賂范圍的理解和掌握實際上有一定程度的突破,部分可以直接物化的財產性利益,如提供免費旅游、無償勞務、消費權證等,有時也會視具體情況被認定為賄賂。
為適應新形勢下懲治賄賂犯罪的客觀需要,綜合考慮我國國情和司法操作的實效性,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實際上也將財物擴大到財產性利益。如該《意見》第7條規定,“商業賄賂中的財物,既包括金錢和實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錢計算數額的財產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裝修、含有金額的會員卡、代幣卡(券)、旅游費用等。財產性利益數額認定以實際支付的資費為準”。至于非財產性利益,如謀取商業機會、招工提干、調換工作、遷移戶口等,則一般不被視為賄賂。
三、索取商業機會入罪存在法律障礙
第一種觀點認為王某利用職務便利,采用謀取商業機會的手法實施權錢交易,最終獲得了非法利益,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第385條之規定,構成受賄罪。該觀點把對商業機會的利用產生的收益直接認定為受賄數額。但我國刑法規定,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目前,我國刑事法律將受賄罪的犯罪對象界定為財物及可以計算數額的財產性利益,不包括商業機會,即商業機會不能成為受賄罪的犯罪對象,所以認定王某通過該商業機會獲得的24萬元為犯罪數額缺乏法律依據。
商業機會不同于財物,也不同于財產性利益。商業機會是一種交易的機會,是一種交易現實性和利益或然性的結合體,沒有交易就沒有交易利益,有交易也可能不產生期望的交易利益,在交易機會變成具體的商業行為之前,商業機會蘊涵著期待性利益,交易利益只是一種期待利益,具有不確定性。有交易就有風險,在期待交易利益的同時也應該承受可能的風險。行為人索取的商業機會是因為其具有極大的獲利可能性,即所謂的穩賺不賠。但這只是一種主觀認識,市場風險的難以預測并不會因為行為人對利益的高期望而變得簡單明了、風平浪靜,行為人在期待利益的同時也必然要承擔可能的風險,而不同的行為人對商業機會的把握和利用其結果也是差之千里。在商業機會轉化為交易利益時行為人也付出了勞動,其中的哪些部分應作為勞動所得,哪些部分應作為犯罪數額實難判定。因此,直接把對商業機會的利用而產生的收益認定為犯罪數額于法無據,于理不通。索取商業機會既不屬于刑法規定的索取財物,也不屬于可以用金錢計算的財產性利益,索取商業機會雖為不當行為,但尚未為我國刑事法律所評價。
四、處理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王某索取的只是商業機會,王某所得的12萬元回扣是加工單位所給,而王某與加工單位并無職務上的制約關系,現有證據也沒有反映某房地產公司將該筆門窗加工業務的利潤抬高以變相給予賄賂,其所獲利益為其經營所得,而索取商業機會的行為不屬于我國刑法所規定受賄罪犯罪對象,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不予認定。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20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