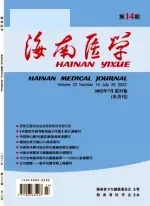平山病的診治進展
郭 劍,陳遜文,曹正霖
(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佛山市中醫院骨一科,廣東 佛山 528000)
平山病(Hirayama disease,HD)最早是由日本學者平山慧造(Keizo Hirayama)等[1]在 1959年首先報道的一種良性自限性運動神經元疾病,主要特征為單側前臂尺側肌萎縮,故又稱青少年上肢遠端肌肉萎縮(Juvenile muscular atrophy of the distal upper extremity)。目前,全球報道不超過 1 500例,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在日本、亞洲其他國家及歐美等國家[2],散在發病,罕見家族史[3]。
本病起病隱匿,好發于青少年,15-25歲為發病高峰,男性多見,男女之比約 20∶1[2]。患者病后 1-5年病情開始穩定,但極少數患者肌肉萎縮仍緩慢進展。隨著世界醫療技術的不斷提高,尤其影像學及輔助檢查的廣泛應用,我國對此病的報道隨之增多,此病臨床上與運動神經元病相似,但預后不同,故提高對此病的診斷和治療是非常必要的,現就此病的診治等介紹如下:
1 臨床表現
典型的臨床表現為一側上肢遠端肌肉萎縮、無力。肌萎縮最早起于手部,隨著病變的進展,少數至上臂;多數為單側損害,亦有不對稱的雙側損害,肌肉萎縮以手小肌肉為主(骨間肌,大、小魚際肌,以尺側明顯),肱橈肌相對輕,呈“斜坡樣”改變。萎縮的肌肉有相應的輕中度肌力減退,多數患者有“寒冷麻痹”,即手暴露在寒冷環境下無力癥狀明顯加重;“伸展束顫”即束顫在安靜狀態下不明顯,但在手伸展時常發生。受累的肢體腱反射對稱正常,也可減弱或消失,但無疼痛麻木等感覺障礙的表現,無錐體束征、發射異常、括約肌功能障礙等。
2 電生理檢查
2.1 常規肌電圖提示神經源性損害[4]對側無萎縮的同名肌肉也可見神經源性損害,但神經傳導速度正常,F波缺如或潛伏期延長。少數病例出現運動傳導速度減慢,Hirayama等[5]在年輕人一側上肢肌萎縮首例尸檢中發現頸膨大前角中央見質疏松、壞死,神經細胞減少、變性,前根纖維脫髓鞘、萎縮,即從病理改變來解釋傳導減慢。單纖維肌電圖顯示,在病情進展階段,其纖維密度和顫抖值均有增加,而到晚期進展階段時,纖維密度進一步增加,但顫抖減少。肌電圖異常多為患側 C6-8神經根分布區域,C7損害最為顯著。
2.2 運動誘發電位 曲頸時運動誘發電位潛伏期延長,波幅下降;肌肉輕微收縮時,動作電位時限延長,波幅增高,呈巨大電位;用力收縮時,峰值電位增高,動作電位數量減少[6]。
2.3 交感神經皮膚反應 雙上肢交感神經皮膚反應平均值較正常對照組明顯延長,提示有無臨床癥狀的上肢均存在交感神經系統功能的損害。
3 影像學檢查
3.1 自然位 頸椎 X光線片正常。CT頸髓造影可發現88%的患者存在下頸髓輕至中度萎縮。但MRI平掃中陽性率只為 49%[2]。
3.2 頸部屈曲位 CT頸髓造影陽性率為94%。MRI平掃達87%可見硬膜囊后壁向前移位拉緊,使下部頸髓易位前置,頸髓受壓及變平,前后徑變扁,頸髓前角的非對稱性萎縮;硬脊膜外的集簇狀血管留空信號,增強掃描后呈高信號,推測為擴張的硬膜外靜脈叢[7-8]。
4 發病誘因
對于快速發育的青少年,經常進行激烈的體育運動是發病的危險因素之一;同時,頸部反復進行屈伸運動或長時間維持屈頸的姿勢,均可能導致已前置易位的硬脊膜從后方推壓低頸段脊髓,從而加重血液循環障礙,引起脊髓前角發生缺血性壞死[9]。
5 發病機制
目前,發病機制尚不明確,但確定本病不是運動神經元病的變異型,可推測為:
5.1 生長發育因素 Toma等[10]研究 7例患者的生長曲線后提出,平山病可能是脊髓與硬脊膜之間的生長發育不平衡所致,根據他們對生長發育曲線與發病年齡的分析揭示:(1)平山病的發病年齡與患者身高的快速增長期相關;(2)快速增長期的結束與疾病趨于穩定期之間的緊密關聯,即肌肉萎縮多在病后 2-4年出現,在快速增長結束后停止進展;(3)頸髓前根相對性縮短決定了此病病程具有自限性。在平山病的 MRI成像圖像上前置的脊髓與其后方的硬脊膜之間存在很大的空間,很少能看到硬脊膜對脊髓形成壓迫,而且在正常的情況下,隨著頸部的屈伸,脊髓也會前后移動,頸屈曲處也可看到相應平面的脊髓變平,下頸段硬膜后壁與椎管后壁分離前移,國外又稱“失連接現象”(Loss of attachment,LOA)[11]。
5.2 動力學因素 Hirayama等[12]據曲頸時的MRI成像顯示 87%可見硬脊膜的位置和前后徑出現動力學異常改變,而在頸部處于直立位時沒有這些動力學改變的特點,推測:(1)患者反復的曲頸運動或長期維持曲頸的姿勢可導致已前置易位的硬脊膜從后方推壓低頸段脊髓,從而造成血液循環障礙,長期如此則引起脊髓前角發生缺血性壞死,繼而引起繼發性神經失用,最終出現運動神經傳導的異常改變;(2)由于本病在日本的發病率最高,所以不排除人種因素。
5.3 無彈性、限制性的硬脊膜壓迫 王向波等[13]在手術中發現硬脊膜早先被牽連的證據,另外術中超聲脊髓活動減弱,病理組織學提示硬脊膜中彈性纖維減少,原有的起伏結構變直。脊髓誘發電位發現曲頸 3 min,波幅降低 34%,直立位后波幅迅速恢復到 98%。作者認為是異常的硬脊膜牽連限制作用所致。不但直立位有受限,而且屈曲位加重,考慮脊髓受限制性與非彈性的硬膜壓迫是此病十分重要的發病機制。
5.4 其他 有學者根據 5例過敏史、兄弟及父子平山病家族史推測與變態反應、遺傳突變可能有關,已有學者報道該病與超氧化物岐化酶(SOD1)基因突變有關[14],需進一步證實。
6 平山病的病理學表現
取萎縮肌肉活檢可見典型的神經源性改變,但與運動神經元病不同,本病受累肌肉節段局限,病變程度相對較輕,萎縮的肌纖維分布不均,靶纖維少見,代償性肥大多見,可繼發肌病性改變[15],但是,肌肉活檢并非臨床診斷本病的金標準,只能作為臨床參考。部分病例在電鏡下觀察示:肌纖維萎縮變小,肌節稍短,Z線及 M線都存在,肌絲分布正常。其他輔助檢查如肌酶學檢測、腦脊液生化以及常規、免疫檢查均無異常。
7 診斷及鑒別診斷
7.1 診斷依據 臨床表現:(1)青春期早期隱匿起病,男性多見;(2)局限性上肢遠端、手指及腕無力,伴有手及前臂遠端肌群萎縮;(3)寒冷麻痹和手指伸展時束顫;(4)癥狀為單側或以一側明顯;(5)無感覺異常,顱神經損害,毒物暴露史,下肢、括約肌、腦干損害;(6)發病后數年間呈進行性(85%患者發病后 1-5年停止進展)。輔助檢查:(1)電生理:肌電圖檢查示萎縮肌肉呈神經源性損害,對側無萎縮的同名肌肉也可見神經源性損害,但周圍神經傳導速度正常。(2)影像學檢查:自然狀態下 MRI可見脊髓非對稱性前角萎縮和硬膜外靜脈叢擴張;曲頸狀態下(平臥位曲頸下頜靠近胸部)MRI檢查可見頸髓的硬脊膜后壁向前推移使下部頸髓受壓[16],脊膜后有月牙形異常信號影。
7.2 判斷標準 (1)肯定:具備“臨床表現”和“輔助檢查”各項;(2)可能:缺少“臨床表現”中除第六項以外的一項,但具備“輔助檢查”各項;(3)可疑:缺少“臨床表現”中除第六項以外兩項以上,但具備“輔助檢查”各項,并排除其他可能相關疾病。平山慧造認為本病診斷的主要依據為臨床特征,病程為自限性尤為重要,肌電圖檢查及 MRI發現椎管后壁前移壓迫脊髓對診斷有重要意義[17]。
7.3 鑒別診斷 (1)進行性脊肌萎縮癥:首發癥狀常為一只手或雙手小肌肉萎縮、無力,漸累及前臂、上臂,遠端萎縮明顯,肌無力,腱反射降低,無感覺障礙及括約肌障礙,與平山病臨床上相似,但進行性脊肌萎縮癥的起病年齡多在 30歲以后,病程呈進展性,至少有兩個部位受損,可波及延髓,磁共振成像顯示受累脊髓和腦干萎縮變小,但平山病無此表現。(2)多灶性運動神經病:為非對稱性的肢體遠端的肌無力伴有肌萎縮,以上肢為主,無感覺及括約肌障礙,無錐體束征,與平山病相似,但多灶性運動神經病發病年齡多在 40歲以上,病程呈緩慢進行性,肌電圖特點是運動神經出現特征性多灶性傳導阻滯。(3)慢性運動軸索性神經病:是最近報道的一種周圍神經病,臨床主要表現為進行性肌萎縮、無力,感覺正常,但其電生理特點是復合肌肉運動電位波幅普遍性降低,可鑒別。(4)脊髓萎縮癥:尤其是脊髓萎縮癥 III型即青少年型,表現為下運動神經元損傷,肌萎縮無力,但多從四肢近端開始,病程呈進展性,為常染色體隱性遺傳,基因檢測可以鑒別。(5)普通脊髓型頸椎病:由于支配頸、胸、腰、骶的神經纖維在皮質脊髓束中從內到外的排列順序,所以脊髓受壓后運動障礙是先下肢后上肢,表現為步態笨拙、搖擺不穩、下肢無力、肌張力增高和出現病理反射,早期可出現動態 Hoffmann征(即患者在頭頸部后伸狀態下引出該反射),并多數有頸肩部麻痹酸痛等癥狀,可以與本病相鑒別。
8 平山病的治療
8.1 非手術治療方法 由于頸部過屈可能是平山病的致病因素,因此,Tokumaru等[18]采用頸托治療,使下頜與胸壁之間保持一定距離,治療后發現患者病程進展時間顯著延長,肌力有所恢復,萎縮得到一定改善,尤其對病程短、輕型脊髓萎縮者效果顯著,但治療時間相對較長。袁泉等[19]利用頸托治療11例,其中 3例已隨訪 1年零 8個月,病情無進展。中醫治療根據中醫“脾主身之肌肉”及“治痿獨取陽明”的理論,我院通過補中益氣湯及歸脾湯加減來治療 10例平山病患者,效果良好,癥狀有相當的改善,故中醫藥治療平山病有一定優勢。
8.2 手術治療方法 早在 1996年 Konno等[20]嘗試用硬脊膜成形術 +脊髓松解術來治療此病,并比較 5例患者手術前后動力學、影像學、超聲學、脊髓誘發電位的變化及臨床癥狀是否改善來驗證手術的治療價值。術中發現橫向切開硬脊膜時,硬脊膜自發的形成一個間隙,驗證了硬脊膜早先被牽連的觀點。手術結果示:當硬脊膜被切開時誘發電位波幅迅速增高至正常的127%;術后頸部位于直立位時脊髓壓迫現象消失;硬脊膜成形術 48 h后可觀察到臨床癥狀已改善,結果顯示手術有效。隨訪證實手術能改善患者近期及遠期神經功能。但目前,多數專家的觀點還是傾向于非手術治療。
隨著我國醫療水平的提高,此病報道日益增多。本病多是在無意中發現,進展緩慢,預后較好,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相當重要。
[1] Hirayama K,Toyokura Y,Tsubaki T.Juvenile muscular atrophy of unilateral upper extremity:a new clinical entity[J].Psychiatry Neurol Jpn,1959,61:2 190-2 198.
[2] Hirayama K.Juvenile muscular atrophy of distal upper extremity(Hirayama disease)[J].Internal Medicine,2000,39(4):283-290.
[3] 孫小添,馬 英.平山病一例[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7,16(21)∶3 053.
[4] 高社榮,胡冬梅,李小剛.平山病的診斷及治療[J].醫學綜述,2008,14(3)∶396-397.
[5] Hirayama K,Tomonaga M,Kitano K,et al.The first autopsy case of“juvenile muscular atrophy of unilateral upper extremity”[J].Shinkei Naika(Neurol Med),1985,22:85-86.
[6] 劉健萍,黃 飚,梁長虹,等.平山病 MRI診斷價值的初步研究[J].醫學影像學雜志,2009,19(7)∶816-819.
[7] Courie-Devi M,Nalini A.Sympathetic skin response in monomelic amyotrophy[J].Acta Neurol Scand,2001,104(3)∶162-166.
[8] Hirayma K.Juvenile muscular atrophy of distal upper extremity(Hirayama disease):focal cervical ischemic poliomyelopathy[J].Neuropathology,2000,20∶91-94.
[9] 許 蕾,黃勃源,李彩英,等.平山病 4例臨床和影像學分析[J].中國神經精神病雜志,2006,32(1)∶23-26.
[10]Toma S,Shiozawa Z.Amyotrophic cervical myelopathy in adolescence[J].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1995,58(1)∶56-64.
[11]Chen CJ,Hsu HL,Tseng YC,et al.Hirayama flexion myelopathy:neutral-position MR imaging fingings-importance of loss of attachment[J].Radiology,2004,231(1)∶39-44.
[12]Hirayama K,Tokumaru Y.Cervical dural sac and spinal cord in juvenile muscular atrophy of distal upper extremity[J].Neurology,2000,54(10)∶1 922-1 926.
[13]王向波.右手肌肉萎縮 1年余(下)--平山病(家族性)[J].中國精神病雜志,2006,32(3)∶附 1-附 3.
[14]Kira J,Ochi H.Juvenile muscular atrophy of the distal upper limb(Hirayama disease)associated with atopy[J].Neurol Neuro surg Psychiatry,2001,70(6)∶798.
[15]陳 強,樊東升,康 德.平山病的臨床研究進展[J].神經疾病與精神衛生,2001,1(4)∶3-4.
[16]Tokumaru Y,Hirayama K.Acervical collar therapy for norrprogressive juvenile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of the distal upper limb(Hirayama's disease)[J].Rinsho Shinkeigaku,1992,32(10)∶1 102-1 106.
[17]楊鳳民,賈剛田.青年單側上肢萎縮(平山病)的診斷[J].國外醫學?神經病學神經外科分冊,1997,24(3)∶159.
[18]Tokumaru Y,Hirayama K.Cervical collar therapy for juvenile muscular atrophy of distal upper extremity(Hirayama disease):results from 38 cases[J].Rinsho Shinkeigaku,2001,41(4-5)∶173-178.
[19]袁 泉,賈建平.11例平山病臨床特征分析[J].中風與神經疾病雜志,2009,26(4)∶477-478.
[20]Konno S,Coto S,Murakami M,et al.Juvenile amyortrophy of the distal upper extremity:pathologic findings of the dura matter and surgical management[J].Spine,1997,22(5)∶486-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