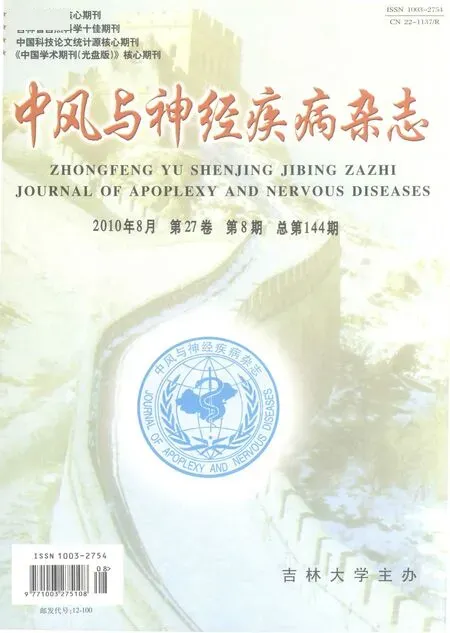慢性前腦缺血致癡呆大鼠 IL-1β、IL-6及 TNF-α的研究
金 濤, 吳 江, 鄒昕穎, 張海寧, 孫 莉
血管性癡呆(Vascular dementia,VD)是老年期癡呆的重要類型。以往認為血管性癡呆是腦梗死所致。近年來臨床研究發現:慢性腦灌注不足尤其是皮質下白質腦血流量慢性持續性下降可能是導致血管性癡呆的主要原因之一,故慢性缺血在 VD發病機制中所起的作用開始引起人們關注。在前期工作中,我們采用雙側頸總動脈永久結扎方法成功制備了慢性前腦缺血動物模型,應用激光多普勒血流儀檢測了各組大鼠術后不同時間點額葉、頂葉、海馬及皮質下區局部腦血流量,利用 Morris水迷宮法檢測各組大鼠的記憶功能,結果顯示雙側頸總動脈永久結扎可導致大鼠出現慢性持續性腦血流量下降及持續性認知功能障礙,說明我們的慢性缺血致血管性癡呆大鼠造模成功[1]。長期以來,免疫炎癥反應作為腦缺血損傷級聯反應中重要的一環一直倍受人們的關注。其中,IL-1β、IL-6及 TNF-α被視為與中樞神經系統缺血相關的最主要炎癥反應分子。至今,人們對 IL-1β、IL-6及 TNF-α在缺血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急性腦缺血尤其是短暫腦缺血后再灌注方面[2~4],而在慢性腦缺血方面研究甚少,有關慢性腦缺血致血管性癡呆大鼠 IL-1β、IL-6及 TNF-α經時變化的基礎研究國內外尚未見報道。
本實驗在前期工作基礎上,采用雙側頸總動脈永久結扎方法制備慢性前腦缺血動物模型,并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癡呆大鼠海馬及顳葉皮質中炎性因子 IL-1β、IL-6及 TNF-α的經時變化,以期闡明 IL-1β、IL-6及 TNF-α在慢性腦缺血致血管性癡呆發病機制中的作用,為臨床上防治血管性癡呆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和方法
1.1 動物模型制備 選用長春高新醫學動物實驗研究中心提供的健康雄性 Wistar大鼠 150只,鼠齡 3~5個月,體重 300~350g。隨機分為對照組和實驗組,實驗組又分為手術后 24h組、1w組、半個月組、1個月組、2個月組、3個月組及 4個月組。采用雙側頸總動脈永久結扎方法制備慢性前腦缺血動物模型,具體方法如下:大鼠術前 12h禁食,4h禁水。用 1%戊巴比妥鈉(10mg/kg)腹腔注射麻醉,保證手術期間有自主呼吸。仰臥固定,頸部去毛、強力碘消毒后沿頸正中切開,分離雙側頸總動脈,并套以“0”號線。分別結扎雙側頸總動脈的遠近端,并從中間剪斷,以確保阻斷動脈血流。術中大鼠肛溫保持在 36.5℃ ~37.5℃,手術后動物送至有通風和空調設備的動物房飼養。對照組(假手術組)除不結扎、不剪斷雙側頸總動脈外,其余過程與手術組相同。
1.2 行為學檢測 采用 Morris水迷宮法進行大鼠記憶功能的測定[1]。
1.3 腦血流量測定 應用瑞典 Perimed AB公司生產的 PeriFlux System 5000型激光多普勒血流儀(LDP)檢測各組大鼠術后不同時間點(術后 24h、1w、半個月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4個月 )額葉、頂葉、海馬及皮質下區局部腦血流量(rCBF)[1]。
1.4 免疫組化檢測癡呆大鼠海馬及顳葉皮質中 IL-1β、IL-6及 TNF-α的表達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采用鏈霉素抗生物素蛋白-過氧化物酶連接法(SP法),其步驟如下:(1)石蠟切片常規脫蠟經乙醇脫水;(2)PBS沖洗 5min×3;(3)3%H2O2-蒸餾水阻斷內源性過氧化物酶 25min;(4)PBS沖洗 5min×3;(5)將切片置入盛有抗原修復液的容器中,抗原修復液為 0.01mol pH=6.0的枸櫞酸鹽緩沖液(工作液),置爐上加熱至溫度達到 92℃~98℃之間,保持5min關火,5min后從爐上移下,待溫度冷卻至70℃,入 PBS沖洗 5min×3;(6)加山羊血清(1∶20)封閉30min;(7)傾去多余的血清,滴加適當稀釋的特異性一抗于切片上,4℃冰箱過夜;(8)PBS沖洗 5min×3;(9)滴加二抗(IgG/Biotin),孵育 40min;(10)PBS沖洗 5min×3;(11)滴加三抗(S-A/HRP)孵育40min;(12)PBS沖洗 5min×3;(13)DAB-蒸餾水溶液顯色,顯微鏡下觀察,控制反應時間;(14)Mayer蘇木精復染,二甲苯透明,中性樹膠封片。結果判定:免疫組化染色陽性結果為棕黃色或棕黑色顆粒。對照:用 PBS代替一抗做陰性對照。定量分析計數方法:在顳葉、海馬區的錐體細胞層,在 20×10倍光鏡下隨機選擇 5個視野,做免疫反應陽性細胞數計數,計數方法采用標準網格,以“個 /視野”為單位,結果取 5個視野的平均值。
2 結 果
2.1 癡呆大鼠海馬及顳葉 IL-1β的變化 IL-1β免疫陽性細胞胞漿內出現棕黃色顆粒。對照組有少許的 IL-1β免疫陽性細胞,大鼠雙側頸總動脈永久結扎后 24h海馬 IL-1β免疫陽性細胞數即明顯增高并達高峰,顳葉在 1w時達高峰,以后均逐漸下降,至 4個月時仍明顯高于對照組(見表1)。
2.2 癡呆大鼠海馬及顳葉 IL-6的變化 IL-6免疫陽性細胞胞漿內出現棕黃色顆粒。對照組有少許的 IL-6免疫陽性細胞,大鼠雙側頸總動脈永久結扎后 24h海馬及顳葉IL-6免疫陽性細胞數即明顯增高,并均于 1w時達高峰,以后逐漸下降,至 4個月時仍明顯高于對照組(見表2)。

表1 癡呆大鼠海馬區及顳葉皮質 IL-1β免疫陽性細胞的比較

表2 癡呆大鼠海馬區及顳葉皮質 IL-6免疫陽性細胞的比較

表3 癡呆大鼠海馬區及顳葉皮質 TNF-α免疫陽性細胞的比較
2.3 癡呆大鼠海馬及顳葉 TNF-α的變化TNF-α免疫陽性細胞胞漿內出現棕黃色顆粒。對照組有少許的 TNF-α免疫陽性細胞,大鼠雙側頸總動脈永久結扎后24h海馬及顳葉TNF-α免疫陽性細胞數即明顯增高,并均于 1w時達高峰,以后逐漸下降,至 4個月時仍明顯高于對照組(見表3)。
3 討 論
認知功能障礙是一個復雜的病理過程,發病機制有很多學說。與記憶有關的腦內結構主要是大腦皮質聯合區、海馬及其鄰近結構、丘腦等。遠事記憶貯存部位主要在大腦皮層特別是額葉、顳葉;近事記憶在邊緣系統,其中海馬是近事記憶信息轉變、貯存的主要部位。前期工作中,我們選擇顳葉、海馬作為觀察點,發現顳葉皮質錐體細胞從術后 24h出現水腫、缺血,以后逐漸發展成凝固性壞死、變性,錐體細胞慢性進行性脫失伴膠質細胞增生;海馬區錐體細胞也從最初的水腫、缺血逐步發展成嚴重脫失、基質疏松、微空泡形成,各實驗組均未見明顯梗死灶[5]。Sontag等曾報道,將大鼠雙側頸總動脈結扎 60min后處死,并無明顯的梗死灶[6],這與我們的研究結果相似。雖然各實驗組均未見明顯梗死灶,而大鼠的認知功能障礙卻持續存在[1],我們認為這與顳葉皮質及海馬區的神經元慢性進行性變性、脫失有關。
以往認為,中樞神經系統(CNS)是受血腦屏障保護的“免疫特免器官”,腦組織僅有很低的免疫活性[7],然而近 10年來不斷涌現的免疫組織化學與分子生物學證據表明,腦具有一個活躍的內源性免疫系統,腦內的慢性炎癥可能在多種神經系統疾病的進行性神經元死亡過程中起重要作用[8]。長期以來,免疫炎癥反應作為腦缺血損傷級聯反應中重要的一環一直倍受人們的關注。其中,IL-1β、IL-6及TNF-α被視為與中樞神經系統缺血相關的最主要炎癥反應分子。至今,人們對 IL-1β、IL-6及 TNF-α在缺血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急性腦缺血尤其是短暫腦缺血后再灌注方面[2~4],而在慢性腦缺血方面研究甚少,有關慢性腦缺血致血管性癡呆大鼠 IL-1β、IL-6及 TNF-α經時變化的基礎研究國內外尚未見報道。為了進一步探討慢性缺血致血管性癡呆的炎癥機制,本實驗采用雙側頸總動脈永久結扎方法制備慢性前腦缺血動物模型,通過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癡呆大鼠海馬區及顳葉皮質 IL-1β、IL-6及 TNF-α的經時變化情況,研究發現對照組大鼠的海馬區及顳葉皮質僅有 IL-1β、IL-6及 TNF-α的少量表達,而大鼠雙側頸總動脈永久結扎后海馬區及顳葉皮質IL-1β、IL-6及 TNF-α免疫陽性細胞數明顯增高,其免疫陽性細胞主要為星形膠質細胞、小膠質細胞和神經元。其中,IL-1β在海馬于術后 24h呈現表達高峰,在顳葉則于 1w時達高峰,以后均有所下降,直至4月其表達仍明顯高于對照組。而 IL-6及 TNF-α在海馬及顳葉均于 1w時呈現表達高峰,以后逐漸下降,至 4個月時表達仍明顯高于對照組。我們推測細胞因子 IL-1β、IL-6及 TNF-α在慢性腦缺血大鼠腦內星形膠質細胞、小膠質細胞和神經元中的持續高表達,可能是由于大鼠腦血流量的持續下降引起。腦組織新陳代謝率很高,腦重量只占體重的 2.2%,腦血流量卻占心輸出量的 15%[6]。當腦灌注壓開始降低時,正常組織通過擴張血管,動用循環儲備來維持 rCBF不變,當 rCBF進一步下降,因能量供應不足,出現細胞膜電位不穩,Na+-K+泵障礙,細胞膜功能受損。Kanno等研究認為,腦缺血的功能閾值為正常腦血流量的 50%,當腦血流量低于正常的 30%時,將出現梗死灶[9]。本組實驗大鼠腦血流量下降程度未達到引起梗死的閾值,所以梗死灶出現較少,而這種腦血流的降低作為一種較弱的刺激,雖不足以引起神經細胞壞死,但可能會刺激星形膠質細胞、小膠質細胞和神經元分泌 IL-1β、IL-6及 TNF-α,并通過一系列免疫炎癥級聯反應介導腦缺血損傷。結合腦血流量變化、病理學及行為學改變我們推測 IL-1β、IL-6及 TNF-α的慢性持續性高表達在慢性腦缺血致血管性癡呆的病理損傷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已有實驗證實,應用免疫抑制劑 FK506可以阻止大鼠慢性腦缺血所致的白質疏松及神經元損傷[10]。由此提示我們在治療慢性腦缺血致血管性癡呆的過程中,輔助抗炎治療可能會阻斷炎性因子所致的炎癥級聯損傷,從而延緩血管性癡呆的病情進展。
[1] 孫 莉,金 濤,丁艷華,等.慢性前腦缺血致癡呆大鼠腦血流量及行為學對比研究[J].中國老年學雜志,2009,29:920-922.
[2] Liu T,Mcdonnell PC,Young PR,et al.Interleukin-1βmRNA expression in ischemic rat cortex[J].Stroke,1993,24:1746-1751.
[3] Berti R,Williams AJ,Moffett JR,et al.Quantitative real-time RT-PCR analysis of inflammatory gene ex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ischemia reperfusion brain injury[J].J Cereb Blood Flow Metab,2002,22(9):1068-1079.
[4] Yang GY,Gong C,Qin Z,et al.Inhibition of TNF-alpha attenuates infarct volume and ICAM-1 expression in ischemic mouse brain[J].Neuroreport,1998,9:2131-2134.
[5] 孫 莉,張 昱,鄒昕穎,等.慢性前腦缺血致癡呆大鼠皮質及皮質下白質區病理學變化的對比研究[J].中風與神經疾病雜志,2004,21(5):403-405.
[6] 馮新為主編.病理生理學[M].第 3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
[7] McGeer EG,Mc Geer PL.The importance of inflammatory mechanisms in Alzheimer disease[J].Exp Gerontol,1998,33:371-378.
[8] McGeer PL,Mc Geer EG.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stem of brain:implications for therapy of Alzheimer and othe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J].Brain Res Rev,1995,21:195-218.
[9] Kanno I,Vemura S,Higro S,et al.Oxygen extraction fraction at maxillary vasodilated tissuein theischemic brain estimated from the regional CO2 responsiveness measured by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J].J Cereb Blood Flow Metab,1998,8:227-235.
[10] Wakita H,Tomimoto H,Akiguchi I,et al.Dose-dependent,protective effect of FK506 against white matter changes in the rat brain after chronic cerebral ischemia[J].Brain Res,1998,792:10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