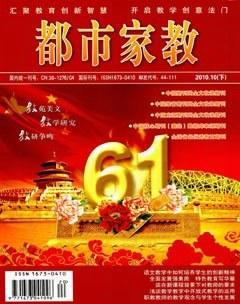語文教學中的想象和藝術感受
王建美
提起藝術,人們會不由自主地想到音樂,舞蹈,繪畫,雕塑之類的東西,而語文這門學科的藝術性容易被人們忽視了,僅注重于實用性和人文性,就是很多語文教師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其實語文學科是非常有藝術感染力的,因為語言是最能描繪豐富多彩的世界的,高爾基指出:“語言是文學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種事實,生活現象一起,構成了文學的材料。”又說:“文學就是用語言來塑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語言來反映現實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維過程。”從中可以看出語文可以將現實,自然景象和思維形象描繪出來,而音樂舞蹈繪畫等都離不開大自然和人的思維創造過程的,因此說語文是非常有藝術感染力的。那么怎樣去感受它的藝術感染力呢?最重要的是想象。
語言文字具有表層意義和深層意義,很多教師(特別是小學初中)只教給表層意義或缺少引導去理解深層意義。其實詞語句子的含義直至文章的場景,意境等的理解,都離不開想象,讓學生發揮想象,聯系生活構造出畫面來。如“蹣跚”含義為:因為腿腳不靈便,走路緩慢搖擺的樣子。很多學生死記住了這句話,如果教師引導學生想象幾個畫面:一個腿腳受傷或身體虛弱的人或不靈便的老年人走路的樣子便是“蹣跚”,學生記住了含義也運用了它。還有一些詞語或句子拼命解釋也很難讓人理解,即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教師不坊讓學生想象一下它們能構造的場面,或動作示范模擬它所能表示的情形就好理解了,要不然會出現解釋“弟弟即哥哥腳下的男人”的笑話。而要感受文章的藝術魅力,更是離不開想象。
很多文學作品,作家都是很注重藝術表現的,文學家其實也是藝術家。山水詩祖師謝靈運就詩文兼善,而且工于書畫,他的詩就注重對山水景物的聲光色的生動描繪。“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是暖色基調,“野曠沙岸凈,天高秋月明”是冷色基調,色彩統一和諧。“鳥鳴識夜棲,木落識風發。異音同致聽,殊響具清越”寫聲音曲盡其妙。“詩圣”杜甫為了在色彩的組合造成先聲奪人的藝術境界,他常把色彩字放在句首,如“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這里僅舉二人為例說明文學作品的藝術感染力,但是不注意引導學生,讓他們發揮想象,在腦海中構筑畫面,場景,就很難體會藝術在其中。
據舒乙回憶說,他的父親老舍先生雖然不是畫家,但他對繪畫很會評論的,他經常評點名畫家的作品。老舍夫人是一位畫家,很能接受他的指點。因此可以看出老舍在繪畫方面的才能,難怪老舍的文章很多就像一幅優美的圖畫,給人以美的享受。下面就老舍《濟南的冬天》一文談談怎樣運用想象,感受它的藝術魅力。
閱讀《濟南的冬天》一文,首先讓學生反復讀課文,在讀的同時細細品味,在腦海中想像構造畫面,再接著讓學生寫出一些具體的景物,根據課文內容,叫學生總結有幾幅怎樣的畫面?可歸納為:“陽光下的老城,雪后濟南的山和城外小雪后的山村”三幅圖畫。
學生可能還停留在籠統,模糊的印象中,緊接著叫學生想象那些畫面,用語言細細的描繪。“陽光下的老城”有山有水,暖和的陽光,含笑的人群,整個基調暖色的,“小雪后濟南的山”又是一番景象,落日的余暉映照著白雪,銀色的山邊襯托起碧藍的天空,色彩明暗對比,使畫面顯得斑斕多姿。“城外小雪后的村莊”是一幅小水墨畫,基調是冷色的,黑白給人素凈淡然的感覺。描繪完畢后,把學生分組,拿起筆畫出這三幅圖,在畫中抓住山和水,突出濟南城“只有北面缺著點口兒”的地理特點。學生有的興趣很高,但也有的拙于繪畫,但不管怎樣,不求于繪畫水平,只要有對景物的體現,讓學生放手畫。畫完后,各小組進行交流對比,那么學生眼中的畫面就豐富起來了。再挑幾名畫的好的學生到黑板上畫,“暖暖的陽光,矮矮的山,白白的雪,小小的村莊,青黑的矮松,澄清的河水漫步的人——”都被描畫出來了,還有的學生補充點什么或改動一兩處。教師同時提醒表示顏色的詞語,陽光是“微黃”的,雪是“白的帶黃”的,樹是“青黑”的——通過這樣的學習,學生體會到了濟南冬天的特點,更得到藝術感受,并明白了“哦,語言文字這么神奇,能構造這么美的畫面。”
當然,《濟南的冬天》一文很容易讓人在腦海浮現美麗的畫面,有的文章不那么明顯,那就更需要我們教師引導學生想象,去藝術性的閱讀語言文字和文學作品。
語文中的藝術感受和想象是聯系非常密切的,不發揮想象是感受不到其中的藝術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