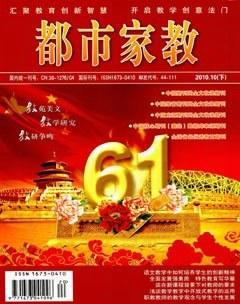離散性與連續性角度下語義模糊根源探析
孔繁星
【摘 要】模糊性是自然語言的根本屬性,它源于客觀世界、人類認知和社會交際等因素的模糊性。研究語言模糊性有助于促進新的表現手法產生,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語言文字的隨意性,人們可以更多地利用語言文字的模糊性去創造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文從語言的離散性與連續性的層面去分析,進行證明語義模糊的根源來自于人類的認知行為和人類語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而導致的語言現象,并非事物本身具有模糊性。
【關鍵詞】語言模糊性 離散性 連續性 主體模糊
語言模糊性的研究催生了模糊集合論,模糊集合論的產生又為一切涉及模糊性的科學領域鋪設了一個描寫模糊性的最一般框架。隨著模糊語言學這個學科的形成,其重要意義越來越明顯。因為模糊性是非人工語言的本質特征,所以,它是語言學不能回避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人類語言中,許多詞語所表達的概念都是沒有精確邊緣的,即都是所謂的“模糊概念”。
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語言符號在傳播過程當中存在著一定障礙,最主要的便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曖昧性與多義性。各種同音、同形但不同義的現象,類似歧義和通感等修辭手法,甚至是不同的文化理解背景都會在很多方面影響語言的表達和接受效果。例如,有一篇西方人文章中講到太平天國時用到了這樣幾個的詞匯:uprising, rebellion, the most destructive。從西方人的角度來說,這幾個詞匯具有貶義色彩,分別為:暴動,叛亂,最具破壞力的。而在中國的讀者的語境影響下,這些詞匯就要被解讀為:起義,反封建運動,打倒舊勢力。所以,相同的語言符號能夠傳遞出不同的意義,也標志了非人工語言的模糊性特點。
一、語言模糊與其根源問題
從模糊語言學這個學科出現起,人們就開始討論這個學科中的一個基本問題:“語詞(語言)的模糊根源在哪里?”。多年來,國內的專家學者們一直關注這個問題,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例如,張喬 (1998)、伍鐵平(1999)、石安石 (1988,1991)、符達維(1990),他們爭論的核心問題是語義的模糊的根源是否為“客體模糊”。符達維在其著作中區分了三項定義:客體模糊、主體模糊和語義模糊;而石安石(1994:94-96則對此觀點持否定態度。其他一些學者也參加了這場辯論,陳維振(2000)、吳振國(2001)、趙德遠(2001)、唐鋒盧(2003)和張華茹(2004)等也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批判性意見。
陳志安、文旭(1996)、吳世雄、陳維振(2000,2001)、姚鴻琨(2001)等還在不同的時期針對不同學者的意見進行了歸納整理工作,其中吳世雄、陳維振的總結較有概括性,本文第三部分將會提到。
對于語義模糊根源的根源問題,眾多學者從符號學、現象學、認知語言學等角度進行新的研究,但仍然沒有達成一致觀點,相反這引發了更多學者從更廣泛的領域對這個問題進行再思考,從而加深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科學認識。
根據知語言學的觀點,語法是依附于語義存在的,所以語法必然具有其語義根據。按照Langacker、Talmy和Taylor等人的看法,人的一般認知系統和心理能力與語言具有非常緊密的關系,這種認知系統和心理能力能夠制約人的語言結構的形成和使用。而這種語法和語義之間的關系都與語言的“離散性”和“連續性”有著直接的關系。
本文擬從認知語言學觀點出發對語言模糊性及根源和前人的研究進行反思,從語言中體現的“離散性”和“連續性”出發,借鑒符號學的觀點,探討這兩個概念在模糊語言學研究中的應用。試圖對“語言模糊性根源”這一問題進行分析,旨在拋磚引玉,為他人研究提供一點幫助。
二、語言的離散性與連續性
離散性和連續性并不是語言學研究獨有的概念,在很多學科領域中都使用了這兩個概念。例如,在物理學中,光既具有粒子性,又具有波動性。嫁接到語言學領域中,所謂的粒子性就是離散性的特征(也有人稱之為粒散性),而波動性則具有連續性的特征。數學領域中也有離散數學和連續數學的概念。本質上來說,這兩個概念反映了人觀察和認識世界的不同方式。在語言的研究方面,不管是對語言現象的研究還是對語言學理論的研究,也都可以使用離散性和連續性這兩個概念。
符號學認為,連續不斷的語流其實是由許多基礎的離散單位構成的,信息的傳播者要重視語言符號本身的離散性。而對于傳播過程中受者一方來說,解碼具有重大的意義,語言符號的離散性特點在這一方面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語言離散性的理論基礎為語言全息論。語言全息論,就是用大自然的規律去解釋人類的語言現象。歐洲中世紀的語法學派“摩迪斯泰(Modestae)學派”認為:“如果能證明大自然的規律與語言內部的規律有一定的聯系,那么就能解釋語言現象。”在語言全息論的理論框架下,我們能夠發現語言的一些新的重要的特征和性質,如語言全息性,即語言全息律、語言遞歸性、語言離散性等等。語言全息論大致上說研究兩個大的問題;一是語言內全息狀態,二是語言外全息狀態。這便是語言全息論總體構想。
如果對一個數量體形成的概念是在其構成整體中有分離或中斷的情況,這個數量體就是(內部)離散性的;否則,對這個數量體形成的概念就是(內部)連續性的,即在其構成整體中沒有分離或中斷的情況。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一把椅子和另一把椅子之間都是分離的,因為在人們的認知概念系統中,每一個人、每一把椅子都有空間上的界限。這就是離散性。而水、土壤、塑料等物質在人們的概念系統中沒有具體的邊界,它們體現的則是連續性。體現在語言表達方面,有界物體一般由可數名詞表示,如英語中的man、desk、bottle等;連續性物質一般由不可數名詞表示,如water、soil、plastic等。
三、語言模糊的產生根源——主體語言模糊
關于語言模糊性產生根源問題,國內專家學者主要有三種觀點,如下:1、認為語言符號的模糊性來源于事物的模糊性,2、語言的模糊性來源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3、模糊性是語言符號本身的基本屬性。本部分從語言的離散性與連續性關系的角度去證明語義模糊是由于人類的認知行為和人類語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而導致語言現象,并非事物本身具有模糊性。
自然界屬于自在怡然的大存在,雖然可以從中發現諸多規律讓人們去利用,但從混沌理論的角度來看,其中的變化性和不可預測性是本質特征。在人們認知中也存在著無法清晰分類和描述的現象,認知的模糊性則因此可能產生,它源于人的認知行為,而不是來自客觀事物本身。針對于這個問題,皮爾斯認為當人們難以確定“事物出現幾種可能的狀態”是否屬于某個命題的時候,在人們的認知中就會出現一種模糊性,同時它也會體現在對認知的表述中。因此,他特別指出“這個命題就是模糊的”、“說話者的語言特點就是模糊的”。羅素關于模糊根源的的論述也是如此,他說:“模糊性和精確性一樣,只能是表達方面的特點,語言屬于表達手段。”由上可見,羅素和羅爾斯關于語言模糊性來源的論述是一脈相傳的。兩者都在強調模糊性就存在于人們對客觀世界的這種認知把握中,語詞作為認知的外在表現手段,也具有了模糊性。
詞義的模糊性根源問題則可以用語詞的“離散性”和“連續性”二者的關系來解釋。首先,語言符號本身具有離散性,那么用具有離散性的語言符號去標志連續的事物,結果就可能造成邊界不明的效果,從而產生模糊性。比如,模糊性與一粒米到一堆米的變化過程有關,但是模糊性并不來源于這種關聯,而是產生于對“從一粒米到一堆米整個變化過程”的抽象切分、分類及用語詞來標志的結果中,也就是說來源于人類用于標志過程的語言中。
很多時候人類使用語言的時候并不具有鮮明的確定性,便是所謂的模糊性。從語言離散性和連續性的角度來觀察,這種模糊性的根源主要是人們在觀察事物時所采取的角度和主觀的目的性等主要因素的影響,從而對同一事物的闡述就衍生出了諸多義項。簡單說來,離散性的事物和連續性的物質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簡單的、自然的視覺關系。Lakoff提出這樣一種假設:有一群奶牛,如果你在近處觀察的話,能夠分辨出每一頭奶牛的個體,你看見的是一個包含具有離散性特個體的群體,所以看到的這些生物就用cows表示。隨后設想你走到遠一些的地方,在你無法分辨出每個奶牛的個體的時候,你的眼前只是一團連續性的物質,則這種生物便用cow表示。這種認知基礎就是最簡單的視覺的體驗,就是我們在使用語言時區分離散性事物和連續性物質的第一根據,此處產生模糊性的根源就是主體觀察奶牛時候的出發點是奶牛的離散性還是連續性。另外,我們既可以把大米看作是一個單獨的、有界的結構,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集合中的一個成分。如此推理,在語言使用中對個體和其集合可以有不同的領悟方式,這邊產生了模糊性。以上的例子反映了我們的認知能力處于不同層次的時候,所起的作用也不同。關注單獨的構成成分時語言體現的是離散性;而進入一個更高組織層次上,當關注大量的這種構成成分時,語言突出體現出來的則是一定的連續性。
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模糊性的產生不是因為所表達的事物本身是離散性的還是連續性的,而是說話人這個主體把客體事物看作是離散性的還是連續性的。例如,具有連續性的物質一般由不可數名詞表示,而在特定的主觀和客觀條件下,人們的認知體驗決定了不可數名詞體現的連續性。換言之,在我們使用語言的時候,主體說話人有意或無意忽略了個體間的差異而把它們看作是同一集合的事物,進而用同一個不可數名詞來描述各構成成分的共有特征,將其劃分入同一個集合體內(例如,把男孩和女孩看作是一個集合體內的成分,都用child描述)。
在語詞中把客觀事物歸類為離散性的或者是連續性的集合,是人的一種基本的認知能力的結果。所以,客觀事物本身具有離散性或者連續性不會導致在語言的使用中事物被描述成離散性的還是連續性的特質。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也可以明了客觀世界本身存在著混沌狀態的特征,所以也不會有一個特定的范疇標準來幫助人確定事物的離散或者連續性。Langacker將這種基本的認知能力定義為construa1(識解),這種基本能力能夠幫助我們根據自己的心理體驗從不同角度去認識和理解同一個情景。正是由于這種能力的作用,我們在語言使用中可以把同一個事物有時表達為離散性的,有時表達為連續性的。簡而言之,語言中的模糊現象恰恰也來源于此。
就本研究進一步而言,由主體認知模糊反之驗證離散性與連續性的密切關系也可得出相互契合的結論。人類語言具有結構的二層性,可以以有限的單位組成無限的句子,人類語言也具有開放性,它是一種開放系統,雖然音位數量有限,可是經組合與替換,可以構成無限的句子。開放性還體現在語言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不斷產生新詞,吸收外民族的詞語,一些社會現象的消失,語言中相應的詞也隱匿或消失。所以,語言在遵循著混沌理論的規則不斷發展、演變,單純的把語言歸入離散性或連續性的方法并不科學。
綜上所述,我們只有看到語言模糊性與人類認知的關系,以及這種認知形式化為詞語的過程特點,我們才有可能更加深入的探究語言模糊性的根源。“模糊性在本質上是客觀的,但又包含一定的主觀的成分。”語言中的模糊性是由于人的認知能力所導致出現的一種特質。
參考文獻:
[1] 錢冠連.語言全息律[J].外語與外語教學,1998,(8).
[2] 王存臻,嚴春友.宇宙全息統一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
[3] 張公瑾. 渾沌學與語言研究[J]語言教學與研究, 1997,(03) .
[4]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5] Taylor, J.R. Cognitive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Langacker, R. W.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New York: Moutonde Gruyter, 1999.
[7] Langacker, R. W. Metonymy in grammar [J].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