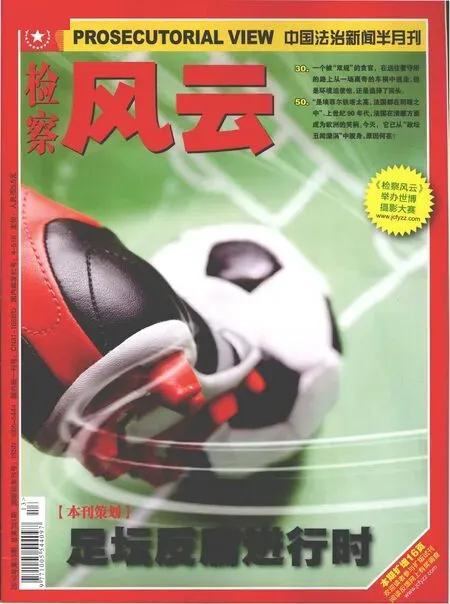中國經濟到底缺什么 與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一席談
文/朱敏
中國經濟到底缺什么 與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一席談
文/朱敏

朱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導刊總編輯,工商管理博士
前不久,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所著《陳志武說中國經濟》和我的《中國經濟缺什么》兩部經濟專著由同一家出版機構同步上市,而此時他又歸國巡講。趁此機會,我們探討了中國一些經濟熱點問題,以及如何借鑒英美金融監管做法的問題。
創新與監管
就在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后,國內有些人認為,中國比西方將更快走出危機、更快實現復蘇。遺憾的是,正因現有經濟模式下的增長來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國人易于虛妄,不去研究一些實質性的問題。
對此,陳志武也是有所擔慮的。這位求學和執教于大洋彼岸的知名華人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接下來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機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礎性、更加重要的工作。
“我最近接觸一些中高層人士,發現有的已經開始飄飄然了,”陳志武坦言,“對他們講法治和科學,無疑是對牛彈琴。許多人開始對美國經濟危機幸災樂禍,但他們忽略了美國制度的修復能力。美國之所以成長為世界超級大國絕不是偶然,背后的制度依賴,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告誡國人,不要以為奧巴馬在走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從長遠來看,所有發達國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競爭的結果。美國雖然在上世紀30年代實行羅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經濟危機,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總統時就逐漸放松了管制,克林頓在90年代總體上沒有強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國真正最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自主創業輝煌期。
應當說,英國當年也是因為實行自由經濟才推動了18世紀、19世紀的繁榮,但今天的現狀卻很遺憾,原因何在?
陳志武表示,最近一項研究發現,英國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當于所有交易量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業。原來,英國在“一戰”和“二戰”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國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稅,這比現在中國的還要高得多。這些政策使得二戰后英國的資本市場停滯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漸被美國所超越。
從各國的發展經歷來看,陳志武的結論是:“政府管制得越多,越會損害一個國家的發展活力和新經濟的推進。”
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銀行界為了生存和發展,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所導致的缺陷進行了深刻反思,并開始想方設法避開分業經營的法律障礙,通過兼并投資銀行和金融創新等手段向證券業滲透。
與此同時,美國金融界開展了由商業銀行發起、證券業與保險業隨后加入,游說美國政府和議會的活動,要求取消跨業經營限制,修改直至廢除該法案,最終獲得了成功。
當然,也有許多人認為,廢除這個法案帶來的問題也很大。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就好像一枚硬幣的不同兩面。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后,美國國會又先后頒布了《1934年證券交易法》、《1940年投資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從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業經營制度的基本框架。這一系列舉措,使得之后十年,美國的金融創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世界制造業經濟的業務逐漸轉移到中國之后,對美國經濟帶來了許多挑戰,逼迫美國的經濟結構開始調整,經濟重心開始放到金融、技術創新和銷售市場。上述制度架構的改革對于美國強化經濟競爭的優勢,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所以,在陳志武看來,這次金融危機不能問罪于美國的經濟創新制度,否則未來10年的經濟增長點更加是一個問號,更將失去應有的創新活力。
“重新讓美國回到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是不現實的,因為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沒法和發展中國家競爭。”他認為,這次金融危機又出現了跨行業的經營,完全放開之后,所帶來的交易鏈條的不斷延伸,由此導致道德風險和委托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這次危機及時暴露了問題,在更大意義上說不是壞事”。
辨析“復蘇”背后
中國經濟率先復蘇,已成全球亮點。
不過,以房地產為例,有研究者表明,“地王”基本上都是國企或有國企背景的地產商在炒;而陳志武也表示,中國經濟復蘇的代價很大。
那么,判斷經濟是否復蘇的標準,究竟是什么呢?
在陳志武看來,評判復蘇與否,更多的還是依賴官方的GDP的數據。“盡管大家都知道背后有些水分,包括地方政府出于政績方面的壓力,而不斷往數據中注水、做一些手腳。但是從一些硬指標看,4萬億刺激方案和7萬億天量貸款,肯定可以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項目中,短期內制造一些GDP。所以總體上說,確實存在經濟復蘇跡象。”
對于短期依賴天量信貸刺激經濟,陳志武認為“起碼在結構上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有一點突出的問題,就是這7萬多億貸款的去向”。
在他看來,大量的信貸主要是支撐那些大中型國有企業和大型民企集團,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各種“鐵公基”的項目,這些對整個社會而言,包括老百姓的收入和就業,皆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市場經濟本身也會遭受破壞,許多民企由此要戴上“紅帽子”。
而最致命的是,把國內有限的資源投到“鐵公基”項目之后,必然使大量中小企業能夠得到的資金更少,民營經濟將進一步陷入困境。這些中小企業,給中國非農就業的貢獻超過了四分之三,即75%左右。
所以,當天量資金投到這些不創造就業機會的大項目后,就業機會的創造性將受到根本性的破壞。一旦就業機會增長下滑,就意味著老百姓的收入下降了;雖然就業機會增長在下滑,但是就業需求還在增長,每年有1000多萬人的新增就業隊伍。這使得就業市場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加劇。
“我們都知道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原理,即供大于求的時候,價格會下降,這就意味著,以后勞動力的價格上漲和收入上漲的壓力等于零,下降的壓力卻在增加。這就是為什么說此次信貸的過度寬松以及4萬億的刺激方案,負面影響非常大的原因。”陳志武說。
“據我了解,像一些外資企業,金融危機以來所公布的銷售數據都存在虛假成分,因為出于某方面的壓力,提倡信心就是黃金,真實數據被公布出來的話,不是打擊信心嘛?這個是蠻好玩的一件事。”
其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華經營的外資企業,按公布的數據來看,似乎普遍都不如國內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
“這背后也讓我感覺到,一些企業增長的水分還是比較多,否則,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都在中國做業務,差別怎么會那么大?外資企業都是負增長,國內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都是高速的正增長。我覺得,從另外一個側面,也反映了政府數據的問題。”陳志武說道。
熱點問題對話
朱敏:打破對過去經濟模式的依賴,唯一的出路或選擇,就是制度上的改良。您認為要紓解內需之乏,應著力于哪個點上?
陳志武:尤其是要控制稅收的增長。特別是2009年,據報道6月份全國財政稅收同期增長了將近20%;7月份的財政稅收,還是增長了10%以上。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之下,稅收還繼續按照這種速度增長的話,這是不可原諒的。
據我了解,其中一個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地稅局和相關部門,給當地企業施加壓力,要求把下一年的稅賦提前上交,這是一個極其糟糕的、破壞性的舉措。為了追求稅收增長率,不惜殺雞取卵,要求民營企業將好不容易賺到的一些錢提前繳公,等于把民營企業逼到了死胡同。從長遠來說,對中國經濟的活力、對老百姓的就業機會的增加,都是根本性的打擊。
朱敏:談起就業,就涉及收入問題。為什么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總是慢于GDP的增速?為什么普通人能夠感受得到的經濟增長沒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就像您另一本書的書名所揭示的:為什么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
陳志武:第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個是國家財政稅收太多,特別是最近十幾年,政府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大餡餅中分到的國民收入越來越大。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有資產的升值都轉移到了國家手中,卻沒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因此,我覺得所謂9.8%的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和其他方面的數據是不一致的。就像剛才所說,如果勞動力就業市場供給不出現根本性增加的話,在需求遠遠大于供給的前提之下,勞動力的價格不可能出現快速上升。從這些大的宏觀數據可以看出,可支配收入增長了9.8%,可信度不是太高。
編輯:陳暢鳴 charmingchin@163.com
我本人對人類的歷史演變的進程,以及具體國家,包括中國的歷史非常感興趣。中國以后的發展會跟發達國家一樣,最后也會實現基于民主憲政的法治社會。
——陳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