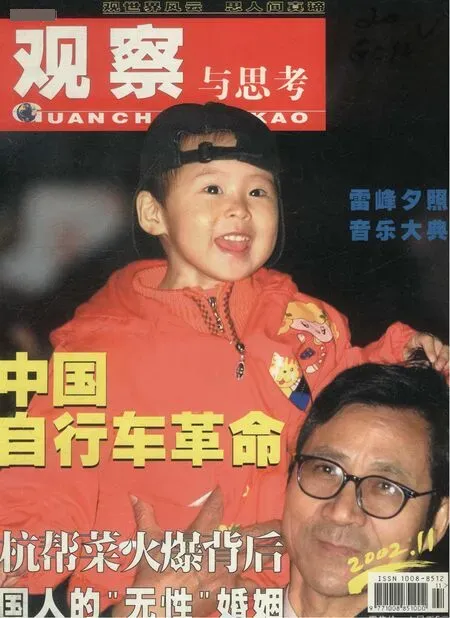農轉居,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部
■秦均平
農轉居,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部
■秦均平
在很長的時期里,人們包括學者們也認為,只要戶籍轉變成了居民,就是實現了城市化。從人口統計、行政管理等角度的確如此。然而,由于多種原因,農轉居問題遠比人們想象得要復雜得多,并不是簡單的戶籍改變所能解決的。
進入城市生活曾是人們的向往,甚至于是夢想。亞里士多德說:“人們為了生活來到城市,為了活得更好而留于城市”。在很長的時期里,人們包括學者們也認為,只要戶籍轉變成了居民,就是實現了城市化。從人口統計、行政管理等角度的確如此。然而,由于多種原因,農轉居問題遠比人們想象得要復雜得多,并不是簡單的戶籍改變所能解決的。
農民轉居民后的就業問題
農轉居勞動力就業困難。由于農轉居的勞動力普遍文化程度偏低、年齡偏大、勞動技能偏弱,在勞動力市場擇業難度大,農轉居勞動力的失業率相對偏高。同時“小富即安”的農民意識,也制約了農轉居勞動力的就業愿望,有的村民依靠原來每月能享受的幾百元福利收入勉強生活,對擇業崗位較為挑剔,寧可閑居在家,不愿從事勞動管理較嚴的工作。在我們的調查中,2008年農轉居新市民群體的下崗失業率達到8%,明顯高于杭州市的平均水平。
即使是就業者,在職業分層結構中也比較低。農轉居新市民群體專業技術人員只占4%,干部及行政人員占17%,相應地,工人占到了27%(見圖1)。
在自然狀態下的城市化,人口的轉移、非農就業是同步的。城市化的過程本身具有的選擇機制,使得那些文化程度較高,或有一技之長、素質較好的,并且適合城市就業的人遷往城市,使不適合者,或不愿意在城市就業者留在農村,繼續傳統的產業。而農轉居新市民群體在農轉居前已經基本失去了土地,迫使他們全部要非農就業。農轉居時不得不實行整體性轉移,個人不能選擇,但是城市的就業又沒有放棄選擇,因而出現個人與就業之間的錯位,增加了就業的難度。
影響農轉居人們就業的的重要原因除了前文已經提到的原因外,農轉居新市民群體文化程度偏低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小學文化的占15.6%,初中文化的占37.7%,高中文化的占18.9%,三項之和達到72%以上。有中專文化的占4.8%,大學專科文化的占17.9%,大學以上文化的僅占4.4%。文化程度低,有專業特長的人少,因此在就業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
農轉居社區建設滿意度不高
農轉居社區建設,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如上下水管網、電網等,從理論上說,應該是城市建設的一部分,應當與其它城市社區同樣由政府及相關部門按城市建設投資,而且也的確有相應的政策規定。但在實際執行中,往往由于傳統的思想觀念及部門利益的驅動,得不到落實,致使一些農轉居新市民群體對社區的環境、治安、衛生、綠化和道路等滿意程度不是太高。調查顯示,對上述項表示滿意和較滿意的在60%左右,認為一般的在35%左右。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滿意率還是相當多的農轉居社區自己從集體經濟中投入了較多的資金。

社區服務有困難。調查發現,成建制撤村建居后的新建居民委員會,多數是由原來的村民委員會翻牌而來,基本套用了原來行政村的管理模式,有的村民至今仍習慣將其當成村干部,削弱了撤村建居的工作效果。從撤村建居的現狀看,按2000—3000戶的規模組建社區居民委員會的為數不多。現在大多數撤村建居的居民委員會的戶數在300—800戶之間,財政給社區劃拔經費按居民數核算,即使給予適當的照顧,總經費也明顯低于老的社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委會的工件,影響了社區建設。實際上,這些新建社區與老的社區相比,工作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原因在于這些社區都有大量的外來人口,外來人口的服務不能少,工作經費卻沒有。
集體經濟發展較慢
農轉居社區的集體經濟是一個非常敏感且涉及面很廣的問題。它既涉及以原來村集體經濟的管理,又有改居過程中的量化到個人,還包括農改居后的集體經濟發展,財產、資金的管理并不斷增值。集體資產量化后管理的難度較大。據調查反映,集體資產(資金)的量化涉及到人員界定、時間界定及公益分配等諸多因素,工作量大,政策性很強。現在大多數采用的方法,一是撤一村建一居,原村兩委(村民習慣稱兩委即黨支部或黨委、村民委員會,實際還應增加上經濟合作組織的管理委員會,是三委,以下仍稱兩委)的干部班子人員不變;二是管轄范圍及對象不變,原村級組織的管理職能、權力義務整體移交新的居民委員會;三是集體資產不變,原村集體經濟性質不變,村級集體所有的資產(包括債權債務)全部劃歸新建立的居委會所有;四是原村福利待遇的享有對象和政策不變;五是原村兩委會制定的各類政策及對外簽訂的各類經濟合同均延續不變。即“五不變”。“五不變”辦法只是權宜之計,若長期拖而不決,村民變股東后對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仍不放心,有的干部也認為依靠股份合作制經營集體資產,依然存在流失的隱患,若處理不好,也可能產生新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目前集體經濟的發展大都以房租為主,經營中多數求穩,發展比較慢,有的居民有意見。但是如果冒較大風險經營,又擔心引起更大問題。雖然在理論上,甚至于在政策上黨組織、行政組織和經濟組織的產生方式及其功能區分都是很清楚的,但在實際上,交叉兼職又是比較普遍的,如果處理得不好,出現決策失誤等問題將是難以避免的。
新型“租金食利階層”
農轉居新市民群體的經濟收入大多數都比較高。他們不僅高于外來的“無村籍”的打工者,也遠非普通的市民工薪階層可以望其項背。據調查,月收入超過10000元的超過了11%,超過5000元低于10000元的達到21.5%,超過3000元低于5000元的達到32%,低于1000元的只有7.7%。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房屋出租的收入占的比重比較大,占收入的44.3%(見圖3)。有的“村民”,完全依靠房屋出租收入過著悠閑的日子,成為新型的“租金食利階層”。即便是“村民”自己住宅的鋪面,有的也都租給別人經營,自己只是按月收房租。較高的收入和較多的空閑時間,既可以提高生活品質,提高個人的素質,從事文化、科技等活動以增加對社會的貢獻,也可能是社會穩定的不利因素,即人們平常所說的“無事生非”。
農轉居新市民群體正在引發一系列重要的社會變遷。在變遷過程中,出現了值得注意的群體分化現象,給市民化進程帶來復雜的社會后果。
農轉居對居民生活影響不顯著
一般說來,某件事物對人們越有積極的影響,人們就越多地持肯定態度。調查所知,村轉居對居民生活影響并不是很顯著。調查對象中有55%的人認為農轉居對他的生活沒有影響,25%的人認為農轉居對他的生活稍有影響,只有20%的人認為有影響(見圖4)。
村轉居如果對居民的生活有影響,那么是何種影響。43.6%的被調查者認為,村轉居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44%的被調查者認為差不多,還有3%的被調查者認為變得更不好。可見,居民的對農轉居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評價并不高。
制度的社區與現實的村莊

撤村建居實現了由農村向城市的轉變,戶籍也由農民轉變成了居民,從而在制度層面上實現了城市化。然而,現實中這類社區仍然保留著明顯的村莊特征。村莊是一個以血緣、親緣、宗緣、地緣等社會關系網絡構成的生活共同體。農轉居新市民群體雖然在制度上已經市民化了,即使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非常城市化了,但原有的社會關系網絡并沒有因此而發生斷裂,沒有城市化。“村落社區”與城市的“街道社區”和“單位社區”都有很大的差異,它不是一個由陌生人構成的生活共同體(如街道和物業小區),也不是一個僅僅由于業緣關系而構成的熟人社區(如單位宿舍大院),而是一個由原來的村民組成的由血緣、親緣、宗緣和地緣關系結成的傳統的互識社會。據調查, 農轉居新市民群體中原社區的居民占到89%(見圖5)。農轉居新市民群體的戶口也同樣以本社區占絕大多數, 占到89%以上。制度的社區與現實的村莊問題會影響到諸如人際關系、包括兩委干部選舉等問題。這是其它老的社區所不存在的。
被動城市化衍生的被剝奪心理
村改居前的“城中村”是二元體制下城市化過程中“要地不要人”的政策選擇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農村居民的剝奪結果。而村改居又是在政府主導下自上而下實施的,不同于以往城市化中人口遷移,產業發展和人們的非農就業而同步發生。人們要實現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夢想,是要經過艱苦奮斗的,是主動的城市化。與此相比較,農轉居新市民群體的城市化卻是被動的城市化。首先,土地征用是被動的,由此產生了被剝奪感。其次,即使當年土地征用給予了相當多的土地補償,但是當周邊土地升值后又有了新的補償標準,便會以當前的新標準與當時的標準進行比較。因而,在調研中我們常常聽到的反映是,當年給的土地補償是多少,現在的是多少,或者政府征用后出售時是多少,由此產生了心理極大的不平衡。被剝奪心理幾乎成了農轉居新市民群體的心結。
外來人口聚居引發的種種問題
農轉居社區是大量的外來人口的聚居地,大量的外來人口又是農轉居新市民群體出租房屋、增加收入的重要目標人群。兩者相互依存,又往往產生各種矛盾,引發諸如經濟糾紛、治安事件、環境衛生等多種問題。
(此專欄由本刊與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