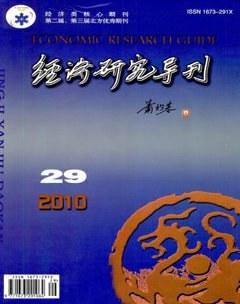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管理的理論依據與現實途徑
柯 燕
摘要:隨著經濟社會轉型的加速,公共危機事件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的不利因素。非政府組織作為一種制度創新,可以有效彌補政府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失靈和不足。從治理理論、危機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的角度,研究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的理論依據和現實途徑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非政府組織;公共危機管理;理論依據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9-0171-02
引言
2004年12月,印度尼西亞地震引發大海嘯,大量國際非政府組織迅速參與到救援工作中。在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聯合會呼吁國際社會提供600多萬美元的“即刻援助”,幫助了大約50萬幸存者。國際“無國界醫生組織”用飛機向最接近震中的印度尼西亞蘇門達臘島運送去32噸的醫療和衛生物資。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社會和受災國政府等在救援工作中緊密配合,行動統一,使得聯合國負責人道救援事務的副秘書長揚·埃格蘭不得不贊嘆,這是人類迄今對重大自然災害所作出的“最為有效的應急反應” 。而在我國2003年的“非典危機”中涌現了大量草根非政府組織,為危機的及時化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非典”事件后,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獨特優勢逐漸引起我國學術界的關注,且在危機主體方面形成了區別于“政府主體論”的“資源整合論”,強調在發揮政府作用的同時,要調動社會組織在危機管理中的積極性。有學者認為,應該促進各類非政府組織的正常發展和能力構建,增強公民的自組織能力,以便在危急時刻充分利用非政府組織的資源,及時有效地自救和救助別人。 還有學者認為,中國應該大力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增強其自治性,健全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法律政策環境,推動公民參與和志愿組織建設,并逐漸建立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互補、合作的良性伙伴關系,以適應向現代治理結構轉型的發展趨勢。總的來說,目前國內相關研究的現實性較強、理論性相對薄弱。研究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管理的理論依據和現實途徑,具有彌補以往研究不足的重要意義。
一、非政府組織與社會公眾參與公共危機管理的理論依據
(一)治理理論
治理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西方國家和一些國際性組織中興起的,西方學者提出治理概念,并主張用治理代替統治,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存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治理理論打破了管理公共事務的傳統觀念,建立多元主體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石。全球治理委員會在1996年發表的《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報告中,對治理做出了相對權威的界定: 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 。治理理論打破了國家和社會二元對立的格局,強調了各種公共事務中民間組織的參與,強調了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與合作。具體而言,治理理論強調了以下幾點。
1.治理理論意味著,政府并非公共危機管理的唯一主體,社會組織及公民也能成為治理危機的中堅力量。傳統觀點強調政府是危機管理的主要責任者,危機處理的成敗取決于政府的決策機制是否健全。然而,治理理論強調了各種非政府組織和私人機構都可以在危機處理中成為權力中心,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行動,達到增進公共利益的目的。
2.治理理論意味著,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存在權力的讓渡。國家正在將以往獨自承擔的責任轉移給第三部門和公民社會。各種非政府組織和志愿者團體將越來越多地承擔公共管理領域的職能。
3.治理理論強調在危機治理的主體之間需要相互依賴與合作。即在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之間要及時溝通,交換資源。危機處理的成敗取決于三方的合作,而非單方努力的結果。這個意義上的危機管理“不再是監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權,而是權力分散;不再是由國家進行再分配,而是國家只負責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門的管理,而是根據市場原則的管理;不再是由國家‘指導,而是由國家和私營部門合作” 。
(二)哈貝馬斯的“危機理論”
哈貝馬斯將危機定義為這樣一種情境:一個系統無法產生足夠的可交換資源,以滿足其他系統的期待或需求。 目前存在的四種危機類型以及其源起和轉移模式是:(1)經濟危機,即國家由于承擔了越來越多的針對調控、保護、提供基礎設施以及公共部門生產的責任,而產生危機;(2)理性危機,即“政府預算負擔著日益社會化的生產的公共支出”而產生的危機;(3)合法性危機,即如果國家對民眾福利支付的需求超出了實際可能的資源,那么帶來國家合法性的危機;(4)動機危機,是由合法性危機導致的社會共同體整合不良的危機。由于公共危機涉及國家、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一旦發生則需要大量的人、財、物等資源予以支持和化解,單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應對。在哈貝馬斯看來,要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機,出路在于讓自發、非政治化的社會有機體健康發展起來,第三部門可部分釋放政府的合法性危機。 危機理論指出了政府在應對公共事務的不足以及可能產生的危機,強調了非政府組織在化解政府危機中的特殊功能。應對公共危機的各種資源一般分布廣泛,而公共管理系統在短時間內如不能調動各種資源進行支持,快速遏止危機,往往會引發政府自身的危機。而解決這一難題的有效途徑就是讓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公眾參與到危機管理中,最大限度地調動全社會的力量,不僅可以提高應對危機的效率,而且能有效化解政府失靈帶來的雙重危機。
(三)社會資本理論
當代第一個對社會資本理論進行系統論述的是布迪厄,他認為,“社會資本是真實的和虛擬的總和,通過相互熟悉與承認的人之間或多或少制度化的持久的關系網絡,來增進個體或群體的利益。” 布迪厄將社會資本視為一個群體成員的集體財產,人們由此相互認可和交換資源。研究發現,在危機中,“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都會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但相對而言,平時最不顯眼的社會資本遭受的損失最少。因而社會資本是應對公共危機的有效工具。另一個從群體層面研究社會資本的代表人物是普特南,他指出,“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征,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可以通過促進、協調行動而增進社會的效率” 。普特南認為,社會性團體和參與程度反映了一個社會中的社會資本范圍,它們也促進和增強了集體的規范和信任,這對集體福利的生產和維持是至關重要的。根據社會資本理論,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管理的積極作用有以下幾點:
1.減少信息不對稱,穩定民心。危機事件發生后,人們的本能反應是千方百計地尋找與事件有關的任何消息。而由此產生的謠言和恐慌會給社會帶來比危機本身更大的威脅。非政府組織擁有的社會網絡、信任和規范能使正確的信息在成員之間快速有效的傳播,達到遏止流言,穩定民心的作用。例如,在“非典”時期,不僅可以通過非政府組織向社會公眾講解風險的真實面目,還可以通過非政府組織向社會公眾講解行動常識、講解國家的政策,從而使他們能冷靜有效地面對危機。
2.優化資源分配,增進社會效率。在不同網絡之間,由于網絡的性質不同以及其社會資本的存量不同,社會資源并非均勻分布。解決的辦法是把不同的網絡連接起來形成更大的社會資本網絡,增大社會資本的受益面。非政府組織參與危機管理,可以將其所擁有的不同資源進行互換和共享,達到優化資源分配,增進社會效率的目的。
3.促進社會融合,培養公民意識。社會資本的關鍵特性是促進聯合成員為共同的利益進行協調與合作。在一個公眾參與程度高、社會資本豐富的社區,公益事業就會興旺發達。非政府組織是個人基于共同信仰、興趣、愛好或意志自愿結成的,并通過各種自主、自愿的活動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期望和價值追求,在這種自由結社和自我管理的社會生活中就會逐漸養成公平、平等、權利和自由等理念。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非政府組織將這種理念滲透到社會成員之間的橫向交流與合作中,培育了廣泛的互惠規范和社會信任關系,進而為全社會提供了道德規范;與此同時,也發展和促進了信任、團結、互助的價值觀,培養了公民意識和志愿者精神,進而為應對危機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
二、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管理的實現途徑
1.加強立法,提供法律保障
首先,要加強非政府組織立法,為非政府的良性運行與發展提供法律保障。政府應根據實際情況對非營利組織的性質地位、作用、權利與義務等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逐步形成配套的、不同層次的法律法規體系,使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管理有法可依。一方面,非政府組織只有在法律上取得合法性,才能得到社會成員的認可,并有效地參與公共危機的管理中;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只有依靠法律、法規定位和行事,才能在組織內部形成自治性規范,培養成員的自律精神,進而在全社會培養公民意識和志愿者精神。
2.合理定位,確保獨立功能
在公共事務的多元治理結構中,應將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領導與從屬的支配關系轉為平等合作的伙伴關系。政府可以采取邀請、授權、委托等方式與非政府組織建立起聯合治理的格局,將政府權力回撤的“治理真空”交給非政府組織管理,確保非政府組織獨立自主地參與公共危機事務的管理。與此同時,政府要強化對非政府組織的監督與管理,確保其合法規范地運作。
3.加強建設,提高整體素質
非營利組織要得到健康發展,必須加強組織能力建設,提高整體素質。根據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現狀,首先,要提高成員素質,吸引高素質專業管理人才;建立多元化的資金籌資渠道,為非營利組織開展各種活動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其次,要加強內部管理,實行民辦民管,逐步形成民間組織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機制;最后,非營利組織不僅要健康良性發展,還要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包括組織的活動能力、組織和管理能力、資金籌措和運作能力等。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其重建社會資本的作用,參與公共危機的管理。
參考文獻:
[1] 鄭安云. 試論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J].理論導刊,2008,(2):39-41.
[2] 彭宗超.非典危機中的民眾脆弱性分析[J].清華大學學報,2003,(4):25-31.
[3] 賈西津.透視公民社會的治理機制[J].中國審計,2003,(Z1):11-14.
[4] 全球治理委員會.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M]. (Our Global Neighborhood),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2-3.
[5] 弗朗索瓦-格扎維爾·梅理安.治理問題與現代福利國家[J].國際社會科學,1999,(2).
[6] 馬爾科姆·沃特斯著.現代社會學理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7] 吳東民,董西明.非政府組織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8] 莫洛·F.紀廉,等.新經濟社會學——一門新興學科的發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9] 李蕙斌 楊雪冬. 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