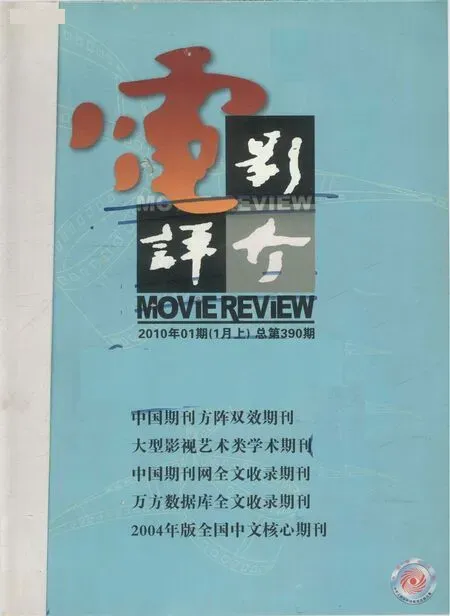文明與人性的詩意之思
2003年的西班牙評論之眼小說獎頒給了《冷皮》的作者阿爾韋特?桑切斯?皮尼奧爾(Albert Sánchez Pinol)。該書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翻譯之后,在沒有靠任何機構的幫助下,就能很快贏得世界聲譽并獲此殊榮,實在難能可貴。作為人類學家的皮尼奧爾第一次寫長篇就引發二十四個國家的讀者的思考,足見這位學者型作家深刻的敘事魅力和思想感召力。
跟不大喜歡社交的書齋小說家奧爾罕?帕慕克很相似,皮尼奧爾是一位不喜歡顯山露水,不喜歡拋頭露面,而且不茍言笑的嚴肅作家。但卻跟他的作品一樣,他是一個真誠的人,從不裝腔作勢。《冷皮》這部小說的情節雖然十分驚心動魄,但小說家并沒有把色彩絢爛的敘事技巧作為表現這則令人迷醉的寓言的重要途徑。他是直接把這個島上每一天發生的事情整整齊齊地娓娓道來。整部小說給讀者一次質樸坦誠的心靈震撼。
如果有人把皮尼奧爾的《冷皮》用一幅超現實主義畫畫出來,那么畫面中一定包括這樣的場景:兩個人、一座孤島、一座燈塔、一本弗雷澤的《金枝》、一艘沉船、一場人與怪物無休止的戰爭。這是一次人性、獸性與文明交相輝映的哲學實驗。就像人類的戰爭從來沒有真正停歇過一樣,在這個孤島上,循環演繹著同一個恐懼、孤獨、顫栗、野蠻的主題。
“我”曾是一名對愛爾蘭革命事業失望的激進分子。在對生命抱著永遠漂泊的信念之后,被國際航海協會委派到一個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小孤島上進行氣象測量工作。入住的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令“我”驚恐萬分的事情,一群怪物瘋狂地攻擊“我”的住所。而不愿跟“我”交流的“原住民”巴蒂斯住在燈塔上,冷漠地不愿伸出任何一只援助之手。瀕臨精神崩潰的“我”在與怪物斗爭了三四天后,終于挾持了巴蒂斯馴養的奴隸女娃臉怪,才取得了與巴蒂斯同住在燈塔上并肩作戰的機會。此后,“我”和巴蒂斯發揮聰明才智,與娃臉怪斗智斗勇,甚至把沉船里的硝化甘油取上岸,試圖制成炸藥以便一勞永逸地炸死不斷進攻的娃臉怪,讓它們喪失信心,不做無謂的犧牲。在這期間,“我”深深地愛上了勾魂攝魄的女娃臉怪,并與其多次偷偷做愛。女娃臉怪的一次不經意的行為突然讓“我”有所醒悟,“我”從此認為娃臉怪并不是原先以為的那么冷酷無情。“我”開始與小娃臉怪們接觸,并與失去雙親的小娃臉怪三角產生了深厚的友誼。然而,巴蒂斯始終不與“我”合作,還喪心病狂地破壞了我的一切努力。最后他們的爆炸威懾并沒有讓怪物們停止攻擊,精神崩潰、失去理智的巴蒂斯最終死于娃臉怪的攻擊。巴蒂斯死后“我”幾乎變成了第二個巴蒂斯,“我”開始在醉酒之后,脾氣暴躁地虐待女娃臉怪。就在這個時候,島上上來人了,而“我”對他們的反應就如同當時巴蒂斯對“我”的反應一樣,一言不發。而這個新來的氣象員也同我當初一樣,在第一天晚上就受到娃臉怪的攻擊。在一夜間,新來的氣象員從中產階級模樣變成賤民的模樣。似乎一切都從一年前開始,一切都是一個循環。
《冷皮》是一部實驗小說,也是一部科學幻想小說,更是一部哲學幻想小說。就像做實驗必須控制許多參數和影響因子一樣,作者把人類的文明放置在這座孤島上構造一個微型社會。實驗表明,從西方帶來的文明很快就湮沒在與怪物的對抗中。這部小說開始和結束有著非常相似的情節。從歐洲來的新人面對躺在燈塔里的孤島人,提出從歐洲大陸的文明社會帶來的許多問題,在孤島人身上沒有激起任何漣漪和回答。比如,提供保護資產的信息、審判、失蹤的負責、控告、高尚智能的原理書籍,這些文明社會的關鍵詞不能引起巴蒂斯,以及后來變成第二個巴蒂斯的“我”的任何興趣。就連島上唯一的一本書弗雷澤的《金枝》,巴蒂斯也從來沒有看過。而基輔大學的生物實驗、柏林地理協會要求的搖蚊科海蠅、法國公司的礦物研究、天主教傳教士的問卷調查,尤其是“我”作為氣象觀測員的工作,與后來跟娃臉怪的殊死搏斗相比,與整部小說的驚心動魄的生命之重相比,顯得那么的輕飄、可笑、荒謬、嘲諷。作家皮尼奧爾并沒有如同笛福一樣把獲得食物之艱難放在故事表現的重要位置上。恰恰相反,幾近諷刺的是,文明社會發明的子彈和炸藥卻在這里成為生存的必需品。于此,野蠻與文明的撞擊形成了讓人沉思的裂口。
實際上,這一切反差的關捩點,我們可以從“我”把一切問題都退歸到一個死亡的話題上管窺:那就是,要讓自己的恐懼不至于壓得“我”無法抬頭,正如“我”的心思所言,“我很快就會死,臨死之前,道德僅僅是路上揚起的灰塵罷了。”[1]在死亡的恐懼面前,人是很容易沖破一切的道德和一切的倫理的界限的。為了壓倒自己內心的絕望與恐懼帶來的不安,兩個男人最終不約而同地把自己的壓力轉移到對女娃臉怪身體的占有和虐待壓迫上。
兩個男人對女娃臉怪的攻擊和壓迫,都在各自的心底起到一種戰俘效應。這種關系一方面象征著人把怪物給他們的痛苦轉嫁到了女娃臉怪身上,另一方面象征著一種對娃臉怪族群的攻擊和侵略上的勝利。我們可以看到,在與女娃臉怪愛恨糾纏的性愛中,長期在島上戰斗而心靈扭曲的人的殘忍在這里展露無遺。起初,“我”以為“我”的溫存會俘虜女娃臉怪的心,而后來,實際上,“我”對女娃臉怪的性虐待在巴蒂斯的基礎上,更加變本加厲。而從巴蒂斯對女娃臉怪來歷模棱兩可的交代中看出,作者似乎是在有意暗示我們,巴蒂斯并不是第一個占有女娃臉怪的人。而國際航海協會每年派一名氣象測量員的事實,也旁證了這一點。
作者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很古老,千余年來一直不斷言說的話題,那就是人性的邪惡和善良。就娃臉怪而言,巴蒂斯的奴隸女娃臉怪以及與“我”親近的小娃臉怪三角等都是給人以弱小、善良、溫順的感覺。而娃臉怪的族群每天晚上瘋狂而殘忍的進攻則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里,作者提示讀者去思考一個問題:個體是一種性格、一種稟性,群體又是另外一種性格和稟性。群體的行動往往容易變得盲目、沖動。群體的力量是無窮的,但是群體的思考能力顯然是不足的。而這種群體性的問題在人類歷史的戰爭中有著最集中的表現,作者在書中曾多次提到許多戰爭理論,作者對戰爭的本性與人性之間的彌合與不足都是有著相當深入的思考的。
就人自己而言,讀了這部小說,似乎一下子就讓人對邪惡是如何造就的,有所感悟。當炸藥把怪物炸得橫尸遍野的之后,看到第二天的日出,巴蒂斯愉快地如同達到性高潮一般。在巴蒂斯這里,不存在任何憐憫、任何同情。因為這里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當娃臉怪攻擊燈塔的時候,不讓怪物滅亡,就只能讓自己滅亡。在生存的本能的驅使下,人只有比怪物更加邪惡,才能活下去。巴蒂斯的死亡是理性變得瘋癲的一種象征,巴蒂斯本來還可以繼續堅持戰斗下去,但是他在一夜又一夜的斗爭中,本來非常懂得自我保護的他卻失去了理智,或許也是出于對自己力量的高估,他奮不顧身地跳進了怪物堆里,很快就湮沒在怪物強大的力量之下,然后四周變得靜悄悄。在人與怪物的大戰中,在怪物始終不渝的戰斗熱情下,巴蒂斯脆弱而勇敢地倒下了。邪惡的結果是自取滅亡,而人在那種環境下,只能變得邪惡。這就是皮尼奧爾給讀者暗示的存在之思。
在《冷皮》里,還有更深一層的象征意蘊:最根本的恐懼來自我們自己的內心。巴蒂斯把自己與娃臉怪用一堵無法逾越的墻隔開,可以猜想怪物的心態跟人類的是一樣,人們之所以稱其為怪物,就是拒絕把彼此放在一個同等的地位上思考問題。如果巴蒂斯面對的怪物象征著人內心深處陰暗的絕望和失落。那么,這里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啟示,我們面對的那些堅信不疑的隔閡和痛楚是否也只是一種想象,或者只是因為我們所采取的視角和操作手段的偏差所導致?這個啟示,在“我”的身上是有明證的,若是用歐洲的文明來衡量女娃臉怪的話,任何標準都將視其為馴養,但是“我”卻發現她是一個女人。可是,不幸的是,她的冷漠卻又讓“我”對她感到失望、麻木。
“我”也曾給巴蒂斯講了一個愛爾蘭人的故事。一個愛爾蘭人獨自在一間黑暗的房間,他摸索著尋找煤油燈。找到了,于是以一根火柴點燃煤油燈。他看到對面的墻壁上有一道門,便迅速地穿過。他忘了帶油燈,因為想再度進入一間漆黑的房間。故事可以一直漫無止境地重復,總是一直往前進,總是面臨一次又一次的黑暗。最后,固執的愛爾蘭人來到一間沒有門的房間,像只被關在籠里的老鼠。他說,感謝主,這是我的最后一根火柴。[2]
“我”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訴巴蒂斯,“我”不想一直在這個孤島與怪物耗下去,直到打完最后一顆子彈后被怪物吞沒,“我”想活下來,“我”想用沉船里的硝化甘油一次性炸死成百上千的怪物。讓它們知道教訓,永遠記住教訓。“我”顯然是想把這種宿命的循環一勞永逸地終結掉。但是很不幸,以暴易暴并沒有打消怪物的進攻,卻讓巴蒂斯變得精神崩潰。努力的失敗,最終讓“我”在這個循環面前低下了高昂的頭。
這部小說的敘事模式讓我們明白,或許這是一個永遠講不完的人類歷史的故事。作者似乎也在警告讀者,這是個永恒的無底深淵。當然,作者也在無意間宣揚了一種歷史循環論的觀點,巴蒂斯之前有許許多多的“巴蒂斯”,巴蒂斯死了之后還會有更多的“巴蒂斯”來守衛這個荒島,最終所有的“巴蒂斯”變得精神失常,然后在永無止境的、看不到頭的戰斗中死去。宿命與悲觀當然是西方文學的一個通病,但這一類作品往往容易發人深省,促使人們思考社會人生。《冷皮》雖然只有二百來頁,但其厚度就同博爾赫斯筆下的《沙之書》一樣,埋藏其中的永恒的話題,始終會引人思接千載。
注釋
[1][西]阿爾韋特?桑切斯?皮尼奧爾著,戴毓芬譯,《冷皮》[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125
[2][西]阿爾韋特?桑切斯?皮尼奧爾著,戴毓芬譯,《冷皮》[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178
[1][西]阿爾韋特?桑切斯?皮尼奧爾著,戴毓芬譯,《冷皮》[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2][意]巴蒂斯塔?莫迪恩著,李樹琴、段素革譯,《哲學人類學》[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3]王南緹,《社會哲學——現代實踐哲學視野中的社會生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