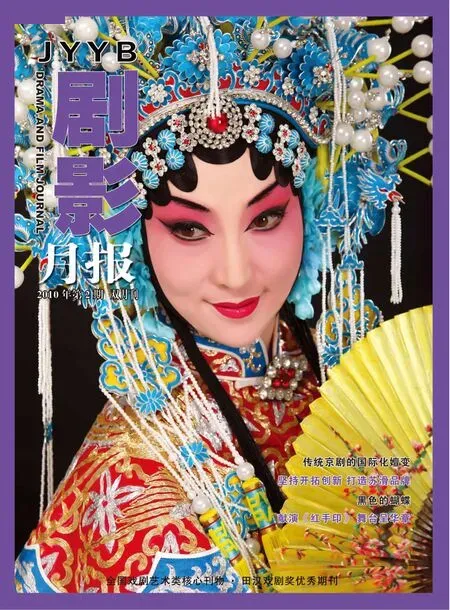學習程腔的幾點體會
■江汁
民國之際的“四大名旦”是旦角表演藝術的一個顛峰,其中,程硯秋先生無疑是最具個性者。程硯秋于“梅派”之外脫穎而出,獨辟蹊徑,自成一派。這也正是程硯秋強烈的“創新”意識使然。
梅派以雍容華貴、絢爛靚麗的表演風格風靡民國以來的菊壇;程硯秋在梅派之外,結合自身的質素,以行腔沉著,頓挫有致,將青衣的表演推向一個新的境界,以此表現卑微女子的身世凄涼和多舛的命運。所以說,如果把梅蘭芳比作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那么,程硯秋則是現實主義詩人杜甫。
(一)
程硯秋談到“程腔”的“演變”,自謙自己“腔調并不特別,更談不到自成一家”,他說:“人家恭維我的腔,都稱為“程腔”,其實我自己自始至終是按著老規矩走,絲毫也不敢越出范圍。我在最初是從王瑤卿等諸位先生學習,因為這幾位都是很有名而老到的。我經他們指導后,即守著這老規矩向前演變,但無論何時,總未越出范圍,不特本人的這樣,就是梅蘭芳先生、楊小樓先生,都是一樣守規律。至于一般人學我的,終未得骨髓的原因是什么呢?在這一點上,我愿特別多說幾句,這里邊最大的關鍵,就是不刻苦,不耐勞,無長性,不重視以上種種毛病,在票友方面犯了還有情可原,因為不受報酬,若以戲劇作營業而仗著吃飯的伶人,那就不會得著觀眾們的原諒了。”
如果談到“程腔”的特點,我想他最善于刻畫人物情感從真實的生活中升華,記得程硯秋談及飾演《青霜劍》一戲時說:“假如我演的雖說是《青霜劍》,而觀眾只看見臺上有個程硯秋,沒有看見什么申雪貞,那就是我不會把申雪貞的人格了解得徹底,所以我還是程硯秋,不會演成一個申雪貞,這樣演員就慘敗了。”
程派的美學境界在于他的深層的哲學思考——對底層人物命運的關注與揭示,契合人物的心理狀態和情感表現,沉郁頓挫的行腔充滿入世情懷,將觀眾的情感帶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作為演員的程硯秋始終堅持進入角色的內心世界,將自己的愛與恨與角色人物息息相關。他不追求嘩眾取寵的噱頭以迎合某些觀眾,而是以聲情并茂的情感去帶動觀眾的情緒。臺上臺下,共同演繹著人生的遭際,所謂“人生看舞臺”。
“程腔”是“程派”藝術的一個重要組織部分,如同中國的寫意畫,充滿沉郁之美,蒼涼樸素并帶著些許的狂狷和超然之氣。杜少陵說:“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臬之流,庶可跂及也。”“程腔”之于“頓挫”,是相;而“沉郁”是其質。無論《荒山淚》、《春閨夢》還是《青霜劍》,程腔與劇中人物心理的完美契合正表現著這一美學的特征。幽咽委婉,蒼涼大樸中益見纏綿細膩,這正是“程腔”既能曠達高揚,以其回腸蕩氣的悱惻悲壯兼有著如山澗流泉、空谷幽蘭之清遠飄逸。故“程腔”能以含蓄內美而體現大樸之境界,絕非“緩步瑤臺”之時尚。程硯秋先生在《鴛鴦冢》中,有一段王五姐的[二黃慢板]“對容光驚疲減,萬恨千愁上眉尖……”幽怨,纏纏,唱腔與聲音的天然結合,達到神妙的境界。
《鎖麟囊》中大段的[二黃]“一剎時……”極易被夸張通俗,而程硯秋則能一波三折,極盡幽咽之曲美,讓我想到中國寫意畫的境界——筆墨的豐富內含之美,如果徐渭的雪中芭蕉和竹石,縱恣超脫而能內斂沉著,筆墨之美和“程腔”的技術處理一樣,到了極致,這種技術便成為一個境界之美,而徒追表相無有扎實的技術層面的嫻熟同樣只能流于淺表,去“程腔”尤遠矣!
(二)
程硯秋骨子里還是具有創新意識的,他繼梅蘭芳之后曾用一年多時間出訪歐洲,對歐洲的戲劇(歌劇)進行考察研究,歸國后,也曾試圖致力于京劇的“改革”,但限于實力(主要經濟)和環境,加上政治時勢的不定,這一美好愿望終未能如愿。
通過歐洲之行的考察,程硯秋對京劇的認識也更深切,他這樣談到中西戲曲的比較:“中國舊日戲劇,全部寫意,亦無布景。降至今日,逐漸加用油畫電光,似為進步之戲劇。究竟,在科學程度幼稚之國家,加以社會日趨困難,營業之人,亦苦資本不足,布景電光有時用,有時不用,有時華麗,有時簡陋,又似弄巧成拙。”
他1933年接受《華北日報》記者訪問時又說:“據德國名導演萊因哈德說:‘中國的舞臺上的布景雖簡而最合舞臺術,劇中寫意的情節及動作,也是我們所應取法的,就以中國的以馬鞭代馬,以槳代船種種動作來說,實比我們騎在木凳上當馬強得多,生動得很了。’萊氏說完,我還做幾個別的寫意的動作給他看,并講明以鞭代馬,以槳代船的好處,他們都點頭稱贊。”
他進一步闡釋:“中國戲劇是不用寫實的布景的。歐洲那壯麗和偉大的寫實布景,終于在科學的考驗之下發現了無可彌縫的缺陷,于是歷來未用過寫實布景的中國劇便為歐洲人所驚奇了。”
談到“改良”,程硯秋先生以為“非得先建筑新式劇院不可,不然哪,什么也先談不到”。可見程硯秋對戲劇的發展是深懷改革使命的。但正因為程硯秋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美學的深刻理解,對西方的親密接觸,才不致于一味“洋化”,追求時尚,迎合時流,所以,他的每一步探索都是極其用心而且是小心翼翼的。
程先生談到唱腔的設計,說“應該按照詞句的意思是悲、是喜,根據詞意創造,萬不能以‘新’腔為主,以詞意劇情為副”我們知道,程先生是一位善學并兼容并取的藝術家,他不僅重視參照西方戲劇藝術,也很重視對地方戲的研究,但他同時也認為:“吸收腔調不能生吞活剝,如果看見越劇好,梅花大鼓好,就搬過來一整段放在京劇里,或者把落子、歌曲大段大段地放在京戲里去;觀眾一定不接受,不承認……”可見,創新并非表面的新花樣。
京劇經過百年探索,經過幾代人的經歷,發展到程硯秋時代已臻至完美,我們今天再遑論創新,首先要清醒地認識到,葆守“原真性”,否則,所謂“原創性”只能是一句空話。弄不好,會對京劇藝術起到破壞的副作用。這正是我們學習程派的后學者應當引起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