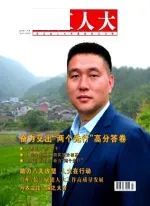嘉興求解“用工荒”
■陳統奎
嘉興求解“用工荒”
■陳統奎
前不久,嘉興市勞動保障局的數字顯示,嘉興勞動力缺口9.5萬人。對比當地擁有100多萬外來勞動力這個“分母”,嘉興市經貿委官員對記者表示:“嘉興沒有出現大范圍用工荒現象。”
與東部其他沿海工業發達城市相比,嘉興的“用工荒”程度屬“中度”,勞動力缺口是1∶2。“嘉興老板很少克扣工人工資,社會治安又好,外來勞工還被尊稱為新居民,這么善待外來勞工,還鬧‘用工荒’,那我們就不能小看‘用工荒’現象了。”《嘉興日報》一位同行如是說。
“量”的復蘇面臨著嚴峻挑戰“,質”的復蘇依舊稀罕
嘉興擁有“一鎮一品”的產業格局,其下轄的桐鄉市濮院鎮是中國最大的羊毛衫生產基地。2010年春節一過,濮院就出現了大面積“用工荒”,羊毛衫企業勞動力缺口近50%,3000多家毛衫企業為招不到足夠的工人而發愁,用工短缺問題以及日益看漲的薪酬,已成為這些賺取微薄代工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一塊“心病”,但“量”的復蘇依然刺激著產能擴張的沖動。
“主要缺操作工,干的活重,時間長,工資待遇不太高。”濮院羊毛衫技術學校校長劉斌功介紹說,從2009年末到2010年春節過后,該校只培訓了100來人,而往年這個數字是800—1000人,“來學的人少了”。劉斌功還發現一個新變化,現在很多男生都喜歡學習一項“套口活”技術,5年前只有12%的男生愿意學習這項技術,現在是80%,“干活輕松,月薪3000元左右”,這說明“新學員在轉型”。
在劉斌功看來,濮院羊毛衫行業操作工短缺原因有三:一是企業老員工轉型當電腦操作工了,由此空出一部分崗位;二是全國羊毛衫工廠遍地開花,一部分轉移到其他地區去了;三是從其他行業轉型來的人,需要培訓才能上崗,但要交學費,他們不愿意學,沒進工廠,沒進培訓學校,又走了。這表明,“量”的復蘇面臨著嚴峻挑戰。事實上,整個嘉興“用工荒”,以技能型崗位缺口為主,達到6.8萬人。
岳姚祥是嘉興成功企業家的代表之一,他是產業轉型的先行者,從傳統皮衣到時裝,從家具項目到高科技項目,經歷過轉型之痛。在金融危機前生產及銷售形勢大好之時,他就積極尋找高科技項目,“完全不同于目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那時他已經意識到,嘉興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主要在于人力成本低”,但這“隱藏著危險”。
“最大的難題就是,對于勞動密集型、外向型的企業來說,今后沒有那么好的環境提供給我們了。首先,人民幣升值,等于去掉了企業近15%的利潤。其次,國家出口退稅率調低,又去掉了8%的利潤。再加上勞動合同法施行,對我們這樣有著上萬名勞動力的企業來說,每年僅用人成本就將增加3000萬元。”可惜的是,岳姚祥這些理性的思考,對嘉興企業主們來說仿佛天方夜譚,面對雪片一般飄來的外貿“大單、長單”,大家還是樂于增加生產線,擴大產能。
面對“用工荒”這個現實壁壘,濮院羊毛衫企業興起了技改熱潮,“以高科技設備來取代傳統的人工”。以浙江利仕織造有限公司為例,它一年產量接近250萬件,采用傳統手搖橫機,“最起碼得有七八百人,每天工作12小時,還得確保不請假,才能消化完。”但2009年以來,這家公司投入1億多元,引進200多臺電腦橫機,用工一下子縮減了3/4。雖然“一臺進口電腦橫機就等于一輛奧迪車”,但面對“用工荒”,濮院羊毛衫企業主一個個豁出去了,2010年已進口電腦橫機900多臺,技改的主要目的便是“保產能”。
劉斌功告訴記者,當前“用工荒”對嘉興企業主搞產業升級“有很大啟發”:“老板們頭腦很清晰了,這是社會發展的趨勢,未來用工更加荒,越來越緊缺。想生存必須創新,打造品牌。光想著眼前,怕虧本,不給員工交保險、福利,這種企業辦不下來了。三五年內,嘉興一定有一大部分企業靠產業升級和轉型發展壯大。”在嘉興市經貿委,記者也聽到一個事實:當前,訂單越來越向規模型企業集中。如此下去,“低、散、小”型企業將逐漸被淘汰出局。
這就不難理解,當地媒體會把濮院技改與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產業結構的調整相提并論。“用工荒”的背后,濮院正在上演一場洗牌大戲,那些因為人工不足無法接單的企業,或者不能滿足下訂單者的需求的企業,將慢慢失去客戶的耐心和信任。“保產能”實際上就是保訂單,保生存。因此,“用工荒”直接導致了濮院技改的熱潮。問題是,緊缺的財力用于進口昂貴的設備,過分注重“保產能”,使得不少企業沒有能力去創新,去做品牌,只能繼續做一頭任勞任怨的“代工牛”。在這些企業,產業升級和產業轉型之路的時間表就這樣慢下來了。

漲薪,這是必須的
從產業結構看,那些高耗能、低利潤、員工收入低的行業,成為招工難的多發區。技改固然是應對“用工荒”的一個有效法寶,但紡織、服裝、皮革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很多環節根本沒有辦法用機器來代替人力。
“隨著用工荒現象的出現,表明我市低價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正在消失,企業必然會采取提高工資待遇等方式,來增強用工吸引力,企業用工成本必將增加。而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紡織服裝業,因其附加值低,已開始不再適應現代產業發展要求了。”嘉興市經貿委的這個判斷,正如某外資集團副總經理費曉波所言,一些行業會慢慢從嘉興消失,“20年前上海也是中國紡織重鎮,后來一樣轉移出去了”。
不過,當下大多嘉興企業主可無心做這些戰略思考,他們著急的是,那些空缺的勞動力從哪里來。嘉興市經貿委也給企業出了“四策”:一是提高工資待遇,增加用工吸引力,“引進外來勞動力,解決用工短缺的關鍵是提高職工工資待遇”;二是保障民工合法權益,“改變短期用工行為”;三是調整用工條件,適當降低在年齡、性別、技能、經驗等方面的要求,擴大用工范圍;四是重視企業文化建設,“對員工要實行人性化關愛和貼心式管理”。
記者調查發現,“漲工資”這一招已經被嘉興企業普遍接受。而且,從4月1日開始,浙江省將最低月工資標準調整為 1100元、980元、900元、800元 4檔,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時工資標準調整為9.0元、8.0元、7.3元、6.5元4檔。其實,江蘇省率先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后,北京、上海、廣東等地也相繼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用工荒”直接刺激了勞動成本的上升。岳姚祥的經驗是,“一個企業要做好,員工待遇要高于社會,生產成本要低于社會,質量要好于標準”。這一輪,嘉興企業主基本上都在原有員工月薪上加了300元左右。
漲薪對企業壓力到底有多大?從嘉興企業家周國建公布的數字來看,最景氣的2007年他的企業銷售收入是20億元,利潤1億元,純利潤率是5%。不過擁有這么大產值的一家服裝企業,它用工一般都是幾千上萬名,每人一個月漲300元,一年下來就是幾千萬元,將吃掉企業不少的利潤。這就是為何不到“用工荒”企業主不愿主動加薪的原因,傳統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利潤率太薄了。代工如此辛苦,為何不走品牌路線?周國建說出了一個事實:服裝品牌,這不是一個企業的問題,甚至和國家整體實力有關。換言之,只有國民整體消費水平到位,才會誕生一批國內名牌。
對于嘉興來說,加了300元,也只是與周邊城市湖州、臺州、昆山等地的原有水平看齊。從薪水上來看,嘉興并未具備排他性競爭力。這就不難理解,嘉興很多企業節后工資一漲再漲,但前來應聘的農民工還是嫌“工資太低”,依然招不足工。記者在嘉興采訪不斷碰壁,很多企業主根本不愿意談“用工荒”這個話題,害怕自己的企業被記者提及后,更難招到人。正因為自己管理的企業不存在缺工問題,費曉波才樂于接受記者采訪,對于用工成本問題,他的看法也與其他人很不一致:“工資這一塊的成本是很低的,其他成本比工資成本多得多,為了贏利而壓低工資,那證明這個企業不能做大,只能做小。”
劉斌功向記者透露,有不少企業主向政府抱怨:“這樣加工資我們受不了了。”但劉斌功總是勸相熟的企業主:“壓力是很大,但想通了就不大!否則員工流動性大,企業總是招來新手,不僅產品質量上不去,招聘、培訓等費用更得不償失。”當前,產品價格不但沒有提高,而且還略有下降,加之原材料價格上揚,對企業而言,確實是一個難關。“越是這樣,企業越需要有穩定的員工團隊,大家愛崗敬業,把產品質量做上去,打造品牌,未來才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關鍵是待遇,這是第一位的。”《嘉興日報》經濟部的一位同行也這樣強調。此外,他還強調“企業要把工人當人看”。他向記者舉了一個小例子。之前他采訪過一位外來務工者,因為別的企業薪水高跳槽過去了,但過了幾天又跑回原來的企業了,原因是原來的企業工作氛圍好。“現在很多下訂單的國外企業,不定期到嘉興代工廠抽員工調查,檢查員工吃、住、上班等環境,如果不好就減掉訂單。”他說,不僅品牌商警惕“血汗工廠”現象,“用工荒”背景下,員工也越來越看重工作環境了。
也就是說,嘉興市經貿委提供的“四策”之中,漲工資之外的其他三條,同樣重要。現在不少嘉興企業已經開始實踐,辦廠報、唱廠歌、開QQ群等,搞企業文化建設。帶薪休假等福利制度出臺,上馬配套文體設施的生活小區,還有生日送蛋糕等人文關懷行動……很多被稱為“感情留人”的創意頻頻亮相,“用工主權”這類充滿“以人為本”的新詞匯也開始從嘉興企業主嘴中蹦出來。還有企業主說,要“讓員工有家的感覺”。更有嘉興企業主,買地造房,以成本價賣給員工。
事實證明,“待遇留人”和“感情留人”都做好的嘉興企業,用工就不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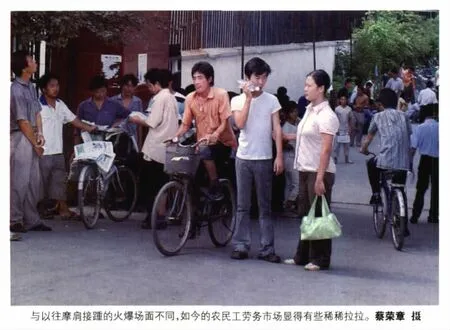
政府應做什么
就目前來說,嘉興制造業基本上處于最低端的“代工”階段,雖然近幾年引進了一批所謂高科技企業,但在產業鏈中還是屬于最低端的角色。因此,如果“用工荒”持續下去,未來若干年后將動搖嘉興“制造基地”的地位,一旦大批企業轉移出去,嘉興將面臨“產業空心化”的危險。這就不難理解當地政府破解“用工荒”的急切心理。嘉興市經貿委提出的應對之策中,對政府職能部門也有要求,其中第一條是,“強化政府職能,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政府相關部門要把維護農民工權益、建立和諧勞動關系、優化就業環境作為重要議事日程”。第二條是,“加強產業引導,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速企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金、技術密集型轉變”。第三條是,“加強勞動就業培訓,提高勞動者技能素質……只有積極實施高技能人才振興工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高技能產業工人缺乏的問題”。
事實上,嘉興這一輪“用工荒”,最缺的正是“高技能產業工人”,這是中國職業教育落后大環境下的產物,同時也是制造企業向來“輕培訓”的必然結果。現在,這個“惡果”通過“用工荒”更顯著地暴露出來。因此,光靠嘉興一地喊“實施高技能人才振興工程”是不夠的,必須在全國范圍內重視“高技能產業工人”的教育和培訓。
劉斌功告訴記者,以前嘉興還有170多家職業技能培訓學校,現在僅剩不到20家,而且很多學校不過幾名員工,不像一個培訓學校的樣子,“政府重視力度不大”。學校開辦23年了,劉斌功僅拿過政府1萬元的補貼,濮院羊毛衫技術學校僅是一所擁有30名教員的小學校(已是當地最好),而且其中一半教員是掛靠和兼職的,但能辦起這樣一間像模像樣的培訓學校,劉斌功已經使出渾身解數,筋疲力盡了。令劉斌功欣慰的是,最近當地政府開始重視起他和他的學校了。作為制造業基地,嘉興已經嘗到了輕視“高技能產業人才”教育和培訓的嚴重惡果,如今喊“振興”了。
不過,應對“用工荒”,嘉興還不能僅僅是“頭痛醫頭”。長遠來看,這是一個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戰略選擇的大方向問題。
目前的嘉興,工業對GDP的貢獻率為70%,是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產業。在嘉興,有人跟記者提到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的“再工業化”概念,認為嘉興下一步的發展其實就是一個“再工業化”的過程,即繼續壯大制造基地,創出一批品牌企業,從低端制造轉向研發、營銷等高附加值的創造性勞動。這就意味著,人力資源必須面臨一個“升級”的過程。那么,決定嘉興“第二次創業”成功與否的將是高端人才,而不是低端勞動力。
從這個意義上講,比起組織企業去中西部省份招農民工,當地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創造更好的創業和就業環境,筑巢引鳳,實施“引智工程”,讓更多的工業產品設計人才、營銷人才、服裝設計師等高端人才來到嘉興。嘉興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家已經提出,打造“總部經濟”,即成為長三角一批新興中國品牌企業的聚集地,依托靠近上海和杭州的區位優勢,為長三角制造業從外貿型轉向內銷型,打開國內市場,提供一個“橋頭堡”的平臺。這個躍升,對嘉興來說,無比艱難,目前仍缺乏向心力和輻射力的嘉興,更需魄力和智慧才能邁向成功。
“工業時代”,嘉興崛起,成為“中國制造”(Made in China)的重要基地。今天,中國正在邁向“中國創造”(Made by China)時代,嘉興乃至整個浙江省對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做“中國創造”的先行先試者,還是繼續停留在“工業時代”?“用工荒”只不過是長鳴警鐘的又一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