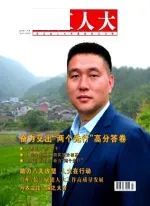工資共決,尊重工人的話語權
■阮蓓茜
工資共決,尊重工人的話語權
■阮蓓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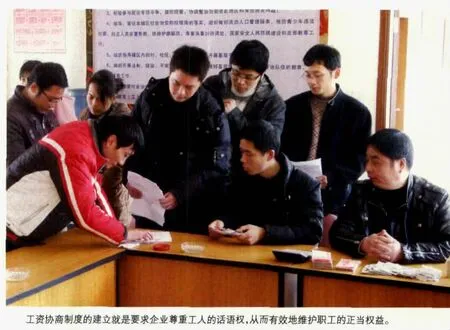
杭州油漆有限公司叉車工朱文斌,終于找到了當家作主的自豪感。他曾兩次下崗,日子過得緊巴巴,公司實行工資集體協商以來,朱文斌的年收入慢慢見漲,從2005年的1.3萬元,漲到了2009年的6萬元。“企業給多少工錢,我們也有說話權,干活更有勁了。”
近幾年,在“招工難”和員工流動率高的困擾下,浙江企業也越發懂得通過重視改善員工待遇,創造和諧的用工環境來吸引人才。工資協商制度的建立就是要求企業主尊重工人的話語權,通過合理的工資體現勞動價值,穩定勞資關系,促進企業發展。
浙江省自2001年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以來,讓越來越多像朱文斌這樣的普通工人,也有機會跟企業主在工資上“討價還價”。日前,記者從在杭州召開的全國勞動關系座談會上獲悉,2010年底前浙江省70%以上企業將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浙江從完善機制、完善配套措施上狠下功夫,先后出臺了《浙江省集體合同條例》、《浙江省企業工資支付管理辦法》、《浙江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等法規、規章,為工資集體協商提供了法律支撐。據悉,目前,浙江省已初步形成“企業協商談增長、行業協商談標準、區域協商談底線”的工資協商模式,但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覆蓋面,仍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一項好制度,推行有點難
一頭是想提高工資福利的工人,一頭是要壓縮勞動力成本的企業主,如何在雙方之間找到平衡點?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給出了答案:由工會出面,把企業和工人召集起來,坐下來談好工錢,再按這個標準發工資。
目前,在溫嶺新河鎮長嶼羊毛衫行業,橫機工每做一件羊毛衫,能拿到11.5元,這是在2009年8月份的“工資談判”上定下來的價格。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會主席陳福清向記者描述當時的談判場景——
工人代表:“橫機工是制羊毛衫的第一道工序,要求高、費體力,工價低了,我們認為應該提高到每件12.5元。”
企業主:“最近原材料都在上漲,這個工種每件10元已經很合理了。”
工會代表:“根據工會調查,大部分工人都反映工價是低了,希望企業給予合理的提價。”
第一輪談判之后,雙方回去緊急磋商。
緊接著,第二輪談判開始,工人代表將這一工價標準降為每件12元,企業主則升至每件11元,雙方要求更加接近。隨后,第三輪談判開始,在行業工會協調下,雙方達成折中方案,都接受了每件11.5元的標準。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溫嶺的羊毛衫行業已經實行7年。陳福清說,大家都嘗到了這項制度帶來的甜頭,即便在經濟不景氣的2008、2009年,工資漲幅也都在5%到10%,當地勞資糾紛也少了。
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讓以往不少行業因工資、工價不統一造成的企業無序競爭,逐步消失。記者了解到,在溫州的五金行業,一位“資深”技術工,“轉會費”曾被炒作到了30多萬元。而如今,整個行業工價統一了,到任何企業拿的都是相同的工資,職工隊伍更加穩定,以往跳槽、“挖墻腳”現象大大減少,企業之間良性競爭的格局逐步形成。
浙江省總工會法工部部長方火春說:“現在,在浙江很多地方,企業職工工資不再由老板一個人說了算,已初步形成‘企業協商談增長、行業協商談標準、區域協商談底線’的工資協商模式,有效地維護了職工的正當權益。”
截至目前,浙江簽訂工資集體協議70936份,覆蓋企業達到13.22萬家,覆蓋職工668萬多人。到2010年底,“工資共決”覆蓋面將達到浙江省企業的70%以上。
然而,這項讓許多人叫好的制度,在一些企業內部的推行,卻相當艱難。“我在公司已經待了10多年,公司規模越來越大,業績年年上升,可是我們的工資卻沒漲多少。”在金華一家民營企業工作的劉女士告訴記者,她的工資、獎金都是由老板一人說了算。“老板能發善心多給些工資,我就已經很滿足了,哪還敢幻想與老板談判。”劉女士很無奈。
實質協商少,有的在“作秀”
記者發現,現在一些企業僅把工資集體協商當成一種“秀”。
在平陽縣鰲江鎮,生產編織袋的企業眾多,經常為招不到工人頭疼。當地企業主向工會干部大吐苦水,說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制也沒用,廠里的員工干了一段時間就走人,職工流失率達50%以上。
經調查,原來當地不少企業在實行過程中,根本沒有什么“協商”,只是拿著早已準備好的協議書,叫員工隨便簽個字,很多員工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鰲江的例子并非個別現象,在一些所謂已經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企業中,沒有多少企業主能跟工人真正坐下來,面對面討論工資問題,能達到1/3就已經不錯了。”浙江省總工會法律工作部部長方火春在調研中發現:“不少企業是為了應付上級的檢查,想法子讓制度變成‘花架子’。”
“企業經營狀況千變萬化,但協議白紙黑字,一旦簽了字,萬一生意不好,兌現不了合同,那等于是拿繩子綁住自己。”溫州一家機械制造廠的企業主坦言,公司會視情況給員工加工資,但真正搞工資協商,內心還是不情愿的。
“中小企業是制度執行的難點,也是重點。目前,浙江省的勞動爭議案件主要集中在勞資矛盾方面,而案件高發地就在中小企業。但單純靠企業主主動讓步或提高覺悟,是很難推行的。”方火春說,從這幾年的成功案例看,都是在一定壓力下實現的,這些壓力來自社會輿論,也有來自工人、工會的干預等。
回憶剛推行工資協商制度的那段日子,陳福清總結了三個“難”:臉難看,人難見,話難說。“聽說是工會來調查工資的,不讓我進門,說老板不在。好不容易見到老板了,我問,你們的工價怎樣?人家老板根本不搭理我,覺得我在跟他對著干。”
“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推行工資集體協商還面臨許多困難。許多企業對行業集體協商還不夠了解,行業協商過程比較復雜,勞動關系雙方都還不太適應。”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在“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下,職工協商代表的話語權相對微弱,他們享有知情權、參與權,但難有決定權。即使企業工會有權代表職工與企業資方協商,但有些企業工會負責人由于自身素質和受限于勞動關系及本人利益等因素,“不會談”、“不敢談”的情況仍較為普遍。
為此,“需要借助當地勞動工資專家參與協商,通過對行業經濟水平、就業和工資分配狀況等進行實事求是的量化分析,來提出切實可行的協商方案,再由工會主席依據此方案出面進行協商。”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韓福國博士說。
勞資拉鋸戰,何時能雙贏
讓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體面勞動,提高勞動報酬是關鍵所在。
浙江省是民營經濟大省和農民工主要輸入地,民營經濟對全省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達70%以上,農民工在民營企業打工的人數占職工總數的90%。民營經濟的發達,伴隨而來的是,勞動關系復雜,勞資矛盾突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推行承載著許多人的期望。
在采訪中,不少業內人士都把解決推行難問題的目光集中在監督上,缺乏對企業的有效監督措施,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推行的一大“短板”,浙江省將填補這一空白。
2010年,浙江省把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列入《浙江省平安市、縣(市、區)考核評審條件》,進一步加大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推進力度。將于2010年10月1日實施的《浙江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中,將平等協商單獨列為一章,并把企業實行民主管理情況納入勞動保障監察的內容,列入企業守法誠信檔案。今后,評選企業和經營者涉及社會責任、生產經營管理等榮譽稱號時,企業是否實行民主管理將作為依據……
“現在正是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好時機。”浙江省總工會有關負責人認為,近幾年,在“招工難”和員工流動率高的困擾下,企業也越發懂得通過重視改善員工待遇,創造和諧的用工環境來吸引人才。
“事實上,很多企業主在實行協商制度后,整個公司的用工環境開始好轉,職工凝聚力、勞動積極性都在提高。”方火春希望企業主能形成這樣一種觀念:協商工資并不等同于漲工資,而是要求企業主尊重工人的話語權,通過合理的工資體現勞動價值,穩定勞資關系,促進企業發展。
浙江省總工會的職工收入狀況抽樣調查也發現,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企業,職工工資能隨著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而增長,有9.3%的企業職工工資增長達10%。
“以前,企業主看到工會的人來了就怕,經過幾年的工資協商制度實施后,企業主的態度也在改變。”陳福清深有感觸。
事實上,在協商中,工會可以代表職工,但誰來代表企業?
2009年,全國總工會下發的《關于積極開展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指導意見》規定,工會協商的對象——企業代表組織,不應僅限于企業聯合會、企業家協會,還應包括工商聯、行業商會等各種企業代表組織。
從工會組織建設看,鄉鎮、街道、社區、區屬經濟開發區和工業園區的工會組織相對比較健全,而作為企業方代表的企業家協會、企業聯合會、工商聯、行業協會和商會等組織,雖在縣一級還相對完善,但在街道、鄉鎮、社區往往沒有對應的組織。
各地為了將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開展下去,采取了靈活變通的方法。有的地方將行業內的企業主召集起來與之簽訂工資集體合同,但是,工會與毫無組織資源的個別企業主簽訂工資集體合同時,它無法證明這種工資集體合同是平等協商的結果。
據了解,有的地方推選出一家企業代表與職工進行工資協商,這種方式雖然可以保證行業性工資集體合同的簽訂,但由于沒有一個固定的企業方代表組織,工資集體合同在履行過程中產生爭議時,往往難以及時協商解決。
“因為實際情況比較復雜,很難一下子界定企業代表組織是誰,這反映出我國目前企業組織不健全、集體協商談判制度不完善等問題。進一步明確企業方集體協商主體,需要相應的配套制度及政策進一步完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博士吳清軍說。
集體協商還遭遇另一種無奈,企業高級管理層(特別是企業主)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過大。工資集體協商調節的是一線職工的收入,對實行年薪制的企業高管起不到有效制約。
在杭州、溫州等地,一線職工年均收入大多數在1.5萬元至3萬元,而經營者個人工資加上資本收入一般在20萬元至50萬元,多的超百萬元,收入差距的拉大影響了工資集體協商的開展。
由于建立集體協商制度就意味著建立了讓職工收入隨著企業經營效益提高而提高的長效機制,相對于那些沒有建立這種機制的同行業競爭對手,已建立協商制度的企業就處于人工成本劣勢。中國企業聯合會雇主工作部副主任程多生認為,政府部門應該考慮給積極開展集體協商、注重保護職工利益的企業一些優惠政策。
“中小企業基本都是微利企業,如果讓其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給勞動者漲工資,其利潤就可能為零,這也是這些企業資方不愿談、拒絕談的重要原因。”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建議,對員工工資低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70%的,通過集體協商增加的工資應允許全部進成本,免收所得稅甚至減收部分流轉稅,以支持這些企業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合理提高低收入員工的工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