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喪失母性的歷史悲劇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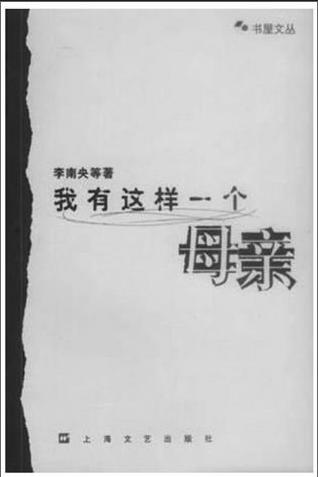
我們以前所接觸的中外文學(xué)作品中母親的形象從來都是正面的、歌頌性的、崇高而偉大的,如高爾基的《母親》、朱德的《我的母親》等。然而在海外看到李南央所著的《我有這樣一位母親》(上海文藝出版社)和老鬼所著的《我的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卻明顯感覺到是少有的塑造了負面母親形象的兩本書。
李南央,李銳與范元甄之女。李銳曾擔(dān)任中共領(lǐng)導(dǎo)人高崗、陳云、毛澤東的秘書。范元甄,享受副部級待遇的離休干部。
李南央說:我取稍有貶義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為此文的題目,是因為我的母親無從歌頌起。但是她是一個奇特的母親,奇特的一定要寫出來。
李南央在書中寫道:小就未有享受到母愛,未嘗過與母親親昵的滋味。不僅如此,子女還遭到過母親的毒打。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由于階級關(guān)系高于一切,人們無視家庭的價值,夫妻之間以及兩代人之間可以隨意反目。有人做過專門研究發(fā)現(xiàn):文革中自殺的很多知識分子,其陷入絕望并不是因為遭到批斗,而是在批斗之后沒有得到任何來自家庭的關(guān)愛,沒有家庭的溫暖使他們更絕望。在一個革命家庭中,母親不愿意為子女花時間,為了革命可以犧牲要孩子,為了革命甚至可以大義滅親。母性在那樣的年代遭到徹底泯滅。
“我的記憶中,媽媽沒有高興的時候,也不允許家里有歡樂的氣氛。記得有一年我從陜西的工廠探親回家,因為自己自由生活慣了,忘了家里的規(guī)矩,一邊干活,一邊哼起了歌兒。媽媽立即厲聲叫了起來:“你有什么可高興的?我們這個家是沒有歡樂的!”
“有一次,媽媽發(fā)脾氣,譏諷我:‘你小小年紀(jì),還母愛,母愛的,滿腦子令人作嘔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遠藏不過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記里寫對媽媽的看法了。可是這點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剝奪了以后,我對媽媽是真真兒地沒了感情。也沒有了一絲一毫的尊敬”。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在學(xué)校挨斗,回家一言不發(fā),精神極沉悶。媽媽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對,問我怎么了,態(tài)度極和藹。我有些受寵若驚,在那種冷酷的環(huán)境里,感到了 一絲母愛的溫暖,不覺地流了眼淚。告訴媽媽:自己因為爸爸的問題,也有她的因素,在學(xué)校里挨了同學(xué)的批斗。還沒等我說完,媽媽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極為幸災(zāi)樂禍、可有機會報復(fù)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標(biāo)榜自己不要母愛,自己最堅強嗎?哭什么!跟我說什么?你在學(xué)校挨不挨斗,跟我沒有關(guān)系,不要往我身上 扯。那是你自己在學(xué)校一定有問題。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講這些事情。你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堅強,就不要以為還有媽媽。我在機關(guān)挨斗,又向誰去哭?我那時還不到16歲,看著媽媽那狠毒的近乎猙獰的面孔,只覺得自己向一個大冰窟窿里沉下去,從里到外地凍僵了。從此以后,我的心門是永遠地死死地向母親鎖住了”。
無獨有偶。另一本書《母親楊沫》的作者老鬼姓馬名波,是作家楊沫的小兒子。老鬼說,在這本“概述母親一生”的書里,他要“盡可能大膽地再現(xiàn)出一個真實的、并非完美無缺的楊沫”。
老鬼用相當(dāng)多的筆墨,在書中寫了母親楊沫早年在烽火歲月中的革命經(jīng)歷,寫了她創(chuàng)作、出版《青春之歌》前后的艱難曲折、聲名鵲起以及幾度風(fēng)風(fēng)雨雨,這些無疑是楊沫一生中的“華彩篇章”。 與此同時,老鬼又坦誠直率地寫到了母親楊沫的另一面。
“文革”中楊沫與丈夫馬建民之間的互相揭發(fā),可以說是置之于死地、“一劍封喉”、直取要害的揭發(fā)。先是馬建民揭發(fā)楊沫是“混入黨內(nèi)”的假黨員,接著楊沫以牙還牙,用大字報揭發(fā)丈夫與鄧拓等人的關(guān)系,還說他“曾替大特務(wù)王光美轉(zhuǎn)過關(guān)系”。書中將這些揭發(fā)、交待材料都原文照錄下來。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像馬、楊這種夫妻反目的事,當(dāng)然不是絕無僅有;但即使在當(dāng)時那種“革命”、“專政”的高壓之下,夫 妻之間、家人之間互相保護、相濡以沫的事情也不會沒有。馬、楊之間的互相揭發(fā),給彼此造成的傷害可想而知。老鬼說:“這導(dǎo)致了兩個人感情 上不可彌補的裂痕。”
然而使老鬼最感痛切的,是母親楊沫身上母性、親情的泯失,“對孩子缺少關(guān)愛,甚至有些冷酷無情”。老鬼認為,這是母親自小生活在缺乏母愛和親情的冷酷環(huán)境中所造成的,楊沫雖然出生大戶人家有親生父母,事實上卻好像是個孤兒。衣服破了,沒人縫;生病了沒人照料;身上長了虱子,沒人管;季節(jié)變化,該換衣服了,沒人提醒……平時吃飯、睡覺都和傭人在一起。她衣衫襤褸,處境還不如闊人家里的一條小狗。這個家是個破碎、畸形的家。楊沫說過:家,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是個溫暖的,光明的,舒服的場所。但對她來說,卻是個冰冷的,陰暗的,不堪回首的地方。楊沫對子女的冷漠也跟長期批判“資產(chǎn)階級人性論”的社會氛圍有關(guān)。老鬼在書中寫道,三年困難時期,父母買了不少高級糖、高級點心和營養(yǎng)品,“但這些吃的都放在他們屋里,只供父母享用。他們出門就鎖門,不容孩子染指”。老鬼那時從學(xué)校回到家里,經(jīng)常吃不飽,而且不交糧票就不給飯吃;老鬼說:“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開肚皮吃飽,姑姑家很窮,什么補助也沒有,可從來不管我要糧票。”他的哥哥也是這樣,有時甚至在家餓昏過去;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頓飽飯;“跟父母一比,真讓人感嘆”。老鬼六歲時,有一次患腸粘連,疼得滿地打滾,母親楊沫也不當(dāng)一回事,過了幾天眼看他奄奄一息了,才讓十幾歲的大兒子帶他去醫(yī)院,醫(yī)生動完手術(shù)之后說:“再晚就沒救了。”老鬼說:“像我母親這樣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并不常見。”楊沫(及丈夫)還動輒跟子女“斷絕來往”,有時還作出令人寒心的舉動。1979年,正在北大讀書的老鬼,與父母發(fā)生觀點的沖突,楊沫便寫信給北大中文系,對兒子的言行加以揭發(fā)和譴責(zé),要求學(xué)校嚴(yán)加管教或給以必要的處分。老鬼說:“當(dāng)形勢緊張時,母親應(yīng)該站出來保護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動給學(xué)校去信表態(tài)批判孩子,聲討孩子,從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李南央在《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一文中,痛切地刻畫了母親范元甄那扭曲的靈魂,及因她的乖戾暴虐給家人造成的傷害。這本書中的“這樣一個”,看似指范元甄一人,實際上包含著“一類革命女干部”。
在“紅色恐怖”降臨己身時,范元甄不惜出賣丈夫以求解脫;為“表現(xiàn)”自己的“革命”,捏造事實,害得弟弟英年早逝;妹妹病危之際,在妹妹脆若游絲的生命上捅上最后一刀;至愛親朋無不遭受過她的告密陷害,無不經(jīng)受過她各種各樣的傷害。用李南央的話說就是:活得只有恨,而且這么刻骨地恨。
范元甄現(xiàn)象,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為了政治,不講親情。為了自保,為了自欺欺人的“原則”,對親人落井下石、揭發(fā)告密;事過境遷,又極力衛(wèi)護致使自己深受其害、又害別人的時代。她也只能通過這些無謂的掙扎,用自我欺騙的方式,給自己找到一點可憐的心理籍慰,用此來反抗自己荒蕪一生的空虛、眾叛親離的孤寂和良心回歸的不安。
老鬼的《母親楊沫》中不難看出楊沫身上范元甄的影子。
老鬼在談《母親楊沫》創(chuàng)作時,談了母親楊沫靈魂扭曲的過程:“應(yīng)該說,母親的出身和個性使她對左的那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過多年的、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親由一個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青年,變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絕對聽上級的話,絕對不會給領(lǐng)導(dǎo)提意見。對任何領(lǐng)導(dǎo),包括自己親屬的領(lǐng)導(dǎo)、孩子的領(lǐng)導(dǎo),她都畢恭畢敬、奉若神明,這幾乎成了她的處世習(xí)慣。這是多年來教育的結(jié)果。”
老鬼說:“困難時期在家里吃不飽,父母躲在自己的房間里吃,卻不給孩子吃。每逢我看到一般人的家庭生活那么和諧,彼此那么關(guān)心,就特別羨慕。”
李南央母親范元甄在延安時,曾經(jīng)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李南央寫道:“媽媽跟我講起過在延安兩次見到毛主席。一次在清涼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帶著警衛(wèi)員下山,主席閃到一邊說:‘小范同志你先走。媽媽很是驚訝主席會知道她的名字。還有一次,她在窯洞前紡線,突然看到紡車前站住一雙大腳,一抬頭,是主席微笑著看著她紡線。可見,媽媽當(dāng)年在延安確實是很引人注意的”。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道:當(dāng)年上海去延安的進步青年、電影明星李云鶴,藝名藍蘋,也就是后來的江青穿一件淺藍色旗袍,非常顯眼。樸素大方的裝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靈動的眼神,非常富有女性的魅力,給人很深的印象。但是最后她們這些美女的女性母性全為黨性所取代。失去母性的女性最后自己異化成沒有人類情感的“鐵人”。豈止是女性,所有參加這場革命的人在革命中,都以革命的名義使得人情變得淡漠,人性漸漸失去。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劇,而這些女性是文革這個荒唐無稽時代的最大受害者。文革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一個時期。以犧牲家庭、以剝奪母性、將人們改造成只有階級性的人,是對人性的最大摧殘。
有評論說:“這兩本書之所以別具價值,就是它們以一種嚴(yán)酷又痛苦的真實,記錄了兩個特別的人物和兩個特別家庭的悲情,又以這兩個特別人物和特別家庭的悲情,最終記錄了一個時代和一段歷史的悲劇”。“這兩本書將個人的記憶與民族的記憶相連,是充滿了血和淚的作品,是對當(dāng)時那個時代的有力控訴。我們不能再讓喪失母性的歷史悲劇重演”。“這兩本書,出于將自己的經(jīng)歷保存下來為他人日后所知的信念,秉筆直書,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母親形象。這兩本書是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家、社會學(xué)家、心理學(xué)家研究的很好的資料”。
有評論特別指出:作為經(jīng)歷了苦難的民族,我們現(xiàn)在要做的就是:既然經(jīng)歷了苦難,就應(yīng)該將這些苦難盡可能轉(zhuǎn)化為精神財富,例如猶太人,他們經(jīng)歷了很多苦難,但是都被他們轉(zhuǎn)化成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反觀我們自己,還是在歷史事實面前采取遺忘、甚至回避的態(tài)度。如果苦難不能轉(zhuǎn)化成精神財富,災(zāi)難就會重新降臨在同一土地上。曾幾何時,我們中國把琴棋書畫、四書五經(jīng)以封建糟粕等罪名趕出了課堂。提倡人性和母性的作家如冰心,竟遭到無辜批判。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傳統(tǒng)的道德規(guī)范被當(dāng)作封建思想徹底掃除,代之以暴力論無神論。中國人在虛假、暴虐的文化氛圍中成型,身上浸染積聚了過多的毒素,仁愛、寬容、諒解、尊重他人的成分稀少,而這些又恰是中國融入世界的障礙。人類重大災(zāi)難,大多是由于人性惡的共振引起的自噬。遵守心中的道德定律,是遏制人類獸性萌動避免這些災(zāi)難發(fā)生的唯一辦法。而守住心中道德定律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恪守住真,真之所至善萌生焉,真是人類一切美好價值的基石。因為,幸福的社會必須有合乎人性的制度來保障,合乎人性的制度必須由正常人格的人去運作,正常人格的人必須有健康的人性,健康的人性有賴于真實向上的文化,而我們的文化里恰恰缺少這些。文化重建——尤其是核心價值觀的建構(gòu)對中國尤其顯得重要。
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國聯(lián)邦政府機構(gòu)擔(dān)任高管的章敏女士在談及自己歷經(jīng)艱辛、在美國的成功之道時說的:具有優(yōu)雅的魅力是女性馳騁商場職場的有力武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聰明才智、見多識廣、反應(yīng)敏捷、舉止優(yōu)雅的女性總是會受到歡迎,一個處處優(yōu)雅具有魅力的人總是屬于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然而受到中國“文革”影響的一代中國女性,早已經(jīng)失去了那種優(yōu)雅,中國女性“灰頭土臉”的打扮、大大咧咧的舉止、不善交往的特征,嚴(yán)重影響了她們在美國職場的發(fā)展。章敏還專門提到《上海生與死》的作者鄭念,一生不改高貴、優(yōu)雅。在“文革”中即使落難牢獄,也盡可能維持自己的生活理念。人們從《上海生與死》一書中看到一位優(yōu)雅、堅毅、機敏、高貴的女性,面對野蠻和強權(quán)的侵犯時,如何堅守底線,維護自己生而為人的尊嚴(yán),以及心中不可折損的道德律。在監(jiān)獄里,她抵抗當(dāng)局對她的種種精神迫害和身體折磨,她以極大的勇氣,堅持不發(fā)瘋,不毀掉自己,保持自己的頭腦,保持自己的身體能夠行動,更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尊嚴(yán)和高雅。由于長時雙手被反銬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廁后欲拉上 褲側(cè)的拉鏈都痛如刀割,她寧愿忍受這鉆心的疼痛也不愿敞開褲鏈以至有可能閃露出里面的內(nèi)褲。在牢獄中受盡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勸她放聲嚎哭來引起惡勢力發(fā)善心,她堅決不從:“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fā)出那種嚎哭的聲音,這實在太不文明了”。六年的牢獄生活,雖然身陷囹圄,她堅持按照自己的意愿盡可能布置那一塊巴掌大的小天地,盡可能生活得有質(zhì)量,為未來做好準(zhǔn)備,這種面對淫威所表現(xiàn)出的傲氣和貴氣,令人肅然起敬!一個人和一個強大無比的制度較量,需要的勇氣也許不言自明。這種個人信念和道德堅持的勇氣,對高壓政治的抵抗,使她從沒有背叛自己的良心。鄭念是一個美麗的、聰明的、機智的、智慧的女性。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在力量根本懸殊的獄中,她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是那些迫使她就范的人無可奈何。鄭念是一個真正的智者。她的機智聰明使她成為兩者之間的精神勝利者。章敏說:在美國女權(quán)主義思潮走向沒落的今天,知性女人追求的應(yīng)該是“成熟、理性、大器、智慧”,而不是成為一個咄咄逼人的女強人形象。女性應(yīng)該是感情豐富具有女人味,“上得了廳堂,也下得了廚房”。“世故當(dāng)中不失天真,張狂之中不失純正”。女人要不忘自己的性別,具有內(nèi)在和外在美的結(jié)合,才符合女性本身的規(guī)律。
湯偉,旅美學(xué)者,現(xiàn)居美國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