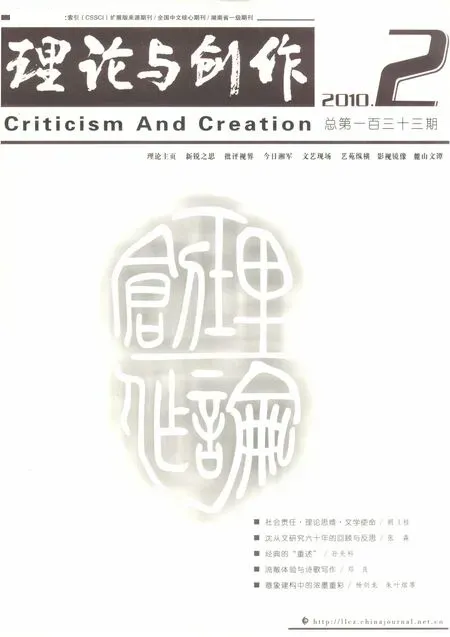作為思想家的沈從文
■ 焦亞東
作為一位獨具個性特色的鄉土文學作家,沈從文自19世紀20年代起即為文壇所注目。然而1949年以后,嚴苛的意識形態使得國內的沈從文研究陷入了低谷,近30年時間居然沒有任何關于沈從文的研究文字發表。新時期以來,與“張愛玲熱”、“錢鐘書熱”一樣,沈從文研究也逐漸升溫,最終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門“顯學”。與此同時,隨著研究的深化,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具有的深刻而復雜的內蘊也逐漸被人們重新發現,重新認識,重新評價,在看似純粹的懷舊情愫和鄉土想象的背后,潛藏著的是一位“鄉土作家”深刻的批判意識,牧歌般的《邊城》是一部將“截然不同的現代和傳統意識揉合一體”的名作,“鄉下人”沈從文也“一躍而成為具有現代思想的人,并越來越懂得了湘西粗俗的鄉土文化帶有人類更普遍的本性。”(金介甫《沈從文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地域色彩》)或許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19世紀90年代以后,沈從文研究開始向縱深推進,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其中,超越一般意義的文學批評,深入沈從文的內心世界,以多維的視角探尋包括人性、審美、倫理、生命、政治、文化等等在內的沈從文的思想內蘊,就成為這一時期學術界研究沈從文的著力之處。
筆者近日讀到的羅宗宇博士的《沈從文思想研究》一書(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就是一部全方位、多角度發掘、梳理、闡發沈從文思想的學術著述。這部致力于抉發沈從文思想的著作,因其學術視野的開闊、研究方法的獨特以及問題分析的深入,極大地豐富了沈從文研究的內涵,深化了沈從文思想研究的成果,還原了一個作為思想家的沈從文的真實面目。該書從這樣幾個層面對沈從文思想進行了探討,一是以“我是鄉下人”為題探討沈從文思想世界的自我之思。作者通過縝密的分析指出,“鄉下人”是沈從文自我之思的核心范疇,這種自我認同心理的形成,源自沈從文在鄉土社會與現代都市間的穿梭行走,其客觀依據正是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代轉型,因此,沈從文的“鄉下人”身份建構與認同,從其主觀意圖與價值訴求看,既是一名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份宣言,同時也是一份現代性批判的思想宣言。第二,作為本書論述的重點,作者以近乎繁瑣的引證和分析強調了沈從文思想的邏輯起點——“重造”,認為這一概念涉及國家的重造、社會的重造、民族的重造、文學的重造、自我生命的重造等廣泛的內涵,沈從文的思想世界實際上就是被“重造”范疇照亮的世界。在這一部分,作者不僅對“重造”的上述內涵逐一進行認真的考辨和闡發,而且還辯證地思考了“重造”思想家族之間的復雜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對沈從文“重造”思想的策略、性質以及內部關系結構給予了整體的揭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沈從文“重造”思想的闡發并非只是單一的分析,他尤為重視這種“重造”思想所具有的雙重張力結構:一是存在于某一重造思想家族成員內部的張力,如經典(文學)的重造即由文藝自身的藝術性與功利性之間的緊張關系構成;二是存在于重造思想家族成員間的張力,如社會的重造、國家的重造表現為現代性的追求,而人的重造、民族的重造、經典的重造則表現為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二者之間無法彌合的分裂狀態必然導致張力關系的出現。對沈從文思想世界中這樣一些矛盾的、復雜的、深刻的內涵,作者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此外,該書還論述了沈從文知識分子觀的形成及流變過程,同時對沈從文的文物考古學思想也有所梳理,盡管這兩部分的內容不是沈從文思想的核心,但依然在某種程度上使得沈從文思想世界的外延有所擴展,內涵有所豐富。
長期以來,在沈從文研究領域,針對具體作品的批評一直是研究的重心,而創作主體的思想研究則顯得比較單薄。已有的思想研究成果雖然在沈從文的文藝觀、生命詩學、審美理想等方面有深入的探討,但不足之處也很明顯:一是對沈從文思想的整體把握和系統研究尚嫌不夠,或在論述具體創作時觸及到思想問題,“思想”并沒有成為研究的重心,或論及的只是思想的某一個方面,未能對其全部思想做整體的統觀總攬;二是對沈從文思想的復雜性尚缺少深入的發掘。沈從文思想的影響來源非常駁雜,既有傳統儒道釋文化的熏染,也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啟示,既沾染上楚地巫文化的神秘色彩,又攜帶有現代都市文明的印記,因此,人道主義、民主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族群意識、人性關懷、現代性反思等等以一種“張力關系”彼此交織在一起,在他的全部著述中構成了對人、國家、民族、地方、自我以及生命的“雜語喧嘩”,對于這種豐富而復雜的思想世界,單一的、簡化的研究顯然無法求得圓足的闡釋。作為一部力求揭示沈從文思想世界的獨特性、復雜性和豐富性的學術著作,《沈從文思想研究》一書的“引言”,首先就將研究對象視為一位“執著于精神探索和思想言說”、“具有思想家氣質”的思想者,以此作為系統論述沈從文思想的前提與基礎;而在接下來的章節里,作者通過多層次的開鑿與多方面的比較,以“鄉下人”、“重造”、“知識分子”、“文物”等核心范疇為線索,從不同的角度對沈從文的思想進行了整體把握和系統觀照,指出“文學家沈從文具有思想家的品格,是一位思想家”,認為沈從文對現實世界及自我生命的思考自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思想系統,從而完成了對沈從文思想體系的整體描述和系統論述。這種全面、系統、整體闡發沈從文思想的研究工作,正如沈從文研究專家凌宇先生所言,“是一次對沈從文全部著述予以梳理、鉤成,并加以相應的闡釋及邏輯推導,以彰顯沈從文思想的整體構架及特色的工作”。(凌宇《〈沈從文思想研究〉序》),因而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正是基于從整體上系統地闡發沈從文思想的研究目的,概述的作者將強烈的問題意識帶入《沈從文思想研究》一書的寫作中,大膽借鑒前人的研究方法,以“獨特觀念/范疇”作為研究思路,梳理分析沈從文的思想內涵。在該書中,“重造”、“鄉下人”、“知識分子”、“文物考古”這些概念,并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提綱挈領式的標題,更是沈從文獨特思想與精神世界的鮮明體現。在此基礎上作者又將上述“獨特觀念/范疇”條分縷析,使在某一核心范疇統合下的“思想家族”細化為更加具體明晰的“家族成員”,如“重造”思想就在作者的梳理下分解為人的重造、國家的重造、民族的重造、地方的重造、經典的重造、工具的重造等細目,此種細化的目的并非為了論述之方便,而是試圖探究某一思想內部以及不同思想之間復雜的矛盾統一關系,從而避免單向性的闡釋可能導致的沈從文思想研究的簡單與粗疏,最終通過核心范疇的特定內涵及其內在邏輯關系,從整體上系統地揭示沈從文的思想世界。以這樣的研究方法與思路為先導,作者尋繹已有研究成果的局限與不足,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接著往下說”,非常圓滿地實現了多角度、多層次揭示沈從文思想的研究目的。通過提煉沈從文思想的核心范疇以及考察核心范疇的內在邏輯關系,闡發了沈從文思想世界的復雜性。
由于時代的變遷(一生幾乎跨整個20世紀)、地域的轉換(從鄉村到都市)、身份的變化(從鄉下人到名作家、名教授)、文化的碰撞(東西兩種文化的影響)等因素的制約,沈從文的觀念世界充滿著各式各樣的矛盾、沖突與困惑,對于這樣一位身兼文學家與思想者的人物而言,任何單向性的闡釋都會使原本駁雜而且復雜的思想變得單薄偏枯。或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沈從文思想研究》一書總是盡可能多的從不同的角度與層面思考問題,以辯證的思維求取問題的深入揭示。例如,對于沈從文的“鄉下人”范疇,以往的研究常常將其作為“他指”進行理解,“鄉下人”即是與“城里人”相對應的“陌生人”、“邊緣人”、“野蠻人”,這樣的理解固然不錯,但相應地也會忽略其中另外一層含義,這就是沈從文自我身份的建構與認同意識。羅宗宇則從“鄉下人”自我認同的形成過程、“鄉下人”自我認同的客觀依據、“鄉下人”自我認同的目的訴求三個方面,逐層論述“鄉下人”這一自我概念的復雜內涵,指出“沈從文進行的‘鄉下人’認同,與海德格爾的‘還鄉’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或者毋寧說就是近義的表達,他希望返回自然,實現精神的還鄉,完成對生命本真存在的探尋”——換言之,由于辯證地思考了“鄉下人”范疇具有的雙重意蘊,這個常常被沈從文掛在嘴邊的語詞,傳達出的就不僅僅只是作為湘西少數民族族裔的沈從文對都市的向往或厭惡,它同時還寄寓著一個在都市與鄉村之間游走的思想者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彰顯出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勢不可擋的現代化潮流中難能可貴的主體性與獨立性。
或許,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20世紀的中國文化史與文學史上,沈從文不僅僅只是一位杰出的鄉土小說作家,也不僅僅只是一位從事文物研究的隱逸的學者,他還是一位極具自我意識和個性色彩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