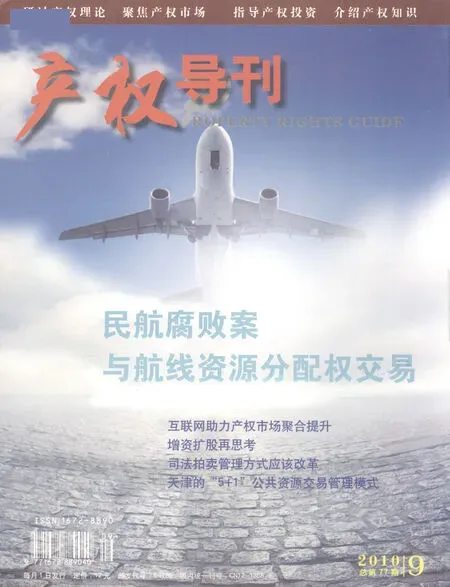話新舊“36條”,促民資發展
□/陳柳欽
話新舊“36條”,促民資發展
□/陳柳欽
2005年,國務院印發“36條”,全面系統地推出了促進非公有經濟發展的36條政策規定,給了民營經濟迅速發展的希望。然而配套措施落實不到位,最終使得民營經濟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
《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36條”(下稱“舊36條”)出臺一年之后,國資委出臺《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隨后,2007年出臺的《反壟斷法》更是對國有經濟絕對控股重點行業做出相應規定。但由于沒有配套細則等原因,相關政策的執行效果并不理想。
“舊36條”實施5年來,民間資本普遍感受到的仍是民資進入壟斷領域門檻過高,融資瓶頸未見擴寬。不但未能實現“國退民進”,反而在某些行業還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在市場準入條件方面,“舊36條”明確規定,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民間資本進入。但根據有關方面的調研情況看,目前我國壟斷行業中民營資本進入比重不超過20%,在全社會80個行業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有72個,允許外資進入的有 62個,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只有 41個。此外,民間投資在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所占比例非常低。有統計數據顯示,民間投資在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中占13.6%,在教育中占12.3%,在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中占11.8%,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中占7.8%,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中占7.5%,在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中占6.6%,在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中占5.9%。
一、“新36條”更具可操作性和廣闊空間
為深入貫徹落實“舊36條”等一系列政策措施,2010年5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被稱為“新36條”。“新36條”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金融服務、商貿流通、國防科技工業六大領域,興辦金融機構,投資商貿流通產業,參與發展文化、教育、體育、醫療和社會福利事業;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新36條”明確提出,規范設置投資準入門檻,創造公平競爭、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市場準入標準和優惠扶持政策要公開透明,對各類投資主體同等對待,不得單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
比起“舊36條”,“新36條”給民間資本提供了更為寬廣的空間。只從名稱上來看,已經少了些意識形態色彩,即從“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換成了“民間投資”。“舊36條”基本上是就非公談非公,就民營談民營,讓人感覺是一個相對孤立的文件。“新36條”則基本上站在國家整體的經濟格局上,明確了國有資本要把投資重點放在不斷加強和鞏固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一般競爭性領域,要為民間資本營造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在提到民間資本準入的行業領域時,“舊36條”采用的是“允許”,如“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等等,而在“新36條”中把“允許”全部改為“鼓勵”。這種用詞的變化表明國家對民間投資加大了重視的程度,并將對民間資本健康發展采取積極推動的態度,體現管理層“調結構”的決心。“舊36條”是對打壓民間投資的糾正,而“新36條”則是對2009年以來的4萬億投資導致的“國進民退”進行扭轉。“新36條”旨在從源頭上對民間資本進行疏導與分流,讓其從投機短炒中“改邪歸正”,進入實體經濟生根開花。
雖然“新36條”實施后國有資本在眾多行業中的壟斷地位短期內仍然難以打破,但民間投資的權益保障將得到顯著改善,對內開放的國民經濟發展思路正在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將逐步形成,“新36條”的戰略意義遠大于短期的經濟意義。“新36條”的突破在于:
(一)提出要扶持和引導民間資本的發展,而未提及外資。“新36條”是改革開放以來出臺的第一份專門扶持民間投資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意義,“新36條”不再強調要大力引進外資,而是將對內開放作為未來經濟工作的重心。
(二)對民間投資可進入領域的規定大大細化,可操作性強。“新36條”突出了執行性和操作性,提出了細化到二級科目的領域。“新36條”對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不是像“舊36條”那樣,只是列出了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等行業的名稱,而是細化到每個行業的具體項目領域以及投資方式。如對鐵路行業,提出“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鐵路干線、鐵路支線、鐵路輪渡以及站場設施的建設,允許民間資本參股建設煤運通道、客運專線、城際軌道交通等項目”,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民間投資可以獨資、控股方式進入的領域大為拓寬。“舊36條”規定,在鐵路、民航等領域,非公有資本可以參股等方式進入。在“新36條”中,雖然電信、核電站、石油天然氣等領域仍然只允許民間資本以參股形式進入,但允許民間資本獨資進入的壟斷性領域已大為放寬,可以獨資、控股、參股等方式,投資建設公路、水運、港口碼頭、民用機場和通用航空設施等。與“舊36條”相比,“新36條”第一次明確地把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政策性住房建設領域寫入了文件;鼓勵民間資本發起或參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金融機構,放寬村鎮銀行或社區銀行中法人銀行最低出資比例的限制。這是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的開端。

(四)打破了國有資本的“控股慣例”。“新36條”明確指出,“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合理降低國有控股企業中的國有資本比例。”這也是國務院首次在政策法規方面提出,允許民間資本在改制中控股國有企業,或者較大比例地參股國企改制。
二、“新36條”仍然缺乏政策細節支撐
從“舊36條”到“新36條”,包括其間還有諸多打破壟斷和給民資“松綁”的法律和政策,如《反壟斷法》的出臺,都未能讓民資走出游資的陰影,個中原因值得深思。理論上說,法律未禁止的民資都可進入,而且“舊36條”也已經提出降低壟斷領域的準入門檻。但關鍵是有形的門檻降低了,有形的障礙消除了,無形的門檻和無形的障礙卻依然存在,正是這些無形“玻璃門”和“彈簧門”的存在,導致很多壟斷行業對民資“名義開放、實際不開放”,或者“領了準生證,卻辦不下戶口”等問題。而“新36條”盡管“看上去很美”,但在一些關鍵領域則寫得很抽象,對中國民間資本的提振,還需要時間觀察。隨著準入門檻的進一步放開,其他無形門檻也要打破,民間資本才有可能真正進入相關領域。
“新36條”未來能否達到預期實效,關鍵取決于國家推行政策貫徹落實的決心和力度,以及今后細則措施的鋪墊施行。在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的同時,如何避免公共利益與私有利益沖突?民間資本進入壟斷性管制行業以后,權利歸屬是否能夠得到切實保護?民間資本進入壟斷性管制行業的資格如何審定?民間資本以什么形式、什么價格進入壟斷性管制行業?這些問題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辦法,“新36條”的出臺就有可能與初衷背道而馳,就會重蹈“舊36條”難以落實的老路。如果各方面有利因素配合得較為理想,國家調結構的意志堅決,那么,2010年有可能是真正的接下來一個經濟周期的“民間投資元年”。
天津社會科學院城市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