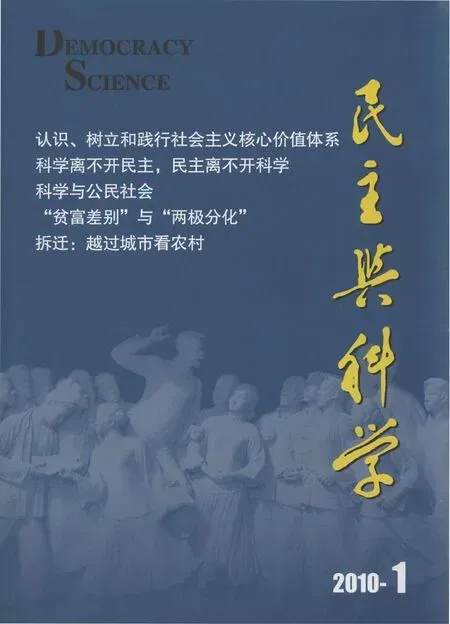科學與公民社會
■李大光
科學與公民社會
■李大光
科學研究學科分類的精細和研究手段的復雜,使得科學和技術與公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的撥款控制導致整個研究過程呈現出科學僅僅是政府和科學家團體之間的事情。但是,科學研究成果最終體現在技術和工程項目的實現。公眾作為科學研究項目的納稅人的身份在整個過程中被隱去,科學研究的成果最終是否能體現公眾的利益成了難解之謎。時代似乎在呼喚公民社會的出現,但是,公民社會,談何容易。
飛速的科學與瞠目的公眾
近些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其迅速。科學的飛速發展再次引發公眾態度的變化,同時也深度沖擊了公眾的傳統認識和倫理意識。在科學事件中,最具有沖擊力的是對宇宙起源的探索和生命科學的最新研究,這些重大進展引發了人們的討論以及爭論。
2008年是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里基礎物理學研究發生重大變化。2008年3月,蘇黎世地下100米深處,歐洲科學家建立了強子對撞機實驗室。這個強子對撞機加速器中心規模巨大,27公里長的隧道橫穿法國和瑞士。它的能量使它能夠模仿宇宙誕生一千億分之一時候的物質狀態。其內部共有9300個磁體,其制冷分配系統的八分之一堪稱世界上最大的制冷機。在環形的對撞機軌道上,質子束以接近光速,以每秒6億次速度撞擊,產生粒子濃湯,科學家將從粒子濃湯中分離出反粒子,從而重現宇宙大爆炸的瞬間情景。這個對撞機的建立被認為是世界基礎物理研究中心從美國轉移到歐洲,從1999年以來,科學家基礎物理研究進展緩慢的狀況將會發生改變。物理學家希望通過大型強子對撞機對宇宙中種種神秘現象,如暗物質、超對稱粒子等展開新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目標是一種到現在為止尚未發現的次原子微粒,名為希格斯玻色子 (Higgs boson),被霍金稱為“上帝粒子”,它是人類現有理論預言中唯一還未發現的基本粒子。如果它根本不存在,那么傾向于多維時空的其它理論會變得更有說服力。英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霍金甚至拿出100美金打賭自己的黑洞理論將得到證實。但是,按照他的理論,黑洞將吞噬宇宙間所有的物質,甚至光都難以逃脫。消息傳出,歐洲輿論嘩然。很多人認為,科學家們拿著納稅人的錢應該為納稅人謀幸福和利益,這樣的研究違背了公眾的利益。許多社會組織用各種方式提出抗議。其中NGO組織和環境主義者,甚至一些科學家團體都走上街頭,提出抗議。消息傳到印度,中央邦的一個16歲女孩,竟然自殺。
但是,反對聲音最大的還是來自科學家內部。2008年9月10日,大型強子對撞機將要開展對撞試驗。對此,一些歐洲科學界人士聲稱,認為實驗產生的黑洞可以吞噬地球。或者,強子對撞機將產生一類名為“奇異微子”的粒子,將地球變成一團沉寂、收縮的“奇異物質”。他們甚至到法院起訴資助該項目的20個歐洲國家,要求停止或推遲這個項目。據“新浪科技”報道,在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聯邦法官面對科學難題,一直在猶豫是否要考慮聯邦政府的請求,駁回由前核安全專家沃爾特·瓦格納和西班牙科學作家路易·桑奇聯合提起的這起民事訴訟案。而位于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庭目前也面臨著同樣的難題:法院同意審議主要由德國和奧地利教授和學生提出的強子對撞機可能導致世界末日來臨一案。不過,法庭拒絕了他們提出的立即中止大型強子對撞機的請求。
該報道還說,不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的訴訟案中,原告都聲稱,關于這臺大型強子對撞機的描述均未能準確表達它可能帶來的危害,其中包括全球范圍的小黑洞及物質變異或單磁極化等等,要求對該項目開展進一步的安全評估。而被告方——美國能源部、歐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物理中心卻辯稱,一系列安全測試報告的結果表明,上述擔心完全沒有必要。上述安全報告由業內領先的高能物理學家執筆,認為,與強子對撞機的對撞相比,宇宙光的碰撞能量和頻率都要高許多倍。如果大型強子對撞機能引發全球大劫難的話,那么即便在最不可能的條件下,廣闊宇宙中早已應經歷了許多次災難。據說官司現在仍然在進行,公眾的示威和反對之聲仍然強烈。2009年8月13日,美國《斯坦福日報》公布了一個驚人的消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工程學家斯蒂文·奎科(Steven Quake)發明了商用人類個人基因組解讀器。任何想獲得自己的基因圖譜的人都可以僅僅花費48,000美金,在4個星期內就可以獲得自己的全部基因圖譜。自從1975年美國科學家桑格發明了基因圖譜解讀技術以后,科學家已經在1990年實行了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到2003年,個人基因圖譜解讀已經實現個人基因圖譜解讀費用為50萬美金。美國科學怪人溫特已經用100萬美金解讀了雙螺旋結構發現者詹姆斯·華生個人基因圖譜。斯蒂文·奎科的發明意味著今后任何人,只要購買回這個體積僅為冰箱大小的機器以后,都可以在家里就完成自己的基因圖譜解讀,了解自己的父親、母親和孩子獲得某種遺傳疾病的可能性。獲得基因解讀譜的人在知道了自己的身體情況以后,都可以根據自己患病的危險采取措施。比如通過干細胞移植技術修補自己缺損的基因。我們很難想象,采用這種技術以后,人類的壽命會有多長。但是,在這個驚人的科學成果出來以后,理論學家又開始擔憂,假如按照科學家所說,人類的壽命會延長到300歲甚至更長,那么,就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政治制度、教育體制都需要發生變化。與此同時,人類犯罪率會上升,人口劇增導致資源的緊張,甚至國家領土問題,以至戰爭的頻繁等等。
美國為了降低個人基因全圖譜解讀的成本,“X Prize”基金會準備拿出1000萬美金資助100個個人基因圖譜解讀,爭取在2012年將解讀價格下降到每個人5000美金。生命科學為我們帶來了科幻世界一般的未來夢想:當我們的孩子出生的時候,我們只需要交納幾千美金,在帶孩子出院的時候,就可以帶走一個載有孩子基因圖譜的光盤。在解讀以后,就可以基本知道祖父母、父母和后代遺傳疾病的可能性,甚至可以知道在某個年齡段將會患病,或者患遺傳病,甚至可以知道自己的壽命。在得知了遺傳疾病以后,就可以通過干細胞移植技術,在專門培養的迷你豬體內克隆自己的器官。通過一般的手術就可以進行器官移植。人的壽命將大幅度延長。但是,生命科學的飛速增長也會帶來宗教與信仰的沖突等問題。比如,當人類在發現通過干細胞可以克隆與自己身體器官相同的替代器官以后,人類移植肺、肝和心臟等器官都是完全可能的。
在生物技術給我們帶來福音的時候,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人需要得到醫療的時候,他該在自己的信仰和生命之間如何選擇呢?
朦朧中的中國公民
科學家與從事其他工作的人無異。他們都生活在某一個特定時代的評價體系中。科學家的成就與獲得課題經費,完成質量以及社會評價有關。技術開發人員與企業效益直接相關。科學家無論在實驗室還是在經濟社會中都具有明確的社會屬性。在不同的社會時期或者戰爭時期,科學就與當權者的利益相一致。二戰期間,為納粹工作的物理學家差一點趕在“曼哈頓計劃”前生產出原子彈。日本侵華戰爭中的“731部隊”中的醫學科學家應該是當時最優秀的科學家。同時,在納粹集中營中用猶太人和戰俘進行眼睛手術,以使他們更接近日耳曼民族的試驗的也是最優秀的科學家。科學家的科學活動不可能完全是純粹的科學目的。既然這樣,科學家活動的結果就有可能與普通公眾的利益不一致。那么,在科學家道德和社會約束機制不存在或者缺失的情況下,公眾的利益就很難保證。
近些年來,重大的與公眾利益相沖突的事件不斷出現,其中很多事件與科學、技術和工程相關。比如,薩斯、禽流感、圓明園防滲膜事件、“漢芯”事件、太湖巢湖藍藻事件、西部水利大開發爭論、怒江大開發的爭論、廈門PX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中西醫爭論、偽科學的爭論、珍奧核酸事件、轉基因農作物、蘇丹紅、蒙牛OMP、安全飲用水、院士作假、華南虎、三鹿奶粉事件、垃圾焚燒等等。我們的調查顯示,盡管公眾對科學技術還是持積極支持的態度,但是,他們對科學和科學家團體的信任度在下降。其中一個不信任就是信息不透明。
法國科學傳播教授比埃爾·法雅赫(Perrier Fayard)認為世界上科學傳播信息基本存在兩種模式:第一種是計劃模式。這種模式是傳播者將自己要傳播的信息事先準備好,然后在一個信息傳播處(比如科學技術館或者科技節)將至少80%的自己要說的話展示出來。但是這種模式只會吸引來對你準備的話題感興趣的人,而不了解這個領域知識的人就會嚇跑。另一種模式就是自由模式。這種模式只事先準備很少的信息,而安排很多有關科學家在現場進行解釋和回答公眾提出的各種問題。比埃爾認為,第一種模式告訴公眾的是信息,而不是科學。只有第二種模式才能完成真正的科學傳播任務。因為他們告訴公眾的是公眾最需要的。第一種模式雖然效果不好,但是,轟轟烈烈,場面熱鬧,這是政府最喜歡的模式。第二種雖然不那么熱鬧,產生的效果更好。政府或者科學家團體在躲避自身責任或者追求效應方面一般會采取以政府目前的利益為主。避重就輕或者將自己的利益隱含在一種隱晦的說法中,是慣用的手法。在廈門PX事件中,在不得已而必須召開的公眾聽證會上,負責環境評估的化學家將“所有的”環評報告和各種數據都提供給了聽證會的聽眾。你不能不說他的態度是公開的。但是,所有面對復雜的化學公式和數字的人,除了罵自己上大學的時候沒有選擇化學作為自己的專業以外,得到了什么呢?出色的“科學普及”和坦誠的“科學結果公開化”,將自己的結果得到最有效的保密。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趙玉芬這樣的科學家,如果沒有公民自發的“散步”,如果沒有兩會期間104位良心科學家的聯名動議報告,如果沒有那位新華社記者的數碼相機將報告直接送到溫家寶總理的桌子上,廈門政府會有最后的“英明決策”嗎?
為了保證科學符合公眾的利益,1989年在丹麥誕生了“共識會議”制度,很快傳遍全世界。每當一種新技術要使用或者新工程要上馬,科學家共同體或者有關部門要召開公眾聽證會。這種模式被稱為丹麥模式。美國科學基金會在研究項目確定以后,都要將研究內容在網上公布,所有的人都可以登錄查看,發表自己的看法。當然,反對一個科學研究項目也可以上街游行。公眾反對聲音大的項目,很可能導致下一次評審時受到影響。在重大的資源開發項目過程中,比如,在舊金山要開發油田的時候,必須進行公民投票。一種只要發動,無論是在白天還是黑夜,車燈都會大亮的新車制造技術也需要得到公眾的聽證會同意。其實,理由也很簡單,因為這是大家的事情,這是大家共同擁有的財產,使用必須經過大家同意。如果你真心是在獲得大家的同意,那么,你就一定會使用大家都懂的語言。牛頓早在將近300多年前就說:“虛假的事物可以隨意想象,惟有真實的事物才能被理解。”如果你說的是真實的,你一定會被人理解。如果你的假話被人揭露,你的人格也就失去。
中國社會在飛速發展,科學技術也在飛速發展。快速的發展使人欣喜,但是,短桶板效應就會凸顯,那就是,公眾不理解,在不理解的同時,任何打著科學旗號的東西他們都信以為真。中國的公眾是世界上最憨厚樸實的公眾。他們熱愛和崇拜任何一個主流聲音推崇的東西。但是,樸實憨厚的人還有另一個特征,就是一旦發現自己被忽視或者被欺騙,他們又很難重新燃起往日的熱情。中國的科學傳播必須將真實的科學發展告訴公眾,人民才會擁護你們,科學事業才會有美好的前途。
公民社會是怎樣煉成的
科學發展導致利益集團運作的手段的多樣化。地方政府利用科學追求經濟利益;企業利用實用技術開發新產品占領市場;科學家和學者利用科學研究成果獲得學術成就,從而獲得經濟利益。惟有手無寸鐵的公眾,除了采取“散步”的唯一方法,誰來保證他們的利益呢?最近不斷出現的垃圾焚燒事件,再一次將公眾的利益引入社會議論中心。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認為,大眾階級形成維持國家秩序的政權國家。大眾賦予了政府管理國家的權力,通過法律維護社會的穩定。這種通過“君權民授”的方式,使得整個社會得以運行。國家(state)的穩定取決于公民社會是否存在以及這個公民社會的活躍程度。這個公民社會的活躍與否取決于他們法律的認可與允許、國家管理信息的透明程度、公民對自身利益的敏感性、討論自己利益的自由度、討論結果信息的發布有效性、公民選舉權與參與決議權。
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英國、法國、荷蘭等處于工業化前期的國家,在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及維多利亞時代赫胥黎等人的大眾科學運動的催生下,歐洲的公民社會迅速形成。首先是英國的科學咖啡館(CafeScientifique)和法國的沙龍公眾輿論聚集團體的形成。天文學的一系列重大發現引發了人們對生命的起源以及宇宙的形成,甚至上帝的存在等問題的討論。生產與銷售科學儀器的公司開始出現,科學儀器進入到貴族家庭和公園。更有甚者,貴族們籌資購買山頭,建起天文觀測站。發展勢頭之猛,導致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科學咖啡館至今仍然是歐洲最主要的談論科學的場所。
在公民社會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公民自己的理性思考和信息的有效表達。馬丁·路德·金曾經說:“歷史將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喧鬧,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
沉默的原因值得追究。首先是公民自身的覺醒意識。在科學技術事件中,公民作為納稅人,首先應該知道支持科學家的活動的經費來自公民的納稅。最近,美國“科學怪人”克瑞格·溫特(Graig Venter)采用第二代基因解讀技術成功進行的個人基因圖譜解讀和斯蒂文·奎科(Steven Quake)在自己家里將自己的基因圖譜進行了解讀并開發出個人基因圖譜解讀器,使查尋遺傳疾病的方法進入到公民個人家中。他們的經費都是社會自行解決,也就是說,是公民社會自行解決的。前者的經費400萬美金是世界第一富翁比爾·蓋茨掏的,后者的經費完全是自己掏的。這是在高度發達的科學社會中才能出現的科學發展趨勢。也就是說,公民社會在意識到社會的需求的時候,居然能夠通過自己的財力解決科學問題。但是,大多數國家或者大多數科學技術項目中,公眾還是作為納稅人對科學技術進行投資。但是,在公民社會未形成的國家中,作為公民只有納稅的義務,卻并沒有獲得了解產品產出的權利。
中國的情況需要社會學家進行長期的跟蹤研究。在筆者過去20多年的研究中,發現中國公眾的幾個重要特征。
1.我們在過去的將近3年時間內,對不同經濟地區進行的公眾科學意識調查中發現,雖然公眾對科學家的行為已經不是絕對相信,但是對科學還是堅決支持。其支持的態度令人驚訝。他們中接近98%的人異口同聲的聲明,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應用科學研究,他們都堅決支持。甚至聲明:“即使再困難,我們勒緊褲腰帶也要支持!”
2.科學素養水平低。在2008年發布的美國《科學與工程學指標》(Science&Engineering Indicators)的國際科學素養比較中,我國公眾的科學素養水平不僅低于美國、日本、俄羅斯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甚至低于韓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在多項問項中,正確回答比例低到令人無法理解的地步。
3.但是,中國公眾對科學技術信息感興趣卻居世界首位。尤其是對科學新發現和技術新發明的信息尤其感興趣,盡管對醫學新進展感興趣程度不高。
4.盡管我們公眾的科學素養水平不高,對科學技術感興趣程度很高,但是,科學信息渠道卻十分有限。中國公眾與其他國家的公眾一樣,電視是他們獲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中國的電視臺科教頻道卻僅僅只剩下10個,而且多數都在從事商業或者娛樂節目。
5.生活壓力與信息需要的廣度成反比。這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特征,但是,在中國體現的極其鮮明。尤其在中國邊遠的落后地區,信息基本隔絕的村落和社區不在少數。甚至在北京邊遠的山區,竟然還有沒有電腦、沒有數字網絡的村落。農業種植收入是他們唯一的生活來源。生活的壓力使得他們的信息搜索范圍形成“管視”,甚至“點視”效應。他們不知道中國發生的重大科學事件,更不知道世界在科學技術領域中的發展對他們生活所具有的潛在的影響。他們不僅不知道高錕發明的“光纜”已經使得世界連為一體,甚至也不知道中國居然還發射過“神七”飛船。在科學技術發展如此快的今天,知識溝仍然不僅存在,而且發展趨勢以及如何構成的因素,我們并沒有認真研究過。
6.參與意識與自身利益成正比。大量的定性調查表明,我們的公民只有在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或者存在潛在的威脅的時候才會參與決策。近些年來發生的污染事件和資源開發等工程事件與公眾之間的沖突,多數發生在局部,甚至更小的范圍,比如社區和村子。公民沒有形成對作為整體社會公民的利益的思考,對自己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的思考,同樣也沒有理性思維群體,即輿論領袖的產生和活動。所有的事件是否會產生沖突完全取決于一個偶然事件,或者良心科學家的偶然出現。
公民社會形成的外在因素目前在中國還遠沒有出現。最值得考量的就是影響公民社會形成的輿論要素。媒體雖然處于轉型過程中,但是,這個轉型與改革初期的企業轉型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轉型取決于經濟運作模式和資本的再分配的模式轉換。前者取決于掌握權力的政府和國家機構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潛規則。兩種本質不同的“轉型”結果肯定是不同的。對中國媒體的市場化我持懷疑態度。在免費贈閱的科技類報紙、雜志和自己掏錢買的大眾類報刊和雜志中,可以明顯的看出距離政府越近的媒體越遠離科學與公眾利益的討論焦點。而目前技術和工程建設與利益的沖突卻越演越烈。對此,所謂“主流媒體”三緘其口。
媒體體現出應付工作的狀態。科學技術專業媒體遠離科學中心,而社會大眾類媒體卻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接近事件核心。2009年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儀式的中國媒體中只有《南方周末》記者在現場,對華裔諾獎得主高錕現場活動進行了報道,其他所有科技媒體一片沉默。中國的科學技術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由科學技術專業媒體轉向大眾媒體。
最近,國家領導人的表態似乎令人振奮。在2009年10月9日召開的世界媒體峰會上,胡錦濤談話中談到幾個關鍵詞:弘揚社會正氣、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搞好輿論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但愿,所有的號召都能得到實現。
(作者單位:中科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