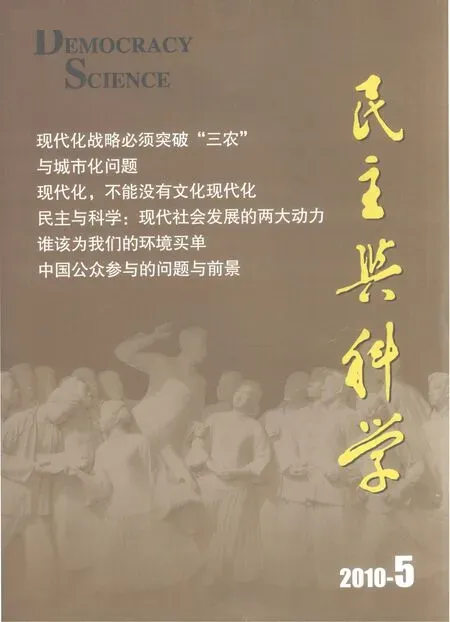好奇
——科學發現的原動力
■黃建海
好奇
——科學發現的原動力
■黃建海
筆者前不久剛從上海世博回來,可以說整個世博園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想象力與創造性相結合的樂園,許多人都說美國館沒意思,館內空空無也,可是美國館播放的幾段視頻所傳達出的一組信息卻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美國人看來青少年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創新是美國的基石;多元文化下的合作精神;以及堅定走環保與低碳的可持續發展之路。美國人認為創新最活躍的元素就是好奇心與想象力,誰抓住了少年兒童的好奇心與想象力,誰就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科學家心目中的好奇心
好奇心是學習動機的核心,是一種追求外界信息指向學習活動本身的內驅力,表現為好奇、探索、操作和掌握行為。從心理學角度來講,好奇心是直接推動個人進行學習探究活動的內部動力,屬于學習動機的內驅力。
許多科學家對好奇心都情有獨鐘,這是因為他們切身體會到了它的好處。美國化學家陶布說,一名科學家必須有好奇心,有動力而且執著。另一位美國化學家歐拉也說,好奇心促使人類做許多事情,尤其是科學。美國生物化學家伯格則說,教育對人一生最大的影響是幫助你發現好奇心和培養你尋找有創造性答案的直覺。
美國物理學家惠勒,4歲時就對宇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天他問母親:“宇宙的盡頭在哪里?在宇宙上我們能走多遠?”母親的回答當然無法滿足小惠勒的好奇心,但母親的回答卻絲毫沒有傷害兒子的好奇心。惠勒清楚記得他當時的心理反映是什么樣子的,他說:“這讓我內心產生了無比的好奇。”不過惠勒的行為并沒有停留在想象上,而是開始了向書本請教,印象最深的就是讀了約翰·阿瑟·湯姆生的《科學大綱》。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惠勒開始了自己的科學探險,在屋里研制瓶裝火箭,從此走上了科學啟蒙的道路。
貝弗里奇在《科學研究的藝術》一書中關于好奇心的作用與原理時這樣寫道:“好奇心激發青少年去發現我們生活的世界:哪些堅硬,哪些柔軟,哪些可動,哪些固定,發現東西向下墜落,水具有稱之為液體的特性,以及其它一切我們適應環境所必需的知識。”
貝弗里奇可以說是研究科學學的專家,他這里其實是將好奇心與知識的獲取聯系起來,也就是說,好奇心是發現和探究新知識的源泉。好奇心主要是對未明現象、事物和知識的探求,而我們時常所說的知識學習,主要是指對已知的了解和掌握,弄清楚好奇心與知識學習兩者之間的區別這一點很重要。好奇心不是知識,但遠比知識更重要,因為好奇心是發現和探索新知識的動力源泉。知識淵博的人未必對科學好奇,但對科學非常好奇的人,一定具有飽滿的科學熱情、頑強的科學意志、積極的科學態度、崇高的科學境界以及堅定的科學精神,而所有的這一切才是科學真正的魅力之所在。愛因斯坦也認為,他的科學成就來自“研究問題神圣的好奇心”。他說:“推動我進行科學工作的是一種想了解自然奧秘的抑制不住的渴望,而不是別的感覺。”為什么會是這樣子的呢?巴甫洛夫的話給出了答案:“我們達到了更高的水平,看到了更廣闊的天地,見到了原先在視野之外的東西。”這就是科學好奇最好的回報,對此丁肇中說:“好奇心是科學研究的原動力。”
好奇心屬于兒童
好奇心是重要的科學品質,但它主要萌芽于童年時期,可以說好奇心屬于兒童。因為兒時的大腦一片空白,可以任由思維的世界擴張、放大,沒有任何條條框框限制思維的飛揚。一個新生命從呱呱墜地睜開雙眼的那一刻起,他就開始對這個世界感到莫大的好奇。
美國生物學家霍普菲爾德認為“兒童天性好奇”。“他會戳戳甲蟲看看它們的反應,扔根樹枝在小河中觀察它漂多遠才沉沒;他喜歡拆開玩具看個究竟,也會對水流進排水溝便不見蹤影感到驚奇”。在霍普菲爾德看來,童年就是好奇的代名詞。
199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保爾·博耶,絕對屬于那種打小時候起就對科學非常好奇的科學家,因為他從一走進校門就對生命現象非常著迷,幼小的心靈里裝滿了對于生命現象的疑問和好奇。他說:“我上中學的時候開始對許多生命現象感到好奇,曾經考慮過諸如植物是怎么生長的,肌肉又是怎樣收縮的等問題。這些問題非常復雜,你在宗教中找不到答案,只能去科學中去尋找。”
2001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獲得者保羅·諾斯對好奇心也格外垂青:“我想不僅是我,很多科學家共有的特點是擁有好奇心,對世界擁有好奇心。只有擁有了這種好奇心,才會有動力進行研究。”至于這種好奇心,特別是對于科學問題的好奇心從何時變成自覺的科學行為,保羅·諾斯說是小時候起就逐漸形成了:“大約是10歲的時候,我從報紙上看到前蘇聯的一顆人造衛星要經過倫敦,晚上我就走出房子望天,真的看到了那顆衛星劃破夜空而過,當時就覺得奇妙極了。于是,開始對科學有了興趣,實際上也是對周圍的世界感到好奇。”
好奇心的培養
好奇心實在太寶貴了,尤其是對于科學而言更是如此,因為科學是最富于好奇與想象,科學一旦離開好奇心的驅使就寸步難行。然而,好奇心尤其是科學好奇心卻非常脆弱。好奇心雖說是與生俱來的,但好奇心除了耐受性的一面外,還有脆弱性的一面,何者起主導作用,主要取決于好奇心是否能夠得到及時的呵護與激發。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勞夫林在回答清華大學學生提問時說:“每個人從小孩起就有好奇心,但這種好奇心到成年后就減少了,要注意這種變化。如果把兒童時的好奇心全丟了,成年后就沒有創造力了。所以保持兒童時的好奇心非常重要。”
好奇心的培養從創設問題情境做起。有人認為,猶太人母親很善于激發孩子的好奇心,她們常常會問放學回家的孩子:“你今天有沒有在課堂上問一些好問題?”其實,這就是試圖通過問題情境的創設激發孩子對科學的好奇。疑問是產生好奇的第一步。疑問生好奇,好奇生動力,科學探索的航船就這樣起程了。我國老一輩教育家陶行知認為只要兒童有疑問,就要鼓勵他提問。他指出,兒童只有言論自由。特別是問的自由,才能充分發揮他的創造力。發明千千萬萬,在于一個問……為此,他強調要解放兒童的嘴,使他敢問。
1962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獲得者弗朗西斯·哈里·康普頓·克里克,小的時候就是一個特別能提問題的孩子,而且他所提的問題讓人覺得哭笑不得。不僅如此,小小年紀的克里克內心深處就有一個憂慮,他總是擔心長大了以后,問題被別人研究完了怎么辦。細心的母親敏銳地覺察到兒子的心思,及時買了本《兒童百科全書》作為禮物送給克里克,克里克這才發現原來科學問題是層出不窮的,從此小克里克像一只張開了科學翅膀的鳥兒,任憑好奇心在科學王國自由地飛翔:“我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如果我的熱情被激發了起來,我就會去分析它、探索它,并且我是愿意努力工作的。”
少年的科學好奇心需要借助實驗與動手能力加以維持。少年不僅好思好問好想象,少年也好動手。而是否喜歡動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好奇心的耐受性和持久性。也就是說好奇心的產生是容易的,但要將其保持下去就沒那么簡單了,它需要一定的條件。奧托在《人類潛在能力新啟示》一文中指出:“我們應當激發求知的好奇心,需要新的經驗,需要冒各種風險,深入人類潛力的各個領域及發展中心。在發展中不怕冒險。”
其實仔細想想,道理就這么通俗易懂。大凡人類好奇的東西,都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正所謂無限風光在險峰。之所以好奇就是因為想象力難以達到,之所以好奇就是因為它充滿著驚險與刺激,之所以好奇還因為充滿著探索過程的無窮樂趣。要滿足好奇心的需要,當然少不了學習,也必須承受探究過程中各種可能的風險。許多科學家早在童年時期就開始進行朦朧的科學實驗,實驗過程中無論是意外的失敗,還是意外的發現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這樣的刺激冒險,以及新發現的無比喜悅和對新問題的再追思,在這樣的準科學實踐探索過程中,少年的那顆科學好奇心,就像是注射了強心劑一樣不斷得到強化,科學探索的勇氣和信心也增強了。
然而應試教育是好奇心的天敵。如今的孩子成天圍著分數轉,學齡前就開始展開分數比賽,一直到完成高考這個階段性任務,考試成了伴隨孩子走完青少年之路的緊箍咒。好奇需要的內在心境沒有了,好奇需要的外界環境與土壤也沒有了,好奇心的日子還能好過得了嗎?與分數比起來,好奇心值幾個錢,中國父母向來是看不上的,甚至壓根兒看不見孩子身上的好奇心。他們比誰都清楚,一分之差孩子的命運就可能截然不同,一個進了重點,一個成了所謂的差生,一個進了高等學府,一個淪落為失學青年。在應試教育的現實面前,分數主宰一切,好奇只得靠邊站,再說沉重的學業負擔,加上沒完沒了的補課、考試就夠孩子們疲于奔命的了,哪來心思好奇與幻想。用父母的話說就是,哎,別傻愣在那兒了,還不抓緊時間做作業。
正確的科學教育是培養和保持好奇心的主要途徑。2010年5月21日,美國科學教師協會總干事長杰拉爾德·惠勒博士接受了中國科協網“在線訪談”,他在訪談中表示,科技教育可以保持人們童年就有的好奇心,不至于隨著年齡增長衰退;而在科技教育中,老師們要對孩子有足夠的愛心和耐心。
貝弗里奇的研究發現,如果方法不得當,保護不及時,好奇心很可能轉移不到智力興趣上,而是早早地夭折了。
好奇心與知識積累的關系不僅不呈現正相關,相反,如果不能正確對待好奇心與知識積累的關系,知識的積累很可能成為好奇心增長的羈絆。貝弗里奇認為,隨著年齡和知識積累的增多,好奇心往往成衰減態勢。因為,我們自以為自身的知識儲備已經足夠應付學習與工作的智力需要了,于是好奇心逐漸退出思維的前臺。尤其是習慣于接受知識灌輸的人,好奇心衰減得更快。知識特別是死記硬背而來的知識在大腦里積累的越多,給好奇心迸發的思維空間就越來越少;而知識的灌輸,不需要好奇心,一旦好奇心不再被刺激、被激活,就很可能逐漸枯竭。要保持持久的科學好奇,就需要不斷地刺激好奇心,使其保持興奮狀態,科學家就能做到這一點。科學家與普通民眾的區別就在于,他通常能覺察到常人所覺察不到的東西,也就是我們時常所說的,見人所不見,聞人所不聞,疑人所不疑。貝弗里奇把科學家的這種行為,總結為:“科學家通常具有一種強烈的愿望,要去尋求其間并無明顯聯系的大量資料背后的那些原理。這種強烈愿望可被視為成人型的或升華了的好奇心。”
這就是為什么說應試教育是好奇心的天敵,因為應試教育典型特征就是知識灌輸。知識被硬填塞進大腦,被動地授受,而不是主動地探究與積極思考,知識在好奇心活躍的狀態下,才最具有活用的價值而不是僅用來應付考試。
(作者單位:深圳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