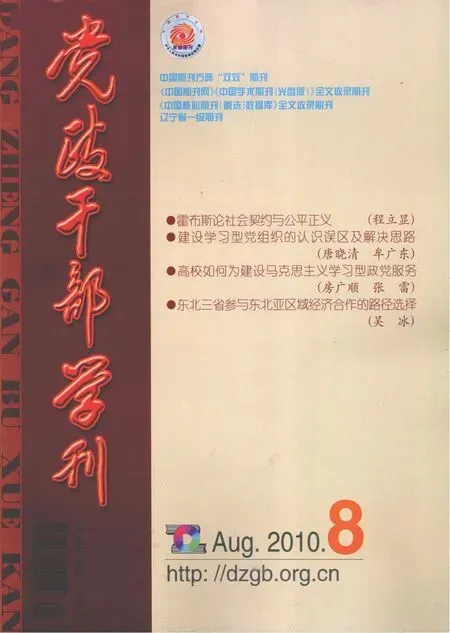霍布斯論社會契約與公平正義
程立顯
(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霍布斯論社會契約與公平正義
程立顯
(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霍布斯的人性論主張,自然狀態下的人類始終處于“每一個人反對每一個人”的戰爭之中,沒有道德和公正可言。這種人性論蘊含著人類平等觀念,具有反對神學倫理的歷史進步性。他將自然狀態和利己理性同公民契約相配合,奠定了維護統治者權力的社會契約論基礎,建構了契約論的公平正義觀。其社會契約論推翻了君權神授之說,又保留了專制主義特征。它一方面賦予統治者以絕對權力,同時主張統治者不得違背契約授權而不公平地對待臣民,主張唯有保障財產權的政府按約行使權力,才能實現公平正義。因此,統治者必須服從自然法,遵守社會契約,依法實施分配公正,而被統治者則必須履行法律義務。霍布斯的思想遺產具有不可磨滅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其契約論公正觀深刻地影響了近代以來的公正哲學,影響著當代社會的公平正義。他將倫理思想和公平正義奠基于人類永恒不變的利己本性之上,為專制主義作哲學辯護,則是其理論失足之處。
霍布斯;自然狀態;人性論;社會契約;自然法;公平正義
托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1588-1679)是英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之一,也是西方近代自然法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經典著作《理想國》、《政治學》、《倫理學》一樣,霍布斯的名著《利維坦》(1651)也涵蓋了政治學、倫理學、形而上學等學術領域,——倘若依照20世紀以來的學科分類,則可以恰當地稱之為政治倫理學經典著作。霍布斯重新闡釋了古希臘的原子唯物主義,試圖在他的近代原子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倫理學體系(或許未能取得完全成功),試圖用物質運動來解釋包括道德在內的一切事物。作為古典自然法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下的人性令人頗感憂慮,——進入人類社會之前,人是這樣一種生物,其整體就是為了滿足各自的永不滿足的欲望而爭奪權力的永不休止的斗爭。正是從這種自然狀態下的人性論出發,他致力于用權力概念來解釋道德和公正,提出了為專制主義統治權力辯護的社會契約論,論證了基于社會契約論的公平正義觀。
一、自然狀態下的人性論:“每一個人反對每一個人的戰爭”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狀態是自然法學者借以思考國家和政府之邏輯前提的重要概念,它所描述的是存在于任何國家或公民社會之前的人類生存狀態。正如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指出的:自然狀態并非指稱人類文明之初的真實的歷史狀態,“它應被理解為一種用來達成某種確定的公正觀的純粹假設的狀態”。盡管它是純粹假設的人類生存狀態,但在霍布斯那里,卻始終具有現實化的可能性,——對國家主權即統治者權力的任何限制,都意味著可能由和平狀態退回到 “每一個人反對每一個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正是借助于對自然狀態的假設性描述,霍布斯提出了當時和以后屢遭譴責的獨特的人性論。
霍布斯的人性論及其歷史進步性
在中外倫理學史上,道德理論總是同人性論密切相關的,因為后者總是構成倫理學體系的基礎或者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這個倫理學基本問題上,霍布斯為后人留下了極其重要的思想遺產。對于“是什么破壞了19世紀40年代英國的政治秩序”這一問題,霍布斯借助于對自然狀態下人性的描述給出了他的答案:
……在人類天性中我們發現:有三種造成爭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競爭,第二是猜疑,第三是榮譽。
第一種原因使人為了求利、第二種原因使人為了求安全、第三種原因使人為了求名譽而進行侵犯。在第一種情形下,人們使用暴力去奴役他人及其妻子兒女與牲畜。在第二種情形下則是為了保全這一切。在第三種情形下,則是由于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如一言一笑、一點意見分歧,以及任何其他對其本人的直接藐視,或是間接地對其親友、民族、職業或名譽的藐視。
因此,不難看出,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于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
這種戰爭是每一個人反對每一個人的戰爭。因為戰爭不僅存在于戰役或戰斗行動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戰斗進行爭奪的意圖已普遍為人所知的一段時期之中。因此,時間的概念就要被考慮到戰爭的性質中去,就像考慮氣候性質時那樣。因為正如同惡劣氣候的性質不在于一兩陣暴雨,而在于一連多日的下雨傾向,戰爭的性質也不在于實際的戰斗,而在于整個沒有和平保障的時期中人所共知的戰斗意圖。[1](引自商務印書館中文版《利維坦》,譯文稍有改動。以下凡引該書,同此。——作者注)
這是霍布斯闡述其人性論的經典文本。在他看來,作為一個自然生物,人的自然本性首先在于求自保、求生存,因而是自私自利、恐懼、貪婪和殘暴無情的,因而人與人總是相互防范,相互敵視,爭戰不已,像狼和狼一樣處于可怕的自然狀態之下。由于人的求利、求安全、求榮譽的本性永無止境,故其貪婪程度遠甚于其他動物。其他動物在滿足食欲之后便會安靜下來,而人的食欲以及其他各種欲求則永無滿足之時。因此,生活于自然狀態下的人類始終處于 “每一個人反對每一個人”的戰爭之中,這是一場殘忍地反對其他一切同類的無休無止的戰爭。這就是霍布斯的備受譴責的人性論——自然狀態下的“人性惡”論。
但對于這種“譴責”,必須著重指出兩點。第一,所謂霍布斯的“人性惡”之說,乃別人或后人所給出的善惡判斷。而在霍布斯本人看來,這純粹是 “自然本性”、“人類天性”,而“人類的欲求及其他情感,本身實不是惡”。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下沒有任何道德可言,不存在誰是好人壞人的問題,因為“善惡之意義、對象之價值,隨著個人欲望因時因地的不斷變化而改變,在這種情形下,也就不存在是與非、公正與不公正之分,也無好人與壞人之別”。[2]第二,霍布斯視利己自保為人類天性的人性論,同當時盛行的基督教原罪說是根本對立的。有學者指出,正是基于這種人性論,“在使道德哲學擺脫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束縛中,霍布斯邁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作為早期啟蒙思想家,他一反基督教從神性中引申出道德的做法,而把人作為道德哲學的出發點,主張以人性為基礎來說明道德”,[3]因而開創了近代功利主義倫理學說的先河,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因此,退一步說,就算霍布斯所主張的是“人性惡”,他的這種人性論也具有鮮明的反對神學倫理的歷史進步性。這種進步性在其人性論所蘊含的人類平等觀念中表現得尤為顯著。
霍布斯的人類平等觀念
霍布斯所主張的自然狀態下的人性論,蘊含著樸素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在他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對在自己看來是其生存所必需的東西也平等地擁有權利。在這里,平等指的僅僅是人們具有傷害其鄰人,以及為了自保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的能力。力量上的差異早晚會被克服,而且弱者也可以毀滅強者”。[4]他將人們平等擁有的這種權利稱為“自然權利”,也就是 “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5]霍布斯寫道:
“自然使人在身心兩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時某人的體力雖則顯然比另一人強,或是腦力比另一人敏捷;但這一切的總和,也不會使人與人的差別大到使這人能要求獲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樣要求的任何利益,因為就體力而論,最弱的人運用密謀或者與其他處在同一種危險下的人聯合起來,就能具有足夠的力量來殺死最強的人。”[6]
不僅如此,霍布斯還發現“一種存在于人們之間的比體力平等更大的平等”。他試圖證明人類天性中例如謹慎、智慧等能力方面的平等,由此“產生出達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因此,按照霍布斯的理論,自然狀態下的人類,拼命而又平等地為自身利益進行著反對其他一切人的生存競爭:“每個人的自愿行為,其目標總是某種自身利益”,因而“每一個人都應當承認他人與自己生而平等”。[7]
顯而易見,霍布斯的人性論所蘊含的人類平等觀念,實際上就是主張在自然狀態下相互為戰與自利自保的自然權利面前,人人“生而平等”。這種“自然權利,人人平等”的主張,成為后來西方思想家的“天賦人權,人人平等”乃至一般的“權利平等”、“自由平等”之類道德主張的先聲。自啟蒙運動以來直至今日,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權利平等”被逐步公認為社會公正或公平正義的第一原則。
然而,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權利平等”同公平正義是不相干的。他根據其人性論得出的推論是:在社會得以形成之前,公正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因而對于使用暴力強迫人們進入文明社會,不可能提出道德上的反對意見。如前所述,在他看來,對于生活在純自然狀態下的人們來說,道德與不道德、公正與不公正、善與惡的概念是不適用的,——此類概念只適用于文明社會的人們。霍布斯寫道:“在沒有公共權力的地方就沒有法律,而沒有法律的地方就無所謂公正不公正。暴力與欺詐在戰爭中是兩種基本德行。公正和不公正既不是肉體官能也不是心理官能……它們是同社會的人而不是獨居狀態的人相關的品質。”[8]
綜上所述,在霍布斯看來,公正話題乃是人類在理性照耀下締結契約、進入公民社會之后的事。“理性產生契約,契約孕育公正”。霍布斯所論述的恐怖的自然狀態和利己主義理性同公民間的契約相配合,為他所論證的維護統治者權力的社會契約論奠定了基礎,進而建構了他的契約論公平正義觀。
二、社會契約、公平正義與統治者的絕對權力
霍布斯認為,“每一個人反對每一個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是受自然法支配的,——自然法(natural laws)就是一種合乎理性的規律或法則,即“理性所發現的誡條或一般法則”。早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就認為有一種無論在哪里都具有同樣權威的、使用理性可以發現的自然法或正義法則。17世紀的荷蘭法學家格老秀斯也相信,宇宙是由有理性的自然法所統治著的。[9]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詳細論證了十幾條永恒不變的 “理性自然法”,其中“第一自然法”是:“每一個人只要有獲得和平的希望,就應當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時,就可以尋求并利用戰爭的一切有利條件和助力。”這就是說,每一個人既要“尋求和平、信守和平”,又擁有“窮盡一切手段以自衛”的自然權利,因為人人都是生而自由的,人人都有保存自己、企求安全的欲望,人人都有大自然賦予的理性與平等權利。不難想象,人們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下總是處于對暴力的恐懼和危險之中,生活得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霍布斯認為,為了擺脫如虎狼之境的自然狀態,避免無政府狀態,人們只有遵照理性所啟示的“第二自然法”的命令,尋求有組織的和平生活。這就要放棄某些權利和自由,達成一種社會契約,從而創造出“偉大的利維坦”,亦即公民社會或國家。[10]
社會契約創造了國家和統治者
霍布斯對“第二自然法”的表述是:“在別人也愿意這樣做的條件下,當一個人為了和平與自衛而認為有必要時,會自愿放棄這種對一切事物的權利;而在對他人的自由權方面滿足于同自己讓他人對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權相當的權利。”[11]于是,在理性的驅使下,依據“第二自然法”,人們便相互締結社會契約,甘愿放棄原來享有的自然權利,并把它托付給統治者或主權者,也就是“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托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12]由此便建立了國家,確立了統治者或主權者。霍布斯認為,國家或統治者的本質,“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訂立契約,每人都對它的行為授權,以便使它能按其認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衛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的一個人格”。[13]在霍布斯看來,正是這種社會契約,導致了“偉大的利維坦”的誕生。
由此可見,按照霍布斯的理論,國家不是根據神意創造的,而是人們經由社會契約創造出來的;統治者的權力或君權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轉讓和托付的;創建國家、確立統治者權力的目的是出于人們的理性和幸福生活的需要,以便“抵御外來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以便保障大家能通過自己的辛勞和土地的豐產為生并生活得很滿意”。[14]如此一來,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便推翻了中世紀的君權神授之說,摧毀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
與此同時,霍布斯的思想又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他那個時代的專制主義特征。他所設想的結束自然狀態的社會契約,是要建立起一種幾乎無限的、令人生畏的國家權力,規定人民必須對統治者的權力無限忠誠,以制約群眾而確保社會秩序。根據這種契約論,霍布斯極力擁護君主制度,認為君主的權力一如其權威,是絕對的權力,它只對上帝負責,臣民必須絕對服從。正是這種令君主擁有絕對權力的主張,使霍布斯贏得了“統治者權力的偉大的哲學辯護士”的稱號。
然而,值得注意是,霍布斯的“偉大”之處,不光是他對統治者權力的“哲學辯護”,更有他對統治者權力的 “授權設限”。他強調指出,君主的權力既然是由臣民公平地集體締約授予的,君主就不得違背契約授權而不公平地對待臣民。因此,從原則上說,臣民可以違抗背約的君主;人民有權不服從非正義的統治者。人民必須服從的是 “守約踐諾”的統治者,也就是維護公平正義的統治者。這是由霍布斯的 “第三自然法”——“所訂契約必須履行”——所決定的。順便指出,后來的許多啟蒙思想家例如康德等人,均主張人民對不義的統治者擁有反抗或革命的權利,這一思想顯然得益于霍布斯的理論啟示。
公平正義的泉源及其權力保障
霍布斯說,沒有 “所訂契約必須履行”的“第三自然法”,“契約就會徒具虛文,而所有的人對一切事物的權利就會仍然存在,人們也就會仍然處在戰爭狀態之中”。他認為,這一自然法是產生公平正義的泉源,“因為沒有契約出現的地方就沒有權利的轉讓,每一個人也就對一切事物都具有權利,也就沒有任何行為是不義的。在訂立契約之后,失約就成為不義,而非正義的定義就是不履行契約。任何事物不是不義的,就是正義的。”[15]在霍布斯看來,“正義取決于事先存在的契約”,“履行契約則謂之公正”。
然而,如何確保所有締約方都能履行契約呢?這就要訴諸國家權力了。“在正義與不義等概念產生之前,必須先有某種強制權力的存在,強制人們以對等的方式來維持通過相互約定、作為放棄普遍權利之補償而獲得的所有權。”他說:“沒有所有權的地方就沒有不義之事;而沒有建立起強制權力的地方就沒有所有權,——那里所有的人對一切東西都擁有權利;因之,沒有國家存在的地方就沒有不義之事。由此看來,正義的本質在于遵守正當的契約,而契約的效力則依賴于足以強制人們守約的國家權力之建立,以及嗣后所有權的確立。”[16]
霍布斯認為,基于開明利己主義的理由,人們寧愿選擇政府也不愿生活于自然狀態。在自然狀態下,沒有任何強制實施契約的制裁手段。“而倘若沒有武力,任何契約不過是空話而已,根本無力保障一個人的安全。為了給予契約以武力支持,就必須訂立人們借以把自己的權利轉讓給公共權力的最初契約,這種公共權力就是統治人們的政府。”這就是說,唯有政府按約行使的公共權力,才能保障公平正義。
由此可見,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主張將絕對的統治權力授予政府。他在《利維坦》中以大部分篇幅討論了如何按約建立國家主權者及其權力的性質,以及根據自然法的理性原則所確立的臣民義務。他認為,按照柏拉圖的哲學傳統,國家統治者所需要的倫理哲學極為艱深;但要將他的 “思維的真理化為實踐的功用”,“主權者及其主要謀臣唯一必備的學識,就是自然法的公平正義法則”;每一個主權者,都要“讓臣民掌握公平正義之道”。[17]
綜上所述,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揭示了公平正義的三個要點。第一,在自然狀態下無所謂公正不公正;第二,在社會契約的條件下,公正就是履行契約,不公正就是不履行契約;第三,離開以權力為基礎的功利和便利,就不存在任何公正的標準,因為,要么公正為權力所強加,要么就無所謂公正不公正。
霍布斯贊同古老的道德箴言,即:公正就是 “使各人得其應得的永恒意志”。而他所理解的“應得”,就是人們放棄自然狀態下的無限權利以組成國家之后所得到的補償。因此,國家主權者根據自然法制定成文法,用法律確定財產所有權,將每人之應得分配給每一個人,便實現了公平正義。一言以蔽之,為了公平正義,統治者必須服從自然法、遵守社會契約,而被統治者則必須服從統治者制定的法律,履行法律義務。
三、服從法律的責任與自然權利
在西方倫理學和政治思想史上,“服從法律的責任乃基于契約”這一觀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智者學派和柏拉圖——他們試圖把道德主體同道德客體相統一——而在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的著述中達于鼎盛。最近幾十年來,社會契約論不但作為公民服從法律的理論基礎、而且作為整個道德的理論基礎,在羅爾斯等人的著述中再度復興。按照這一理論,道德律或道德原則均為社會契約的產物,而且只有理性的人才能夠加入社會契約。社會契約是理性人之間達成的協議,要求人們以一定的方式對待他人,只要自己得到同樣方式的回報。比如說,“我同意尊重你的東西的所有權,以換取你同意不侵占我的東西”。社會契約可以視為適用于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人民允諾服從統治者,反過來統治者也要承諾合法地實施統治。但更為普遍的看法是,社會契約是為處理人們的相互關系而締結的。他們同意建立一定的立法機構和程序,共同服從法律的約束。盡管歷史上并未真的締結過此類契約,但契約論對于西方倫理思想的發展和近現代法治建設是很有意義的。
霍布斯看自然法和成文法
如前所述,霍布斯社會契約論的假定前提是:人就其本性而言是惡的。因此,他可以避免作為社會契約之基礎的大多數自然法學說可能陷入的矛盾。眾所周知,一切自然法學說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要證明成文法的制定或者有資格制定成文法的國家之存在的道德合理性。在發揮這一功能時便產生了矛盾:一方面,大多數學說認為人性是自然法的來源,這表明人性必須基本上是善的;另一方面,它們又只能通過人性惡才能證明成文法及予以強制實施的國家機器的必要性。然而,按照霍布斯的人性論,自然法實際上不是別的,就是這么一條原則:被賦予無限權力制定成文法的國家是必不可少的;根據自然法,人們有義務無保留地服從由國家制定的成文法,——這是一種等于用自然法否定自然法的論證方式。關于自然法與成文法的關系,霍布斯寫道:“自然法與成文法相互包含,二者涵蓋的范圍相同。……自然法是世界各國成文法的組成部分。相應地,成文法又是大自然命令的組成部分。國家的每一個臣民都已立約保證服從成文法,……所以服從成文法也是自然法的一部分。”[18]
根據霍布斯的理論,自然法的唯一功能就是要證明成文法——由有效政府所頒布的任何法律——的道德合理性。正是國家理性而不是個人理性決定了法律的內容,而這一法律既是成文法又是自然法。霍布斯明確主張,“我們這個人造的人——國家——的理性及其命令”造就了法律。這就是說,國家權力應該高于一切。這一觀點使他對權利和法律二者關系的闡釋別樹一幟。
霍布斯看法律和權利
從實質上說,霍布斯關于法律的觀點同中國古代法家頗多吻合之處,但明顯地不同于西方近代以來的 “法律保障權利”的法學理論。關于權利與法律的關系,他寫道:“權利(right)和法律(law)應該加以區別,因為權利意味著做或不做的自由,而法律則規定并約束人們去做或不做。所以,法律和權利的區別正如同義務和自由的區別一樣,二者指稱同一事物時的含義是不同的。”[19]
“法律即義務,權利即自由”,霍布斯對法律與權利之區別的這一認定,使權利概念失去了規范意義。霍布斯要說的是,當人處于“自然狀態”時,也就是處于法律與義務的真空狀態時,他的權利最多,因為“在此種狀態下,每個人都有權做任何事情,甚至對彼此的人身也可為所欲為”。但是,我們同樣可以說,在此種狀態下,誰都無義務“不強取己之所欲之物”,因而誰都沒有任何權利。那么,霍布斯是如何從“權利”進入“法律”的呢?
讓出權利或者屬于單純的放棄,或者是轉讓予他人。若讓出者不關心何人從中受益,那就是單純的放棄;若讓出者有意讓某個或某些人從中受益,那就是轉讓。一個人無論以何種方式放棄或轉讓權利之后,他就有義務或受約束不得妨礙接受他所放棄或允諾讓出的權利的人享有該項權益。
他應當不使自己出于自愿的行為歸于無效,這是他的責任。由于權利事先已經放棄或轉讓,所以這種妨礙便由于不具有權利而成為不公正或傷害行為。……單純的放棄或轉讓權利的方式,是以某種自愿而充分的表示,對接受者宣布或表明就此放棄或轉讓 (或是已經放棄了或轉讓了)該項權利。這種表示有時光是言詞,有時光是行為,而最常見的情形則是既有言詞又有行為。使人們受約束或承擔義務的契約也是這樣。這種契約之所以有約束力,并不是由于其本質(因為最容易破壞的莫過于人們的言詞),而不過是由于畏懼毀約后所產生的某種有害后果而來的。[20]
在就社會契約如何締結的問題作出以上說明的同時,霍布斯還指出:“像這樣放棄權利、轉讓權利的動機與目的,無非是保障一個人使他的生命得到安全,并保障他擁有既能保全生命又不對生命感覺厭倦的手段。”[21]因此,有一些權利是任何人都不會放棄或轉讓的,也不應誤認為人們會通過言詞或其他表示已經放棄或轉讓了這些權利。霍布斯列舉了締結社會契約后放棄和保留下來的權利,——保留的權利包括自衛權,“享用火、水、空氣和居住地以及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權利”。[22]但不同于具體契約的是,社會契約—定是假設性的。于是,在霍布斯看來,一切特定的社會機構的創立與維持均由統治者的法令為之,而統治者的權威則依賴于假設的社會契約:“每個人的契約均采取了每個人會向一切人承諾的相同方式”,承諾放棄自己的權利以支持政府,只要其他人都同樣如此。[23]按照這種契約論,服從君主或統治者是合乎理性的,除非這種服從將直接威脅自己的生命。
總之,在霍布斯看來,每個人的自然權利,就是 “每個人為了保持自己的本性,也就是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而擁有的采取自己的理性判斷所能想出的任何恰當手段,充分發揮自己力量的自由”。但這種自由或自然權利僅僅屬于自然狀態下的人。當人們脫離自然狀態進入國家以后,他們便交出了自然的自由權利以換得公民自由。這種公民自由,在霍布斯看來,不過是做法律所未禁止之事的自由,或者不做法律所未命令之事的自由。
憑借統治權力所制定的法律,本質上體現了作為公斷人的政府所實施的分配公正——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內容。
四、公斷人或政府的分配公正:公道與平等
在古往今來的任何社會中,社會成員的權利或利益的分配公正,都是公平正義的核心訴求。霍布斯認為,除非利益攸關者共同締約服從公斷人的裁決或利益分配,否則便不能獲致和平。他說:“自然法規定,爭議各方應將其權利交付公斷人裁斷。”[24]就全社會的利益分配而言,權威公斷人自然是統治者或政府。公斷人或政府的分配公正,是《利維坦》的中心論題之一。
分配公正乃公斷人的公正
霍布斯在論及公正類型時,引述了柏拉圖、亞里土多德以來關于交換公正與分配公正的分類:
著述家們把行為的公正分為兩種,一種是交換公正,另一種是分配公正。他們說前者成算術比例,而后者成幾何比例。因此,他們便認為交換公正在于立約的東西價值相等,而分配公正則在于對條件相等的人分配相等的利益。意思好像是說賤買貴賣是不公正的,給予一個人多于其應得的東西也是不公正的。一切立約議價之物的價值是由立約者的欲求來測量的,因之其公正的價值便是他們滿意地賦予的價值。……正確地說,交換公正是立約者的公正,也就是在買賣、雇傭、借貸、交換、物物交易以及其他契約行為中履行契約。
分配公正則是公斷人的公正,也就是確定“如何合乎正義”的行為。在這種事情中,一個人受到人們推為公斷人的信托后,如果履行了他的信托事項,就謂之將各人的應得份額分配給了每一個人。這的確是一種合乎正義的分配,可以稱之為分配公正,更確切的說法是公道。這也是一種自然法。[25]
他接著指出:
一個人如果受人信托在人與人之間進行裁斷,那么自然法就有誡條要求他平等對待,因為舍此人們的爭端就只有憑戰爭決定。這樣說來,裁斷偏袒的人便是濫用職權來阻止人們任用公正的公斷人,因之也就違反了基本自然法而成為戰爭的原因。
這一自然法是根據將按理應屬于各人的東西平等地分配給每一個人的法則而來的。遵守這一自然法就謂之公道。正像我在前面所說的,這也稱為分配公正。違反這一自然法就稱為偏袒。[26]
霍布斯把分配公正解釋為 “公斷人的公正”,即由公斷人來確定何為公正,其公斷行為必須不偏不倚。倘若公斷人有所偏袒,公斷機構就會失去信任,以后就不會有人找它“公斷”了。他認為,公斷機構應當成為促進公正和諧的工具。
按照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他對公斷人提出的道德要求同樣適用于統治者的權力。就全社會而言,作為公斷人的統治者權力最大,因為它是大多數人的權力在同意的基礎上集中于一個自然人或公民的手里,此人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運用集體的權力。很明顯,為了實現公平正義,即便是無限大的最高權力,也必須行為不偏不倚,辦事公道。《利維坦》專設一章,題為“論主權代表者的職責”,集中縷述了諸如制定良法、平等施法、公平征稅、對喪失勞動能力者的國家供養、正確賞罰以利國家、選賢任能充當參議人員等等政府職責,提出了政府權力之分配公正和公道的具體要求。霍布斯的這些思想和論述,對于當代社會之政府管理的優化和公平正義的實現,仍然不無借鑒價值。
“公道就要平等分配”
霍布斯認為,分配公正是“較為完全的公道”。同時,他按照字面意義理解“平等分配”的概念,認為“公道就要平等分配,平等分配具有自然法的性質”。那么,在霍布斯看來,公斷人的公正、公道同平等之間到底有何聯系呢?據認為,最符合霍布斯理論體系的答案是:人在自然力方面非常接近于平等,以致無法使除了平等之外的任何規則在自然狀態下得到普遍承認;因此,公斷人必須對有爭執的東西實施平等分配。然而,倘若這是對霍布斯的平等概念的正確解釋的話,則可以得出這一推論:如果當事人的相對能力很不平等,那就必然產生相應的不平等分配。由此看來,霍布斯的公道觀實質上符合于下述古老的公正原則:“平等地對待平等者,不平等地對待不平等者”。
事實上,盡管霍布斯聲稱“公道要求平等”,但他關于體力和智力之自然平等的論點,在社會狀態下不再具有決定意義了。人們有理由假定,社會狀態下的國家暴力總是支持富人、保護富人的,總是要反對窮人為要求平等地位而進行的任何暴力威脅的。因此,統治者宣稱的“社會公正”總是有利于強者和政府的利益,這就是所謂的“強權即公理”、“強權即正義”。霍布斯所經歷的早期資本主義的生活圖景就是如此,而他所提倡的基于財產權的公平正義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一社會現實的理論表現。
五、霍布斯的思想遺產與道德人格
麥金太爾在《倫理學簡史》中寫道:“無論如何,現在十分清楚的是,隨著路德和馬基雅弗利時代的來臨,我們期待著這樣一種道德—政治理論的興起,——根據這種理論,個人是基本的社會單位,權力是終極的關懷,上帝是日漸衰微卻仍未動搖的存在物,而前政治和前社會的永恒人性則是社會形態變革的背景。霍布斯充分地滿足了我們的這一期待。 ”[27]
是的,霍布斯正是這樣典型的思想家和時代產兒。作為社會契約論的思想巨擘,他大力倡導個人主義,削弱了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理論基礎,為接踵而至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理論支持;他的“利己的個人主義”人性論、人類平等論和公平正義觀,將道德的起源和本質從宗教神學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開創了倫理學功利主義的先河。此外,他還奠定了人學、公民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思想基礎,在這些當今堪稱“顯學”的學術領域,一舉成為“骨子里頭有精華,思想延續數百年”的巨匠。正如美國著名的霍布斯研究者列奧·施特勞斯所說:“沒有霍布斯的工作,道德哲學就是不可能的,不但18世紀的理性主義道德哲學是如此,而且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的道德哲學也是如此。然而最重要的是,如果說討論和闡明生活理想的確是哲學的首要和決定性的任務,那么,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作為對道德人生問題的一個根本性的答案,就不但對于作為一個知識門類的政治哲學本身,而且對于整個近代哲學,都具有至高無上的意義。”[28]
然而,必須承認,霍布斯的自然法和社會契約學說,錯誤地將倫理思想建立在人類永恒不變的“自我保存”的利己本性上,為擁有絕對權力的專制主義制度進行道德辯護,——這些理論失足之處,經常為后人所詬病。當我們研究霍布斯思想遺產的時候,有必要結合其道德人格,對這些理論失誤來一番科學的歷史分析。
霍布斯生活在17世紀中期的歐洲君主專制全盛時期,此時他的祖國正值內戰期間,遭受著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威脅。歷史學家一般認為,霍布斯之所以在人性問題上持憤世嫉俗的態度,之所以擁護君主制度,力倡解決政治問題的專制主義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他在英國清教徒革命期間的個人經歷,——他目睹了在長期內戰中個體人的性格和國家機構所受到的腐蝕。他的著作一經問世,就被斥責為不道德的、反宗教的和無人性的。在其后的一百年間,幾乎每一位英國道德哲學家都認為要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就必須從反駁霍布斯的謬誤開始。然而,在這些斥責霍布斯著作的道德哲學家中,絕大多數人早已湮沒無聞,而《利維坦》一書卻代代相傳,成為無數知識分子的必讀書之一,顯示出不可磨滅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價值。[29]
不錯,霍布斯從他的人性論推導出的動機論,認為人的欲望決定了人完全是自私的,人的基本動機就是支配欲與求生欲:“人一出生,就自然地要爭奪己之所欲的一切東西;如果可能,就要使全世界畏懼和服從自己。”在對權力的永無休止、永不滿足的追逐上,唯一的限制是死亡和對死亡的恐懼。然而,同這一理論大異其趣的是,這位思想家卻又那樣地樂善好施、慷慨善良、彬彬有禮而善解人意。一位國教牧師曾經目睹霍布斯施舍給窮人,便詰問這位知名的無神論者:“若不是基督的教導,你會施舍嗎?”霍布斯回答說,他之所以樂于施舍,是因為施舍不僅使得窮人快樂,而且使他自己由于看到窮人快樂而快樂。又據傳說,他的母親在生下他這個早產兒時,正處于對西班牙無敵艦隊靠近英國海岸線的極度恐懼之中。霍布斯就此寫道:“恐懼和我,像一對孿生子一樣,一同來到世間。”許多研究者發現,在動蕩社會中度過了91年漫長人生的霍布斯,絕不是人們想象的那般“自私”,更不曾像“狼—樣地對待別人”。相反地,他的光彩照人的學者人格同他的思想遺產一樣,200多年來始終被視為人類文化的寶貴財富。
[1][5][6][7][8][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3][24][25][26][英國]霍布斯.利維坦[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94,97,92,117,96,197,98,131,132,131,108 -109,109,288,289,266,207-298,97,99,100,131,119,114-115,118.
[2][3]周輔成主編.西方著名倫理學家評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56.252.
[4][美國]S.E.斯通普夫、J.非澤.西方哲學史[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195.
[9]不列顛百科全書 (國際中文版第12卷)[K].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32.
[22]Ferdinand Tonnies(ed.).The Elements of Law.New York,1969:88.
[27]A.MacIntryre.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London,1989:130.
[28][美國]列奧·施特勞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K].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1-2.
[29]Oliver A·Johnson.Ethics:Selections from Classicaland Contemporary Writers.London,1989:136.
責任編輯 姚黎君
B504;D09
A
1672-2426(2010)08-0014-05
程立顯(1948-),男,江蘇沭陽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倫理學、社會公正和公民教育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