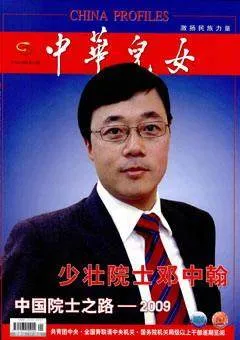鄧中翰人生的三次轉折
上大學。出國留學,回國創業,鄧中翰的人生軌跡熠熠生輝。仔細觀察,他似乎平坦的人生路上,有三個極為關鍵的轉折點。
贏得“挑戰杯”
1992年的中國科技大學,一個叫“鄧中翰”的學生拿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入學通知書。伯克利物理系被高傲的中科大物理系學生視為傳統歸宿,而鄧中翰竟然來自地球與空間科學系這在中科大時引起不小的轟動。
伯克利是美國數一數二的歷史名校,也是全球產生諾貝爾獎大師最多的學校,美國人稱之為“比黃金更能給人帶來光榮與喜悅的大學”。
南京長大的鄧中翰如同那個年代的很多男孩,從小就崇拜科學家。“我那時最崇拜的是愛因斯坦和愛迪生,兩人名字都是‘愛’開頭,小時候一直以為是兄弟呢。后來讀中學時全民學陳景潤,我搞不懂‘1+1=2’這里面還有什么學問,感覺特別神秘,特別向往。”鄧中翰回憶說。
那確實是個崇尚科學的年代,“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則是當時整個時代精神的生動投影。正是在這種氣氛的熏陶下,鄧中翰1987年成為中國科技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系的學生。
大學期間,鄧中翰“鉆”勁是出了名的。“上大學第一學期,我就把關于科學史的一套叢書讀完了,成為我樹立科學人生觀的第一步。”鄧中翰說。
大學二年級時,通過胡友秋老師的介紹,他又找到曾對北京人頭蓋骨做出國際公認明確斷代的黃培華教授,提出了想做科研的打算。當黃教授將一沓厚厚的英文資料交到他手上時,鄧中翰就再也沒有空閑了。他抱著就當是學英文的念頭,苦苦研究了8個月,最終用量子力學解釋了空間射線對地球礦產物質晶體結構產生的影響。
鄧中翰沒有想到的是,這篇論文竟然還有了意外的收獲。“我懷揣著一個年輕人的自信,向《科學通報》投了第一篇文章,還把文章翻譯成英文。沒想到夏天過完之后,我就得到了《科學通報》錄用這篇文章的通知,這對我是天大的驚喜。”鄧中翰回憶說。
大學四年級,他又憑借著這些科研成果獲得了共青團中央與中國科協頒發的“全國大學生科技競賽挑戰杯獎”。
這一系列既偶然又不偶然的事兒給鄧中翰的人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我突然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普通學生是有價值的,而且這個價值是被社會認可的,創造出來的科研成果也會被這個社會所重視;我也開始有了明晰的目標,那就是不管將來做什么,都要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
“這是一個人從幼稚無知的階段,到相對比較成熟,懂得自己的價值,懂得珍惜時間的重要轉折點”。人生的軌跡有時非常奇妙,一次偶然的經歷就能扭轉整個人生的方向。鄧中翰認為,獲得“挑戰杯獎”改變了他一生的方向。
創造伯克利奇跡
1992年正值電腦從286奔向386時代,在伯克利攻讀博士學位的鄧中翰每天都能感受到硅技術和信息技術最前沿的沖擊。當時的風云人物“摩爾定律”的發明者摩爾,英特爾的董事長安迪·格魯夫都畢業于伯克利電子工程系。
他們用IT技術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對“科技改變世界”十分感興趣的鄧中翰希望能效仿他們,決心選修電子工程專業。為此,他找到了伯克利的傳奇校長,美國歷史上擔任頂尖大學校長的第一位華裔——田長霖教授。然而,田校長卻擔心鄧中翰能否完成知識結構的調整。鄧中翰據理力爭,告訴他自己在大學時代就做過非常超前的科研,還在世界一流的雜志上發表過論文,完全有這個能力。最后,妥協的結果是田校長答應給他一個學期考驗。于是當一些中國學生都忙著買車和旅游的時候,鄧中翰卻在閉門苦讀,最終。全A的成績讓鄧中翰順利攻讀了電子工程博士學位。
不久,一次更大的轉變悄然而至。
那是一個午后,鄧中翰因為護照問題滯留在日本東京。他漫無目的地閑逛著,周圍是行色匆忙的人群。一個問題突然出現在他的頭腦中:“為什么自己離開中國時人們的工資才一百多元,而有些國家會這么發達?為什么有股市?為什么有產業?……這些在我以前的生活中從來沒有考慮的東西突然問全冒了出來。這些東西之間有什么聯系,它們又是如何支撐著這個世界運行的?”
鄧中翰陷入了疑問。徜徉東京街頭的幾天,這些問題在鄧中翰的頭腦中不斷盤旋,他意識到這些問題背后可能存在著更多,更復雜的原因。回校后,他決定通過學習經濟學來突破自己的知識局限。
在伯克利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人橫跨過理、工、商,考慮到知識結構和精力的問題,校方拒絕了鄧中翰兼修經濟學的請求。鄧中翰再次找到田校長,獲得了極為關鍵的支持,得償所愿。順利跨入經濟學的大門,鄧中翰發現這個世界遠不是自己當初從技術角度所看到的那么狹窄、那么簡單。一個知識的富礦擺在了面前,樂于迎接挑戰的鄧中翰再次開始了新的跋涉。
到1997年畢業時,鄧中翰已經拿下了物理學和經濟學的碩士、電子工程學的博士學位,成為伯克利建校一百多年來第一個橫跨理,工,商三個學科的人。當商業思維和技術思維交織在一起時,鄧中翰的人生也開始向著更為寬闊的道路邁步行進。
歸國的橄欖枝
1997年,鄧中翰結束了在伯克利的大學生涯。
那時,正值舊M的“深藍”計算機和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的巔峰對決。這場曠古未有的比賽,引起了鄧中翰極大的興趣。帶著這份熾熱的興趣,鄧中翰決定加入風光無限的IBM。
之后,僅僅一年,鄧中翰就接連申請了好幾項專利,同時獲得了“IBM發明創造獎”。讓當時IBM資深的工程師們都刮目相看。但僅僅一年,鄧中翰就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就這樣打工下去嗎?還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呢?
1997年,鄧中翰回到硅谷,給自己設定了一個嶄新的人生命題:自主創業。
他創辦的是一家名為Pixlm的研制高端平行數碼成像技術的公司。出乎很多人的預料,這個不為人知的華人青年很快就獲得了成功,Pixim市值頂峰時已達1.5億美元。此時,鄧中翰的人生無比燦爛,富裕而安逸的美國夢已經實現,沿著這條硅谷生活的既定軌跡,前途不可限量。
就在此時,鄧中翰遇到了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周光召當時是國家科技領導小組成員,同時兼任著國際物理學聯合會副主席,在國際物理學界享有盛譽。在一次交談中,他向鄧中翰提出了一個沉甸甸的話題,“中國半導體工業可能要走一條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辦法來做。”
周老向鄧中翰介紹了中國芯片領域的發展情況。中國科學院早在1965年就開始了集成電路的相關工作,直到1990年,我國仍未能在此類產品的大規模產業化方面取得建樹,1990年后的兩次沖擊也都無果而終。而作為電子信息領域的核心,中國的芯片技術應該也必須發展起來。
面對周老提出的問題,考慮到中國的芯片業到底應該如何突破的問題,鄧中翰從自己看到的、最擅長的,也是親身經歷過的硅谷模式出發,提出中國宜嘗試一種新模式——采用硅谷模式運作的可能。周老聽了鄧中翰的想法連連點頭,突然問:“你來做這件事,怎么樣?”
后來,不少人對此津津樂道,認為周老一句話,鄧中翰回國開創了中國芯片產業。如今,當往事一點點地被揭開,人們發現,鄧中翰回國創業亦非一時沖動。
1998年,在一次與中央領導的座談中,鄧中翰向李嵐清等中央領導就如何推動科技創新做了專門匯報。鄧中翰在匯報中提出了自己關于企業創新發展的大膽見解,那就是在中國的科技體制下,不能僅僅靠國家實驗室的方式搞創新,還要建立起支持創新的產業,通過產業來推動國家的創新發展。
這是一個試探——這個報告猶如一顆石子拋向了湖心。不久,鄧中翰得到反饋,他的報告獲得了高度贊賞,“領導們非常認同我的觀點,給我回國創業以很大的信心。”
舊金山海灣,水天一色,海鳥翻飛,遠處有船艦駛向海洋深處,岸邊走來了鄧中翰,他和幾個同事時而中文,時而英語;時而情緒激昂,時而輕聲細語,最后一起伸出手臂擊掌相約:“回國創業,一言為定!”
那是1999年7月的一個傍晚。正是這一刻,鄧中翰正式踏上了歸國創業的人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