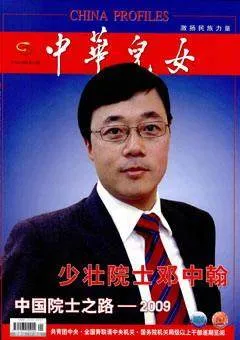于全:耐得大寂寞才出大成果
“像我這樣的人,在中國比比皆是,但是有我這樣機遇的人不是很多,是部隊給我提供了干大事的條件。要說起來,我當時的選擇也是一種思維上的創新。那時,國內洋博士不多,軍隊里更是鳳毛麟角,“像我這樣的人,在中國比比皆是,但是有我這樣機遇的人不是很多,是部隊給我提供了干大事的條件。要說起來,我當時的選擇也是一種思維上的創新。那時,國內洋博士不多,軍隊里更是鳳毛麟角,因此,我到軍隊后很受重視。正所謂,不隨大流,機會概率才會高。”
2009年12月2日,中國工程院2009年院士增選結果在京揭曉。44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某研究所總工程師于全與鄧中翰、吳曼青一起當選中國工程院信息與電子工程學部院士,刷新了中國工程院最年輕院士記錄,成為新增選的48名院士之一。這一消息不僅讓于全的九江家鄉人為之驕傲,更引起世人的普遍關注。
出人意料的選擇
對熟悉他的人來說,于全當選為院士這一消息并不意外,自幼天資聰穎的他,求學與科研之旅可謂一路坦途——
1982年,于全17歲時以九江市高考理科第二名的成績考入南京大學信息物理系,成為其母校同文中學和九江市三中的榮光。1986年,本科畢業后又考入以“西軍電”之稱蜚聲海內外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攻讀物理系電波傳播專業碩士學位,1988年6月30日,作為該校唯一入選的國家公費研究生,被派往在歐洲通信界大名鼎鼎的法國里摩日大學光纖微波通信研究所繼續深造。
初到法國,按法國規定必須首先取得攻讀法國博士的資格(即DEA),一年后,不服輸的他以全優的成績在來自世界各地的60多位同學中名列前茅。此后3年,在集光纖、通信、計算機等多學科為一體的法國里摩日大學光纖微波通信研究所,于全苦心修煉,先后取得了多功能光纖傳感器、光纖網絡的計算機輔助設計系統等3項重要科研成果,撰寫的6篇學術論文在國際著名學術刊物上發表,創造的可調式光纖藕合器獲得法國專利,出色的科研能力令人刮目相看。
1992年5月11日,于全順利地通過了博士答辯,《多模光纖效應的研究及在光纖網絡CAD中的應用》作為一等論文,被列為里摩日大學的博士畢業論文范本,專家評判“非常出色”。尤為人稱道的是,于全在論文中解決了法國巴黎地鐵公司、煤氣公司、電力公司光纖網絡建設中的技術難題,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一時間,法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外諸多企業、大學與研究機構紛紛邀請于全加盟,他卻毅然謝絕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優越條件與豐厚待遇,在1992年6月30日即他出國4周年這一天回到祖國,成為同期70多位留法中國留學生中第一個學成歸國的博士。
“4年留學生活,開拓了我的思維,也給了我自信。我受不了西方人居高臨下的同情與憐憫,不甘于做發達國家的‘二等公民’,選擇回國創業就是希望能在祖國這塊土地實現自己的價值,尋求一種在科技創新上與西方列強精神平等的途徑。”在于全心中,國家絕不僅僅只是一個概念。“祖國送我出國深造,4年就得花費50多萬元人民幣,相當于5000個農民1年的農業稅,這是人民的血汗錢呀!”留學4年,承載著祖國消息的《人民日報》海外版成為他了解祖國的窗口,這種獨特的愛國主義教育已在1400多個日夜中深深浸入他的血液。
彼時,像于全這樣的人才,在國內也是“寶貝疙瘩”。在首都機場,于全就被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給“預訂”了,很快航天部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總公司也向他伸出了“橄欖枝”,有意請他加盟的單位絡繹不絕。與于全同期回國的學者,不少選擇了高等學府,成為了行業領軍者,保持著在全世界行走的高度自由。那時,中關村已經出現了收入高達5萬元的年薪,像于全這樣的“海歸”精英,可以拿得更多。
這時,一位好友給他介紹了總參某研究所。所領導和于全促膝長談,談的不是條件,不是待遇,而是我軍目前的通信現狀及其與國外的差距。于全感覺自己的血管里有一股熱流在奔涌,他出人意料地謝絕了多個國內知名學府與大型企業的邀約,義無反顧地選擇了部隊。這個選擇,意味著月薪300多元,而且,要受到部隊高度的組織紀律約束。
在當時,于全的選擇太出人意料,以至于很長一段時間,他每天都在回答為什么回國、入伍這兩個問題,只因為好奇、不解的人實在太多了。“后來的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
于全含笑謙稱:“像我這樣的人,在中國比比皆是,但是有我這樣機遇的人不是很多,是部隊給我提供了干大事的條件。要說起來,我當時的選擇也是一種思維上的創新。那時,國內洋博士不多,軍隊里更是鳳毛麟角,因此,我到軍隊后很受重視。正所謂,別人不太容易想到的,往往是機會最多的;不隨大流,機會概率才會高。”
1992年9月4日,于全穿上國防綠,成為總參某研究所通信研究中心工程師,17年間,他歷任高級工程師、研究員、中心主任、總工程師,2009年12月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之一。
洋博士的自適應
許多人都以為于全在部隊順風順水,實際上,這位留法4年的“洋博士”曾經經歷了一個相當痛苦的自適應過程——
初進軍營,部隊并不因為于全是一名特殊的新兵,就給他特殊的照顧。幾個月封閉的新兵訓練,讓于全感覺絲毫不比搞科研輕松,但這也鍛就了他作為軍人的剛毅與堅韌。
在山西完成新兵訓練后,于全回到北京。當時各種輿論都將于全“舉得很高”,媒體的輪番“轟炸”與重壓,讓他感覺壓力很大。“最痛苦的不是后來睡實驗室吃方便面做項目的日子,而是那段找不著北的日子。”
一次與同學聚會時,同學跟于全開玩笑說:“在法國,你好比‘人頭馬’,是高檔貨;剛回國,你好比‘五糧液’是搶手貨;當了兵,變成了‘二鍋頭’,是大路貨。怎么樣,現在你是不是有點想吃后悔藥了?”于全表面上嘿嘿一笑,心頭卻是沉重的,怎樣盡可能快地完成自適應過程成為他那段時期重點考慮的問題。
放下“洋博士”身價,虛心向“老人”學習,是他對自己的要求。“我原來學的是物理專業,讀博時學的是光纖通信,進入總參某研究所后,轉攻無線通信。而且,軍事通信與民用通信之間存在差異,我對軍隊的特點、需求完全不了解,因此很多東西都要從零學起。”半年時間,他所閱讀的書籍與資料,摞起來比人還高。
那段時間,于全每天清晨7時就第一個來到辦公室,去幾百米外的食堂打來開水,然后拖地、擦桌子。“我想通過這種樸實無華的方式告訴大家,洋博士沒什么了不起。同時,也想看看,從無拘無束到紀律嚴明,自己的自適應能力究竟怎樣。”就這樣堅持了三四個月,于全的心慢慢沉靜下來,所里的“老人”們也漸漸接受了這個腳踏實地的“洋博士”。
這段自適應心得,后來被于全總結為“打掃衛生理論”,成為其所在單位人所周知的信條之一。在于全看來,掃地、拖地、打水、擦桌子,這些一般人眼中的小事,卻很能反映出一個人的綜合素質,體現出一個人的工作態度、處事心態與精神格調,只有腳踏實地干事、真正融入團隊的人,才有可能成就大事業。
“如果只看外表,沒人知道他是海歸。”于全的戰友們說。他經常會穿著作訓服,與野戰部隊最基層的戰士們混在一起。“只有這樣,我才知道部隊需要什么樣的通信裝備。”于全解釋說。
凡是蹲過點的部隊,于全都能叫出每一名通信士官的名字。在他的帶動下,課題組的同事都愛上了基層蹲點試驗,正是在這種深入接觸與調研中,于全與他的團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耐得大寂寞,才出大成果
接到第一個課題后的一年多時間里,為了加快項目進度,于全與他的兩名助手放棄了休息日,加班加點查資料、編程序,每天都干到深夜,餓了就吃方便面,困了就湊合著在實驗室睡一覺,500多個日日夜夜,就這么不知不覺地過去了。計算機程序枯燥而又繁瑣,他們反復地編寫、修改,再編寫、再修改,光編制的程序就達幾十萬條,打印出來足有幾公里長……
1994年12月,于全主持設計的野戰通信網計算機仿真系統研制成功,并榮獲1995年度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這個系統不僅填補了國內空白,而且有10多項技術指標都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其研制時間之短、質量之高,令專家們驚嘆,更讓人驚嘆的還是它的神奇功效,如今,這一成果已廣泛應用于衛星通信、無線通信、保密通信、電子對抗等軍事領域,產生了巨大的軍事、經濟和社會效益。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信息已成為掌控戰場物質和能量流向的關鍵因素,制信息權成為決定戰爭勝負新的戰略制高點,軍隊信息化建設成為當前世界新軍事變革和各國軍隊轉型的核心內容。多年來,協同通信一直是困擾世界各國軍隊通信暢通的一大難題。這一世界性難題引起了于全的關注和思考。
“軟件無線電”這項剛剛萌芽的新技術進入了他的視野。研究所領導全力支持他的大膽設想,籌備60多萬元人民幣,從全所選調精兵強將,組成一個包括2名博士、5名碩士在內的課題組,協助于全一起攻關。
“軍用軟件無線電網關”課題的研究需要大量野戰電臺運行數據來支持,在立項后一年多時間里,于全和他的團隊從青藏高原到天涯海角,從遼東半島到東海之濱,跋山涉水,戰嚴寒,冒酷暑,深入陸海空通信部隊,掌握第一手資料,僅搜集、歸納的各類數據就有數百萬條。
1998年11月,于全和他的團隊以最少的經費和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中國第一臺“軍用軟件無線電網關”電臺,成功地實現了我軍不同頻段、不同體制電臺的互連互通,較好地解決了三軍協同通信這一世界難題,被譽為“自模擬過渡到數字之后無線通信領域的又一場革命”,使我軍在野戰通信技術研究上第一次走在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前面。
榮譽接踵而至,“耐得大寂寞,才出大成果”,為排除干擾,于全給自己定了“三條規矩”:成果不急于報獎,不急于出專著,不接受媒體采訪。他淡泊名利,多次在報獎時劃去自己的名字,還常把自己所得獎金悉數分給他人。他常說:“泰戈爾說得好啊!鳥兒的翅膀綁上了黃金,怎能飛得遠呢?”
正是在這種清醒與淡定下,于全率領他的團隊繼續瞄準世界軍事信息技術發展前沿,馬不停蹄地創新,先后完成了20余項重大科研項目,成功研制出我軍第一代戰術通信網,實現了通信保障模式的跨越式發展,為我軍打贏信息化戰爭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17年來,于全刻苦攻關,不斷創新,先后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項、二等獎1項;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4項;國家重點資助優秀留學回國人員;全國優秀歸國留學人員;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中國青年科技獎;全國青年科技獎一求是工程獎;全軍學習成才標兵;全軍通信系統優秀科技骨干;總參青年標兵;總參優秀中青年專家;總參優秀科技干部;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1次;第十二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標兵”等獎項。一批科研人員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成為我軍通信領域的中堅力量,而他自己也成為我軍最年輕的軍事通信學科帶頭人,是當代青年景仰的偶像之一。
文理兼備的“交聯”式讀書與學習
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對于全來說,驚喜之外,更是責任。“它是我人生的重要節點,今后,我將在這個更高的平臺與更大的舞臺上,為自己所鐘愛的軍事通信事業而奮斗。”
在一般人眼里,于全是一個傳奇,他的人生寫滿精彩,充滿創新。前輩稱贊他“思維不拘一格”,學生說他“善于出奇制勝”,而于全自己卻謙遜地說這得益于“交聯”式的讀書與學習。“交聯”本是物理和化學領域的一個專業詞語,于全借用過來,旨在強調一種互聯互通、融會貫通、觸類旁通的學習方式。“雖然工作繁忙,但他至今依然保持平均每周讀一本書的習慣。“工作再忙,也不能放松學習;不學習,就意味著放棄明天。”這是于全給自己的忠告。
于全經常閱讀的書基本上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通信行業的專業書籍,第二類是作戰理論方面的軍事類書籍,第三類是涉及人生觀、價值觀方面問題的哲學社會科學類綜合圖書,第四類則是小說、散文、藝術之類怡情養性的圖書。
“各類圖書與各種學科之間,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不斷印證、互相映射的。”對于這一點,于全深有感觸。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讀到美國作家杰夫?凱爾斯撰寫的《分布式網絡化作戰》。這本書從分布式網絡化作戰的基本概念和需求背景出發,描述如何在復雜環境中充分發揮分布式網絡化作戰優勢,文字簡潔優美,內容深入淺出,具有很高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于全愛不釋手,很快將之翻譯成中文,并于2006年11月在北京郵電大學出版。
細細品味,這位看上去很是理性、嚴謹與穩健的軍人院士,內心深處,卻也有著文人墨客的浪漫、憂思與悵然。自幼喜好繪畫的他,后因學習、工作等原因而不得不放棄,每天高強度的工作與學習,使得他幾乎沒有了自己的業余愛好,“但在國外,不少杰出的科學家同時還是出色的藝術家”,于全在法國里摩日大學讀博士時,導師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科學家,小提琴卻拉得相當專業。而這,似乎才是于全心目中真正的科學家,也才是他的理想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