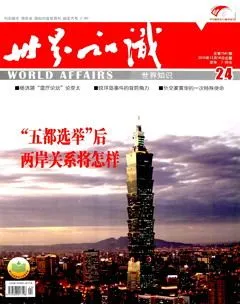五學者解讀今日亞太
2010-12-29 00:00:00
世界知識 2010年24期


秦亞青(外交學院常務副院長)
伴隨著地區的合作與發展,東亞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產生了很多地區機制,搭建了地區構架的平臺。東亞及亞太地區是個很復雜的地區,它的地區構架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我認為,東亞乃至亞太地區合作構架最基本的特點是多元、多重、多樣。這些機制相互之間并沒有完全的等級結構,功能也有重疊、交匯,這也反映了東亞地區的現實。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務實的功能主義。東亞和亞太地區在經濟領域中的功能性合作最有成效。二是合作的多邊主義。這些合作表現出向多邊主義發展的明顯取向。但多邊合作仍然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代表的合作渠道。三是開放的地區主義。地理上是開放的,對域外國家開放,甚至是跨太平洋的開放。制度上是開放的,從原來的10+3擴大到10+6,又加入了美國和俄羅斯,變成了10+8。由于整個體系是開放的,所以制度本身和地區發展也是全開放的。正像楊潔篪外長所說,所有域外的行為者都可以積極地對地區合作作出貢獻。
中國從1990年開始與東南亞國家改善關系,積極參加地區一體化進程。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首先在參加地區合作過程中支持地區經濟合作多元態勢,比如支持清邁機制多邊化、支持建立區域外匯儲備庫、支持建立亞洲債券市場,等等。中國和東盟自貿區現在已形成一個有19億人口、6萬億美元的大市場。為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中國提出了以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為核心內容的新安全觀,對熱點問題采取積極協調、促談勸和態度,對復雜的、有爭議的領土問題,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中國是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東盟伙伴國,積極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國積極支持開放的地區主義,尤其是對有重要影響的區外國家,中國歡迎他們參加到地區合作的過程中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對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推動也在加強。東亞地區的歷史和現實證明,一個穩定、繁榮、進步的中國,對于東亞地區的和平、發展與合作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
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人們談起亞太,更多想到的是經濟一體化和地區合作,但是今天,很遺憾的是,人們會想起亞太地區的沖突,包括朝韓對峙、美韓軍演、中美在黃海南海的戰略博弈,等等。有人認為,亞太地區出現這些不好的苗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美兩國關系出了問題。中美關系去年好到令許多國家嫉妒的程度,今年卻似乎急轉直下。美國有人認為,中美關系出現問題主要原因在中國,因為中國外交更加強硬、更加咄咄逼人,不是美國變了,是中國變了。但中國并不認同這個觀點,中國認為我們在對臺軍售上的合理反制、在釣魚島問題上對自己利益的合理訴求、在南海問題上對自己利益的重申,沒有一個超出中國傳統利益范疇,因此中美沖突主要責任在美方,是美國利用周邊矛盾對中國進行戰略包圍、戰略圍堵。
產生這種認知上的差異,不能說雙方都沒有道理。我認為,出現這種局面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中美力量對比出現了一些變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彼此戰略心態的一些微妙變化。不容否認,今天的中國確實比以前更加自信、甚至自豪,同時人們也看到,美國則好像不像過去十年那么自信,而是有點焦慮。
第二是美國戰略的調整。美國過去的戰略重心在中東、中亞,現在突然來到亞太;以前是應對恐怖主義,現在要應對新興大國的崛起。很自然,美國戰略的調整導致美國和中國以及中國一些周邊國家的關系出現一些較大的變化,這種大的變化有時候不可避免地被中國解讀為是對中國不利的一個態勢。
第三是一些偶然事件,例如“天安”號事件。
第四,中美關系也受到亞太其他國家關系的影響。
所以,中美關系的變化是綜合因素促成的。我不認為美國對華戰略出現了根本性變化,同時中國也沒有改變對美政策。所以雙方還是要堅持積極合作。胡主席即將訪美,我覺得這是重新梳理中美關系的非常好的機會,最重要的話題就是如何實現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和平共處,而實現這個和平共處,有三方面的任務應該是最重要的:一是相互讓對方放心,美國應該以正常的心態歡迎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崛起甚至合理的訴求,中國也應該歡迎美國在這個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二是要搭建一些框架或者行為準則,避免中美在這個地區發生沖突,尤其是海上的沖突。三是因為中美關系的發展離不開亞太其他國家的合作,所以應該實現中美和第三方之間的合作共贏。
劉古昌(中國國際問題基金會副理事長)
在研究亞太問題時,俄羅斯常常被人們忽略。實際上俄羅斯三分之二的國土在亞洲,巨大的發展潛力也在亞洲。俄羅斯是APEC和東盟地區論壇峰會機制的參與者,加入了亞歐會議和東亞峰會,對亞太地區的作用都在提升。
當前的中俄關系正處在空前的高水平。我講幾個表現:一是兩國領導人交往非常密切,雙方高度互信,對任何問題都能夠推心置腹、沒有保留地交換意見。二是兩國本著友好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徹底解決了邊界問題,使4300公里邊界成為友好合作的紐帶。三是兩國充分理解對方的關切,在涉及國家統一、主權、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提供堅定的支持。四是雙方雙邊合作涵蓋了幾乎所有領域。五是兩國對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對當今世界的認識和今后的發展有著廣泛一致,隨時保持密切溝通,合作卓有成效。
中俄關系一直保持良好發展勢頭,主要啟示是:一是雙方超越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差異,尊重對方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從國家根本利益出發,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國家關系。二是雙方都把國家的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支持對方發展興國。通過睦鄰友好,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通過互利合作,促進本國發展,進而實現兩國共同發展。三是能夠從兩國關系的大局出發,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充分地照顧對方的關切,通過友好協商,冷靜、妥善地處理突發事件,解決合作中出現的問題。四是雙方恪守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的國家關系定位,兩國發展關系不對任何別國造成危害,相互不給對方與別國發展關系產生任何限制。五是雙方認準發展睦鄰友好、加強互利合作是各自根本利益所在,堅定地奉行睦鄰友好、互利合作的方針,不受國際風云變幻的影響,不受外部勢力的牽制。對于形形色色的干擾破壞、挑撥離間保持清醒,不為所動。中俄關系保持良好發展勢頭所得出的這些啟示是中俄雙方共同創造的寶貴財富,也是對發展亞太國家關系的貢獻。
中俄關系面臨新的機遇。主要理由有:一是金融危機推動世界大調整、大變革、大發展。中俄同屬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朝什么方向發展的重大問題上目標一致,有許多共同關切和主張。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中俄必須同舟共濟、加強合作,同時也為雙方合作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二是亞太地區成為全球政治、經濟中心的趨勢日益明顯,戰略地位從未像今天這樣重要。俄羅斯更加重視亞太地區,更加積極地參與該地區事務,中國歡迎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這為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進一步發展開辟了新的天地。三是在我國加快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和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同時,俄羅斯也在實施發展創新經濟的戰略和加快遠東西伯利亞地區的開發,這樣雙方就成功地進行了戰略對接,使雙方的合作向更大規模、更深層次推進。
劉江永(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
中日關系在今年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上半年和下半年明顯不同,前暖后冷。上半年鳩山由紀夫首相執政期間,中日關系取得了可喜的發展。但是今年6月菅直人首相執政后,在外交政策上有明顯調整,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系,與中國拉開距離,特別是9月7日日本在中國釣魚島海域非法攔截并扣留中國的漁船,這在歷史上,或者精確地講在戰后以來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雙方在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上有爭議,但是日方企圖按《國內法》處理這個問題,導致了中國政府采取了有力反制措施,兩國關系出現了不愉快。在中方有力交涉下,日方釋放了中國船長,不過兩國關系到下半年仍然是有冷有暖,改善得并不非常理想,這還是由于日本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堅持按《國內法》來處理,同時強調不存在領土爭議,中國政府沒有辦法和日方就領土問題進行直接對話。日方釋放中國船長之后,10月上旬,溫家寶總理在比利時會見了菅直人首相,11月胡錦濤主席出席在橫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也會晤了菅直人首相。中國前國務委員唐家璇率團出席在日本舉行的第一屆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并且在會后和包括菅直人首相在內的日本主要政要進行了直接深入的溝通。
關于中日關系未來的發展,我的觀點是,近期中日關系仍然存在著不穩定因素,但是從中長期看,我認為對中日關系應該抱有信心。近期的問題主要是在12月上旬日本和美國還要進行軍演,同時在今年內日本有可能推出新的防衛計劃大綱,如果這個大綱涉及釣魚島等問題,會給中國和日本關系帶來消極影響。從中長期看,只要中日雙方遵守已達成的四個文件的各項原則,從目前兩國相互依存的關系越來越深、彼此很難分離的情況來看,我認為中日兩國發展健康、穩定的友好合作關系,不僅符合雙方的利益,也符合包括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各國和平與發展的共同利益。
虞少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我首先講一下今年以來中國和東北亞出現的問題。第一,針對地區熱點問題的軍事威懾與同盟行動進一步升級了,美國、韓國、日本針對“朝鮮威脅”的各類軍事演習頻度和力度明顯增加了,三方配合性的行動也有實質提升。同時在一年中有關國家武器配置的升級和軍費價碼,也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相關國家圍繞地區安全問題的立場差異凸顯,雙邊懸案的摩擦加大,政治互信和合作關系遭受沖擊。上半年的“天安”號事件凸顯了中美、中韓在朝核問題以及對朝政策上的立場差異,年中的釣魚島“撞船事件”又導致釣魚島問題升溫,近期美國航母執意到黃海進行軍演激化了中美關系中摩擦對抗的一面。這些事件直接影響了各方對地區熱點問題的合作,非常不利于地區穩定。
第三,地區內的突發事件更加頻發、更加惡性,失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比如說“天安” 號事件、釣魚島“撞船事件”以及最近發生的延坪島炮擊事件,都給地區形勢帶來消極影響,甚至幾乎引發整體局勢動蕩。特別要注意的是,相比以前,這些突發事件不僅頻度更密,而且更為尖銳,有些沖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更大災難。
地區安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有增無減的癥結到底在哪里呢?我的結論是在于冷戰的殘余影響。朝鮮半島分裂與對峙,就是冷戰的延續。雖然朝韓之間已經有一些交流與合作,但是從根本上講,雙方敵對心理和軍事戒備態勢與冷戰時期相比沒有根本變化,有的時候起伏還很大,同時這種結構也體現在周邊大國分別對朝鮮、韓國的關系和政策上,中韓、俄韓建交已經20年,美朝、日朝關系正常化卻遲遲不能實現,由于圍繞朝韓政策的分歧,周邊大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又備受困擾,這種混亂失衡局面某種意義上可能比冷戰對峙更加消極地影響了地區的穩定。再從思維上,就是安全觀念來看,各國之間仍然沒有很好地建立起共同安全的觀念,部分國家是希望將自身的絕對安全建立在別國的不安全之上,或者是尋求用極端的形式挑戰別國安全,從而確保自身的安全。
從各國對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方式選擇上來看,我認為制裁、武力威懾等帶有冷戰特征的手段,阻礙了對話協商的進程,也使得熱戰危險難以排除。
東北亞如何走出當前安全困局?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應該認識到,在解決地區熱點問題和建立地區新秩序方面,各國的利益訴求雖然有差異,但是仍有共同之處,其中最大的共同之處,是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這就應該成為各方處理地區事務的首要目標,如果沒有這種大局意識,片面強調一方、一國或某一群體安全,則共同安全就無從談起,東北亞長治久安更難以實現。
另外我還想強調,解決地區熱點問題應該尋求一種現實可行的途徑。已經有很多事實證明,制裁、施壓、用武都行不通,那樣只能增加互不信任和加大格局失衡。長久和平與合作必須有信任和平衡做基礎,對話協商才有可能讓我們逐漸從積累共識向戰略互信發展,從沖撞失衡向平衡轉換,因而才是最現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