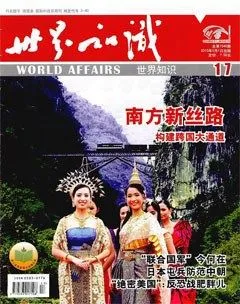東盟區域戰略:平衡中不可承受之重
中國重啟“南方絲綢之路”,重要的合作方就是東盟國家。然而,東盟在處理區域問題時的心態卻頗為復雜……
東盟主導的“大國平衡”
相當長時間內,東盟與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合作都大致在東盟設計的“大國平衡”軌道上運行。概括而論,這些合作包括:與中國、韓國、印度經濟合作以制衡對美、日經濟的依賴;與美國、印度軍事合作以制衡中國崛起帶來的“安全隱患”;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歐洲、俄羅斯合作,以制衡中、美的政治影響;等等。東盟能左右逢源、實現“大國平衡”下的合作,其中的奧妙在于,當其他任何一個大國都無力以“乾綱獨斷”的方式主導亞太或東亞的區域合作時,由東盟這個松散的中小國家集團主導不會對其他大國構成“威脅”,從而易為各方所接受。
東盟成立以來對外部世界的高度依賴和內部“緊致性”不足是其明顯的組織特征。新加坡一位外長曾經這樣評價東盟與區域外部的關系;“沒有切實的外部援助,東盟地區的經濟增長必然極為緩慢……東盟要純粹依靠區域合作策略實現增長是沒有前途的。即使所有東南亞國家都被納入了東盟的框架,我也絲毫看不到東盟國家基于它們自己的資源獲得發展的前景。理論上,東盟國家當然可以作為一個獨立和自成體系的區域來發展……但是,如果東盟要實現其目標,經濟現實要求區域合作必須堅持外部經濟的參與。是區域外貿易和投資而非區域內部的貿易和投資,能夠加速東盟的經濟增長。”
更嚴重的是,東盟各國對外部的依賴長期以來不是作為一個緊密聯合體的對外依賴,而是相互排斥和競爭的對外依賴。雖然有心合作,但東盟內多數國家經濟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相似,彼此都仰仗廉價勞動力優勢,因而競爭多過合作。這種狀態限制了東盟內部的合作與一體化企圖。1967年東盟內部貿易占其全部貿易比重為16.7%,到1974年不升反降至12.8%,可從一個側面佐證之。即便簽署了《東盟自由貿易區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議》,但優惠關稅規定中仍舊排除了許多敏感商品,且以偏高的關稅稅率來抵消一體化進程。
既依賴于外部,內部又各有紛爭,東盟自身的虛弱常常為人所詬病,但這恰恰是其能夠成為更大范圍內的東亞合作的主導、核心或“駕駛員”的重要稟賦所在。試想,假如東盟內的印尼和越南能夠扮演歐洲的德國和法國的角色,試圖實現東盟的高度機制化的一體化和整體崛起,那么,中國與日本等區域大國恐怕就會與英國一般,有被東亞或“東亞-南亞”等更廣范圍的區域合作“邊緣化”之虞,而美國與“歐式東盟”的對抗性也會急劇增加。如果有這些無計回避的大國掣肘,很難想象東盟能夠成為主導10+1、10+3、東亞峰會等東亞合作機制的核心力量。
影響當前合作格局的潛在因素
不過,東亞這種東盟主導的“大國平衡”下的合作狀態,面臨的脆弱性越來越強,表現在東盟自身以及它與中、美等國合作的各個方面。
首先,東盟內部一體化的成效可能削弱其作為更廣泛區域內合作領導核心的地位。東盟推行區域合作的目標是通過貿易投資自由化和更緊密的經濟合作,提高東盟作為世界市場生產基地的優勢地位。東盟把鄰國的競爭視為嚴重的挑戰,為了擴大對其重要經濟伙伴的市場占有,東盟將加速內部經濟一體化。加速內部經濟一體化舉措首先集中在11個優先部門。為促進這些部門的自由化、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監管,東盟提出了一系列有時間期限的措施,希望通過這些措施,按期實現整個區域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可以預見,一旦內部一體化的成效顯現,東盟將成為東亞乃至亞洲地區一支不容忽視的獨立競爭力量,對區域大國構成一定的“威脅”。虛弱性的喪失,可能會讓東盟無法再成為大國環峙之地合作核心的當然選擇。
其次,東盟與中國的合作不斷深化可能打破原有的“大國平衡”狀態。當1997~1998年金融危機席卷東亞大部分地區時,北京在東盟老成員國貨幣因為危機大幅貶值之后,反復強調人民幣絕不貶值。此舉贏得了東盟的贊許。此后中國與東盟的合作迅速推進。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簽署了“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04年11月簽署“貨物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2007年1月簽署“服務貿易協議”,2009年8月15日簽署“投資協議”。2010年中國一東盟自貿區全面正式啟動。同期,美國對東亞的參與卻因為阿富汗、伊拉克事務等牽扯過多精力而下降,多次缺席東亞協商的會議。此消彼長,引得新加坡等國大為憂慮。
第三,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可能帶來新的變數。奧巴馬政府上臺之后,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首次出訪地被確定為亞洲,標志著美國“重返”亞洲,也意味著美國的“競爭性自由化”戰略可能會以東南亞國家為新的實施重點。東盟中新加坡、印尼和越南等,出于平衡中國影響的考慮會非常歡迎這樣的轉變。但從美國一方來說,加入形式上由東盟主導的東亞區域合作不是其利益所在,而通過“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包括了東盟中發達成員)以及湄公河合作(包括了柬埔寨、越南、泰國和老撾)等方式嵌入是極可能的優先選項。美國在東盟各成員中有選擇、有歧視地推行合作的可能后果有二:一是造成東盟內部分歧加劇,最終其機構被“去功能化”;二是東盟借助與其他大國或國家集團的合作機制平衡美國影響力,以避免內部分裂。
盡管東盟所推行的“大國均衡”戰略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東亞區域合作仍然有望在東盟的有力參與下不斷向前推進。例如,如果能充分繼承此輪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制度遺產,在東盟、中國、日本及韓國之間的合作能夠更加緊密,形成區域內統一的最終消費市場,擺脫對外部歐美市場最終消費的高度依賴,那么,東盟不僅無須再作為大國罅隙間審慎的平衡維持者,反倒可能成為與歐美相埒的一方勢力的核心成員之一,這無論對東盟、東亞還是亞太地區的安全及經濟可持續性,都是更大的福音。實際上,無論是日本提出的“東亞共同體”,還是,韓國提出的“新亞洲構想”,東盟都是核心和基礎的合作對象。由消極的“大國均衡”走向更積極的“東亞整合”,恐怕是歷史賦予東盟的新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