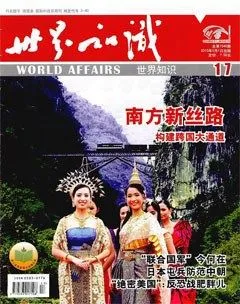電紙書:重塑現代閱讀
“閱讀”已死
雨飛,這個1999年出生的小女孩,是班里的語文課代表,最大的課余愛好就是在網上看小說。“我喜歡看冒險的,還有穿越的小說。”當記者問她喜不喜歡看名著時,雨飛說:“我看過‘四大名著’和《明朝那些事兒》!四大名著嘛,看不太懂,《明朝那些事兒》還挺好看的!”
朱敘,1985年生人,一邊“北漂”一邊籌備考研,目標是中戲的戲文系。他向記者展示了他最喜歡的一個劇本網站:“這個網站的優點就是能迅速地鏈接到評論。”果然,在《哈姆雷特》每一場戲的下方,都鏈接著一長串劇評。朱敘說:“以前在圖書館,我都是先專門找劇本看,再專門找評論看,但是在網上,一個劇本的不同版本、不同學者對它的評論,全都集中在一起了,特別方便!”
吳媛媛,1981年生人,程序員。春節過后,她特意用年終獎為自己買了一部適合看小說的大屏幕手機。“職場、武俠、玄幻我都看,題材無所謂,我就喜歡情節跌宕起伏的!”她笑笑,“其實我也知道,這都是些沒營養的東西,可我家離公司太遠了,在地鐵里要是沒有手機看小說,肯定要無聊得長草了!”
一家文學網站近期的調查顯示:進行網絡閱讀的用戶,73%都集中在18歲~30歲的年齡區間。而中國聯通的《2010年電子閱讀項目規劃》中也披露:使用手機閱讀的人,18歲~35歲占了88%,而使用了手機閱讀客戶端的“重度客戶”更是集中在30歲以下,其中18歲~22歲占45%,23歲~27歲占37%。
在年輕人紛紛轉向“電子閱讀”的同時,另外一組數據也頗值得玩味。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進行的調查中,中國人的圖書閱讀率(即每年至少讀一本書的讀者在識字者中的比例)呈下降趨勢:1999年是60.4%,2003年是51.7%,2005年首次低于半數,為48.7%,到2007年,這一比例跌至34%,雖然自2008年起稍有好轉,但仍不能挽回“一多半的識字人口不讀書”的尷尬現狀。
人們為什么不再讀“書”了?
“我也想捧著一杯茶,在臺燈下安靜地讀書,可是現在生活節奏這么快,哪有時間看書啊?”吳媛媛說,“人和人之間也越來越冷漠,在地鐵上除了看自己的手機,沒有別的事情做了。”事實上,進行電子閱讀的用戶,基本都是利用睡覺前、開會或上課時、乘坐地鐵、等人的閑暇時間進行的碎片化閱讀。
而紙質圖書的“性價比”似乎也不是很高。西單圖書大廈里,有不少人正在或站或坐地“蹭書”看。一個背著雙肩書包的男孩把一本非專業的簡裝書翻到了背面,說:“200多頁,25元。我看就沒有買的必要了吧?”
整個社會的閱讀風氣同樣不可忽視。走進一所大學的自習室,會發現課桌上擺的多是英語四六級、計算機等級考試參考書,而如果是考研的人,更是在面前擺上一摞一摞的英語、政治輔導書。記者問一個考研的學生:“這樣的閱讀,不是太急功近利了嗎?”對方明顯有些不滿:“你可以說這是‘功利’,但我覺得這叫‘務實’。”
對于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深圳出版發行集團公司總經理陳錦濤說:“傳統書業將會逐漸走向衰落,電子閱讀一定是未來閱讀的發展方向。”而當年輕人真的習慣了用電腦、手機來代替原有的“閱讀”時,問題也隨之而來。
網絡文學的興起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不可否認,優秀的網絡寫手為文學注入了新鮮的詞匯和新鮮的語言方式,但是,大部分的網絡小說并不能做到“開卷有益”。打開一些文學網站的點擊排行,僅僅是看一下書名就覺得很曖昧。人大的在讀研究生小戚說:“我覺得網絡小說很多,但是真正讀了能讓人受益的卻很少,不是我們傳統上所說的閱讀。”對此,起點網高級主編“月落黃泉”認為,網絡小說的走紅是因為高速發展的經濟與落后的文化市場,使人們在精神娛樂層面產生巨大缺口。網絡小說的出現,恰恰滿足了人們的需求。他說:“任何文化行業都一樣,發展初期都是泥沙俱下的,有精品也必然有粗糙的。”
閱讀,對于有些人來說是一種享受,對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則只是獲取信息的渠道,甚至是打發時間的消遣,因為出發點不一樣,閱讀的方式和效率自然不同。鄭重其事的、開卷有益的、精英化的傳統閱讀正在逐漸沒落,然而,符合現代人生活節奏和心理需要的“現代閱讀”卻依然猶抱琵琶半遮面。
“閱讀”的救贖
“人們的休閑方式,目前最主流的就是看電視、聽音樂、看電影,而閱讀,和這些休閑方式都不一樣,閱讀是一種基本需求。”漢王科技董事長劉迎建說,“電視的連續性太強,而閱讀可以充分把時間碎片利用起來;聽音樂呢,如果是一首好歌,人們會反復聽,但閱讀是不重復的;至于電影,要去影院才能看出效果,有一種購買上的不便利。對于傳統書而言,購買上的不便利也曾使出版社喪失了很多機會,但是電紙書,用戶可以隨時隨地下載,隨時隨地閱讀,在這個條件下,媒體業也將空前發展。”
在中關村,一名銷售人員也向記者推薦了電紙書。
從平面上看,大尺寸的閱讀屏幕頗有“書”的架勢,而僅一厘米厚度又使它比圖書輕便。打開電源,進入書庫,發現這是一種非常類似于普通紙張的閱讀感受:屏幕無背光,絲毫不刺眼,換幾個角度,字跡依舊清晰,而且能夠進行手寫識別,可以用手寫筆對書籍進行批注和摘錄。
打開WiFi無線下載功能,進入漢王的網上書城,這里有數萬種圖書、數十種報紙。記者搜索了自己兒天前剛剛購入的一套四冊小說《張居正》,當時在當當網上的折后售價為70元,而在這里,每冊的售價只有3元。正在記者暗自驚訝的時候,銷售人員說:“漢王的速度還可以,下載一本書一般用不了半分鐘,也就是說句話的功夫,它就到了您的手上了。”
2007年底,首款Kindle面市之前,喬布斯曾狂妄地說:“這玩意兒永遠不會成功!”然而兩年后,Kindle成為亞馬遜最暢銷的圣誕禮物,在美國掀起了一陣電紙書熱潮。蘋果也忙不迭地發布了iPad,并通過其中的iBooks平臺進入電子閱讀市場。在國內,漢王科技等廠家掀起的電紙書熱潮同樣勢不可擋。咨詢機構Display Search的數據稱,2010年中國的電子閱讀器市場規模將從2009年的80萬臺躍升至300萬臺,達到全球市場的20%。目前,漢王書城每天的下載量已經達到15000份,并且還在增長。
在上海世博會熱門場館的排隊長龍中,捧著小巧輕薄的電紙書看得津津有味的年輕人并不鮮見。對于閱讀而言,電紙書具備了一種“現代閱讀”的氣質,它讓閱讀變得更便攜、更碎片化、更個性化,也更便宜。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但是,一個新的“全民閱讀”時代正在緩步走來。這無論是對一個社會,還是對一種文明而言,都是意義深遠的。
現代閱讀的瓶頸
無論產品的功能如何強大,電紙書的本質依然是“書”,它為“閱讀”開辟了道路,卻也面臨著無法回避的問題。
在現代社會,書,作為一次性消費商品,它的生命力一方面來自內容,另一方面就是知識產權保護。“在臺灣,第一個做電紙書的老板被抓起來了,就因為他的產品里面放了沒有明確授權的書籍。”劉迎建說,“在香港、臺灣、新加坡,經常有因為做盜版而被抓去坐牢的。出版業形成了一種共識:為了一部盜版書而去蹲監獄,根本不值得!而中國大陸還沒有這樣的力度,這就讓我們感到——進行不下去了。”
就在幾天前,著名網絡作家“南派三叔”更新了自己的微博:“本想把我的原稿做出epub格式(注:一種電子書格式),一想何必那么麻煩,立即上網找到一個iPad電子書下載站,我黃色的封皮——《盜墓筆記》全集赫然在推薦位上——我這算不算支持盜版?”自嘲的語氣中透著無奈。
漢王的產品在出廠時已經預裝了三千多種書籍,古龍全集赫然在列,而金庸全集卻不見蹤影,這令很多用戶都感到疑惑。面對這個問題,劉迎建也很無奈:“金庸小說是老少皆宜,我也一直很想把它放進漢王的終端里。但是,一方面是金庸小說的版權費用太高,談判進行得很艱苦,而另一方面,你在網上一搜,免費的金庸小說幾乎到處都是。你說,這讓我們怎么辦?”
屢禁不絕的盜版讀物曾讓傳統出版商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在現代閱讀剛剛興起之際,盜版卻早已風生水起。用磨鐵圖書總裁沈浩波的話說:“現在盜版能搞死出版商,未來借助便利的數字化,就更會搞死數字出版商。”
中國人的閱讀已經延續了千年,為閱讀而生的出版行業也同樣歷史久遠。對于電紙書而言,一邊有盜版不斷吞噬市場,一邊還要面對傳統出版業的擔憂。就像MP3取代CD,U盤取代光盤,數碼相機取代膠片相機,這些數字產品取代傳統產品的事件,似乎都發生在一瞬間,而現代閱讀,事實上也是一種取代。這也是整個傳統出版業的隱憂。在日本,一家公司在完成了電紙書所需的一切硬件和技術后,卻沒有出版社愿意與之合作,最后不得已轉戰美國。在德國,電子書甚至賣得比紙書還要貴。
而電紙書在整個產業鏈條中究竟取代了什么?劉迎建認為,電紙書替代的是造紙、印刷、倉儲、運輸和一部分的發行,“這些環節可能TM3NXLO6UyDMjgF727xquVY4p6RrxP4GV7hYooEtKq8=會出現變化,但這種變化是符合當前全世界低碳、環保趨勢的。電紙書的出現,有一個社會進步的意義,不僅更加環保,而且效率更高。”
如果以作家和記者為代表的內容制造者不會被取代,那么電紙書對于他們而言就只是一種新的發行渠道,就在這看似“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時刻,另一個問題又浮出水面:中信出版社新媒體事業部總經理黃锫堅就曾表示,“電子的東西和實體不一樣,比如我給(傳統發行)渠道提供一萬冊書是很清楚的,但是我給電子通道一個電子版權,他賣多少其實我們是不清楚的。”這種顧慮,顯然是來自支付平臺的不成熟。
此外,有調查顯示,讀者希望電紙書中的藏書量最低可達五萬本,甚至能達到幾十萬本。目前網上的漢王書城已有書籍近九萬冊,預計年底能達到十萬冊以上,與人們的心理預期雖然還有一些距離,但劉迎建表示,他們正在不懈努力:“就像當當網現在是很多出版社最大的經銷商,我希望漢王能在五年之內,也成為各大出版社最大的經銷商!”
劉迎建曾對媒體講述過這樣一段經歷:他曾苦尋幾本80年代出版的老書,但最終沒有找到。一位出版界人士直言相告:“出版社的庫房里肯定有這本書,但絕對不會給你一個人單獨調貨,因為無法形成規模效益。”一方面是讀者想買卻買不到,另一方面是大量書籍賣不掉,如果書報刊全部實現數字化,無論對于傳統出版業還是電紙書,都是一個機遇。可以為這個結論佐證的,是在iPad上市的一個月之內,為《華爾街日報》增加了6.4萬份的訂閱量。第一財經董事長高韻斐說:我們不應懼怕、回避電子科技的發展帶給人們閱讀方式發生的變化,關鍵是我們能不能生產出受眾所需要的、愿意為之付費的、有品牌的內容。
閱讀時代
曾有人調查過人們棄購電紙書的理由:“我想在午夜鉆進被窩看電紙書,但它沒有背光,看不了”、“不能隨手折疊”、“喜歡看漫畫,但它還不能顯示色彩斑斕的東西”……
然而,電紙書的種種不完善,正在飛速地被彌補。上海世博會的城市未來館,展出了一款柔性屏幕的電子紙。它和現有的電子紙一樣,無需背光,利用自然光反射即可閱讀,而不一樣的是,它僅有幾毫米厚,可以彎曲變形。人們完全可以想象,未來的電紙書,將有斑斕的色彩,屏幕柔軟可折疊,尺寸更大,價格更便宜,最重要的是,它將既像一本真正的書,又像一個巨大的圖書館,有著完美的閱讀體驗和無窮無盡的內容。
電子設備的特性,還可以為未來的閱讀帶來更多的享受。老年人可以通過電紙書了解養生知識,白領可以通過電紙書得到打折信息,學生一族可以用電紙書隨時上網“織圍脖”……從技術上看,這些情景都并不難以實現。事實上,也只有讓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都能通過電紙書滿足自己的閱讀需求,才能被稱為一個真正的閱讀時代。
2010年3月,漢王科技宣布在上海開出華東第一家電子書旗艦店,并計劃其彩屏電紙書將在2010年第四季度上市。這邁向“夢境”的第一步已經跨出,看來離真正的“現代閱讀時代”已經為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