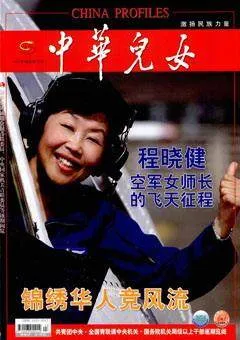王錫鋅 建言希望的良知和熱忱
采訪王錫鋅的這一上午,時間比預計長很多,因為采訪時不時被打進來的電話截斷。粗略地判斷一下,打來電話要求采訪或者邀請他去錄制節目的媒體,不下五個。集中的焦點是時下備受關注的《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因為王錫鋅是建言的五位專家之一。
在這之前的2009年12月16日,王錫鋅和他的幾位同事受國務院法制辦邀請,參加國務院法制辦在京組織專家學者座談會,研討拆遷制度修改的有關問題。
時間再向前,12月7日,北大五名法學學者沈巋、姜明安、王錫鋅、錢明星和陳端洪通過特快專遞的形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建議立法機關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撤銷這一條例或由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向國務院提出書面審查意見,建議國務院對《條例》進行修改。
從上書建言到被邀請參加國務院法制辦開座談會,只有短短幾天時間,從中可以看出,政府對此事的重視。
王錫鋅表示:“政府對于修改現行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決心很大,盡管阻力重重,但是我們仍然看到希望。”
《建議》誕生前后
長達三千余字的《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無異是近年來拆遷混戰中的一道曙光,一時間,坊間一片沸騰。之前,上海扔燃燒瓶保護祖產的新西蘭女子、成都唐福珍自燃事件等都在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事有湊巧的是,在北大五學者上書一周之后,發生在北京四季青南塢的拆遷戶自焚受傷事件,仿佛又在為此事的緊迫性加大注腳。
“是的,看到這么多的拆遷慘劇發生時,我們的心靈受到了很大沖擊。”王錫鋅說,當看到唐福珍自焚身亡這一消息時,他覺得一定要做點什么了。
他的同事沈巋找到他,兩人的想法不謀而合。于是,他們又找到了錢明星、陳洪端、姜明安,自發組成了一個五人法學學者小組,落實起草《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錢明星教授在物權法研究中是權威,陳洪端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憲法,我與沈巋主要研究行政法,姜明安教授是法學界中著名的學者。”王錫鋅這樣介紹起草建議方案的五位學者。
有行政法、憲法、物權法各方權威參與,一封洋洋灑灑的建言書從開始籌劃到寫成并快遞給國務院,僅僅用了四天。
在王錫鋅看來,目前的《拆遷條例》存在著不合理之處:第一,拆遷更多強調了地方政府的管理權,漠視公民合法的財產權;第二,把房屋征收與房屋拆遷分成了兩個階段,使房屋拆遷在沒有得到房屋所有人必要的意見表達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第三,征收和補償沒有在同一階段進行,政府只收回土地,但并沒有對房屋進行征收和補償,而是把補償問題留到了拆遷階段,由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來解決,這不利于房屋所有人利益;第四,拆遷問題沒有區分公共利益拆遷和商業開發拆遷,很容易引發一些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合謀的情況。
“《拆遷條例》強調‘管理’,體現的是傳統的單向的、政府控制的理念,這與政府目前追求的治理理念是矛盾的。在法律上,則與財產權保護的法律規定相抵觸。”
“其實,我之前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就有過研究,畢竟,這是定制于2001年的法律條文,早已跟不上現代化城市發展進程,”王錫鋅說,“唐福珍自焚事件,給了我心中極大的刺激,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會受到觸動。”
觸動之后是行動。北大五位法學學者的上書建言成為2009年末又一輪新聞熱點。上書建言國務院之后,王錫鋅和他的同事們就陷于被媒體圍追堵截的境地中,各路媒體蜂擁而至,向他們詢問新拆遷條例形成草案的改變、困難以及進度。
他們一一解釋,不厭其煩,盡管很多問題已經回答過很多遍,但是依然會有記者前來詢問。法律的建設不僅需要法律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媒體的輿論,更需要公眾的參與,王錫鋅這樣認為。所以,他一遍遍地向媒體解釋新拆遷條例修改過程中的主體,阻力,以及改變。
他希望能通過媒體將改變之急迫的信息帶出去,讓社會的法制建設更完善。
“我總是相信,這個社會的法制建設會愈來愈好,這離不開法制工作者的努力,也離不開媒體的關注。”王錫鋅如此表達他的信心。
民主在行動中
其實,在2008年,王錫鋅就曾經有過一次引人矚目的建言申請。
2008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頒布實施,依據《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方式有兩種:政府主動公開和依公民申請公開。其中,“依公民申請公開”是指市民可以申請要求公開沒有在網上或其他途徑主動公開的信息。
5月30日,王錫鋅、沈巋、陳端洪三位教授根據這項規定向北京市發改委、交通委和首都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分別提交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了解機場高速公路收費數額、流向等信息。“給市發改委的申請,我們是自己當面遞交的,申請號是12、13、14。工作人員說,此前他們還沒有受理過關于要求高速公路收費信息公開的申請。”王錫鋅說。
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申請?王錫鋅說:“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開始實施了,政府信息公開作為一個制度平臺,對公眾知情權的落實到底能發揮多大的作用?信息公開的制度到底能夠有多大的生命力?這些不能僅僅靠理論上的分析,更需要實踐的檢驗。我們選擇一個公眾關注的話題,用這一話題來測試制度的運行,這本身就是在為推動這一新的制度實踐而進行的努力。”
北京大學三教授上書申請公開高速路收費一時間成為2008年夏天的一個重大新聞,許多人拭目以待。 6月24日,北京市發改委和交通委做出了對該《申請》的答復。但答復中只明確表述了機場高速的投資總額及四年來的通行費收入,未對“貸款總額和收費資金去向”這一核心問題給予直接答復。
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自2009年10月1日之后,天竺收費站已改為有限的“單向收費”,“雖然不能說這是我們申請的結果,但也算是一個進步吧,我們會繼續推進此事!”王錫鋅說。
盡管出師不利,但王錫鋅仍然認為,這次申請有很大收獲,至少喚起了公眾的知情權與公眾的參與意識。“政府信息公開的推動必須有公眾參與,但市民在參與過程中需要技術和知識的支持。” 王錫鋅認為,作為法律學者,自己有義務承擔起市民參與過程中的技術及知識支持的工作。
早在2004年,王錫鋅就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成立了“公共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這是一個獨立的非盈利性學術研究機構,中心的宗旨是:提倡公眾參與活動,推動公眾參與實踐,支持公眾參與活動,觀察和研究公眾參與進程中的問題,促進“富有意義的”公眾參與制度建設。
成立之初,只有王錫鋅與他的學生兩個人,辦公條件簡陋,但推進民主與法制進程的努力卻從未停止。他們先后與北京市政府法制辦公室、廣州市政府法制辦公室合作,在一些政策法規的建設中,“中心”對規劃草案的所有意見進行審查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出具可行性報告。在國務院法制辦與歐盟合作研究的“中國-歐盟公眾參與實踐比較研究”項目中,王錫鋅應邀成為該項目高級學術顧問。
如同在“中心”辦公室懸掛的巨大的條幅“民主在行動中”一樣,王錫鋅認為,民主與法制的推進,不是埋怨,不是發牢騷,而是實實在在地去做事,而他也相信,民眾的參與是推進的動力。為此,“中心”專門開設了一條法律專線,幾年來已經接到了兩千多個求助電話,盡管,其中有一些是與法律民主建設無關的,但是“中心”的工作人員依然給予耐心的解答。
學者是這樣煉成的
說起時下備受關注的法律新聞熱點,說起中國的民主與法制的進程,王錫鋅滔滔不絕,說到他自己,他有些訥言:“對于我自己,我沒什么好說的,我的經歷很平淡,考大學,工作幾年之后是考研究生,考博士,然后留在北大,研究的領域一直是行政法。如此而已。”
盡管近兩年因為關心公眾事務而引發媒體的高度關注,但王錫鋅依然是一個低調的人,他所愿意談的只是他的專業領域,他期望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解答公眾不確知的法律區域,在法制建設的進程中讓更多的民眾參與進來,而不再僅僅是政府與法律工作者的閉門造車。
而在公共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的同事們,則是這樣評價王錫鋅的:
“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
“一個外表沉靜,內心火熱的人!”
他們說這些是有事實依據的:王錫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投入大量的時間到“中心”,為了推進民主與法制建設,也可以為了一個素不相識、前來尋求法律援助的人,不計回報地付出一個法學人的學識、良知與熱忱。
在他很零散的、很少涉及到自己的話語中,有一個名字常常被提起:羅豪才。這位曾歷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致公黨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位的法律界泰斗級人物,是王錫鋅在讀碩士、博士研究生時的導師。
“羅老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學者,我作為他的學生,受益匪淺。”王錫鋅神情悠遠。
王錫鋅沒有說過以羅老為榜樣之類的話,卻在行動中昭示:做學者,不只是固守書齋出學術專著,要有參與社會進程、融入社會進步的積極,還要有心懷國家、心系蒼生的大愛。
少年的王錫鋅喜歡歷史,尤其喜歡中國近代史,他一直想弄明白,有著盛唐般繁華的中國,為何在近百年中受盡列強凌辱?他期望能在史書中尋找到答案。當初的高考志愿之一便是學習歷史,錄取通知書上的專業卻是法律,1980年代中后期,他在中南政法學院度過了熱血沸騰的大學時代。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喜歡關心時政,喜歡暢想未來,擁有無窮的夢想與激情。在時光的長河中,有的人將激情轉為憤怒,有的人將夢想藏匿于現實,王錫鋅卻一路沉靜地走來,在漫長的學術道路中,始終揣著一顆熱氣騰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