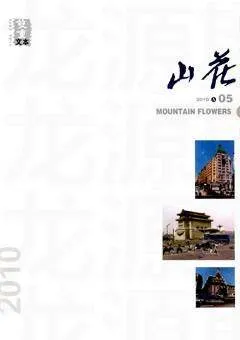對話:還鄉的可能性
藍調讓人迷醉 朵 漁
1)把你的《藍調》又拿出來讀了一遍,呵呵,讀得心向往之。美妙啊。
一個創造性的場,那真是詩人的幸福。
我覺得,在一個豐衣足食的時代,詩歌的場大概就在酒吧、咖啡吧、茶吧、書吧、小女子的私人聚會……上吧。一個半公開的、半私人的、半精神半物質的、半空中的(比如,二樓)、半醉半醒的、半矯情半認真的……場域,大概就是當下詩歌的流行場域了。
在這個場域里,至于能否招魂,能否呼喚出原始的巫性,我也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
有一半,就好了。完全的純粹,在詩人那里是可能的,在讀者,觀眾那里,幾乎不可能。但有一個場,就有可能的交流存在。
這一半,就足夠我們享受。
藍調讓人迷醉。
2)前兩天我去酒吧體驗了一下,一個朋友的電影活動,來了很多年輕人,他們問我:為什么詩人很少在這種場合現身?他們大多喜歡詩,但理解有限。我也想,是啊,為什么詩人很少現身?
現在有很多藝術的場,有詩人現身的場卻不多。詩在紙上流傳的傳統,如今是否應該有所改變?況且,紙上流傳的,只是詩的一部分,詩人的“肉身”并沒有參與。而這是不完整的。詩人應該直接去面對自己的讀者,創造一個身體性的現場,以此完成自己的作品。
很多拙劣的、表演性的偽現場已敗壞了詩歌的場。無論是廣場上的、大會堂的還是劇院的,都已成為“表演藝術”的一部分,詩不在了。甚至連大學里的詩歌現場都凋敝了。酒吧,藍調,我的理解是。詩人以肉身的、出神的狀態,與小眾們共同創造一個詩歌的場。如此,也許真會招出詩歌的魂。
直接面對你的讀者,這讓我激動不已。
詩人不該把自己藏起來,也不必以流氓和名士自居。打倒詩歌的“春晚”,以“詩人”的本義現身,這很重要。
要有勇氣現身,并且要有能力現身。
驚蟄已過,北方還在飄雪,季節有些紊亂。
“念詩”的正式提出,確實能恢復詩歌的一種能量 方閑海
宏論已仔細閱讀!很有意義。因為它能將許多詩人所感的意識轉化為一種行動。你提出的“念詩”的概念是一種針對舌頭音階的調音,并以“心”為出發點,本質是王之喚的“以心擊之”。至少在我的詩歌中,寫的過程伴隨著許多下意識的“念詩”過程,絕對不是“朗誦”,這里面其實包含了“音樂性”。“念詩”貼近著詩人在日常中如何勞作的經驗,能體現一首詩最本質的一個側面。我以前聽聞的“節奏布魯斯”一詞,它的出現其實也暗合著詩歌的“念詩”過程中對節奏的體會和處理。唯一出乎我意料的是你對咖啡館和酒吧的首肯,而事實確實是這樣!讓人感覺有意思的是,中國的茶館不是一個理想之地,或許,是因為咖啡和酒都攜帶著讓人“飛”的基因,而詩歌是需要一點飛行的氣質的。近年,你在現場中屢有出色的詩歌活動,充滿活力。我想,“念詩”的正式提出,確實能恢復詩歌的一種能量!古代所謂的“吟詩”,肯定不是“朗誦”!這是時代里被重新擦亮的一個常識。
創造的抵達——從廣場到部落 賀 念
我以為這篇文章是你長期以來追尋詩歌道路上的一顆碩大的果實。從早期《拒絕隱喻》和之后的《詩言體》等文本來看,你的工作主要是“去蔽”,也就是去掉“詩言志”和“詩無邪”對作為“體”的詩歌本身的遮蔽。詩作為體,是指“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是指真實的生活和生命(包括身體和日常生活中永恒性的一面),指世界本來的樣子,而不是應該的樣子。這樣,你早期的這些思索便實踐了對詩歌本身的一種召喚,它在時代的進程中曾體現出了巨大的革命意義。而《還鄉的可能性:從詩的藍調開始》真正讓你找到了詩歌本身(作為體)得以存在起來的場!它不僅僅是關于當下詩歌寫作的一種可能性的思考,而更是詩歌和這個時代的關系的思考,或者如你所感到的,它思考的是詩歌自身的家園問題。
1)白話詩是與舊體詩本來所有的那個場的分離。舊體詩的格律化就是一種發表的方式,它使詩歌便于傳誦,并因此構成了一個非常自然的少有外力影響的民間鑒賞系統。而舊體詩在內容上,強調與自然(鄉村)的關系(融合),對天地的贊美,以及對個人情感(感受性)的抒發。這兩方面構成了舊體詩的場。而白話詩一開始的使命首先是主動與這個場分裂,這源于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根本改變,也源于一個舊的封閉的系統總會有它自然的壽命。
白話詩更加的自由,這是他的優點,起點,也是它的使命。它允諾了容納西方個體精神的空間。它將時代人復雜的人性和生活之思帶進了語言。可以說,白話詩從一開始,是在暴風雨夜誕生的一個孤兒,但就是因為它的孤兒身份,賜予了它難得的自由。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如果有什么真正的新的精神在中國漢語古老的土地上扎下根來,新詩就都是它新生的土壤。因此,新詩在過去的革命歲月中,在廣場上,在海報上,在宣傳欄上,在廣播和傳單中頻頻扮演歷史的舵手。這樣便興盛起了朗誦的傳統,朗誦注重的聲音的放大,是掌聲,是“志”的鏗鏘有力,而不是思,不是體。
2)然而,在中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社會轉型以及新世紀的網絡時代影響下,新詩又重新成為了孤兒。因為廣場上的人散了,傳單散落一地,無人理會。在網絡起初所形成的一片自由的歡樂氛圍之后,它也重新成為了一個廣場。詩歌寫作又重新成為了為朗誦而寫的寫作。只是這回更加可憐,因為虛擬的網絡廣場讓那些高臺上搖旗吶喊的家伙只能在很少的范圍內享受虛擬的雷鳴般的掌聲。詩人成為一幫顧影自憐的一座座小山的霸王。但是這卻恰恰更加敞開了新詩作為孤兒的實質,在上一階段,新詩并沒有真正獲得自己的這一身份,因為它是被歷史裹挾的,有著意識形態的巨大包袱,無數異己的力量掌控著它的成長。這或許是新詩真正獲得新生的契機。
新詩自己必須長大。而這長大伴隨著它必須告別革命,告別朗誦和廣播,回到思。回到獨立成長,擺脫揠苗助長。這意味著新詩必須找到自己真正的場。這個場不在自然(大自然,鄉村),而在現代生活之中,在現代生活里那些保留了思的可能性的空間。“我以為,今天,新詩應當退出廣場,禮堂,回到部落。”更重要的是,新詩的這份成長,是創造的抵達,是向著自己的本己性自然生長!回到部落,不是又一場革命,而是回到自身,并開始生長。不管詩歌是起源于勞動還是祭祀,我認為它一開始都是為了讓人的身體和精神更加自由,讓身體的節奏更加協調,讓精神得到安寧,讓思得以通過文(紋)呈現。并且在這個過程中,詩實現了人與人的交流,人與神(天地)的交流,人與自身的交流。詩人扮演的是這一交流得以可能的橋梁,也就是說他是傾聽到了詩,并將其表達出來的人。詩人溝通著天與人。詩人首先是傾聽,再有所謂創造。于此,詩歌在古代的神壇上,在群體勞作的大地上,在屈原徘徊的江邊,在流觴曲水列坐其次的朋友聚會中,在琵琶聲聲的江船上發生了。而在當代城市,寫作成為個人的事業,詩歌發生在室內,在獨立的居所,而詩歌的發表(流傳和欣賞)發生在當下城市部落:酒吧和咖啡館。
而在形式上,新詩自由的特質決定了它必須敞開自己,為所有的語言都留有空間。它是開放的,它做著加法。它必須可以具有各種不同的節奏,并讓它們各自找到自身,和諧共存。
3)難能可貴的是,不是通過理論,而是通過身體的現場的實踐,以上二者,在現實層面和語言層面,都讓你非常自然地通過一場別具一格的念詩會找到了新詩所需要的場!布魯斯音樂的即興和自由,開放和沉靜,酒吧和咖啡館相對獨立的室內環境,文字(語言,通過電子屏)和聲音(念,通過話筒)的同時顯現,觀眾的現場參與,都給思在這個時代的現實生活當中的到場提供了可能。這里便是新詩成長的家園。它敞開了新詩還鄉的可能!它不是簡單復古,它不是一種主觀意愿的傾瀉,而是統一了過去的未來,是走向未來的抵達。我看了你現場念詩的視頻,效果非常好,這場儀式創造出了一個場,這個場是詩人自身的表達需要的,也是觀眾的接受所需要的,是詩歌孤兒在這個技術無聊主義的時代里的自身成長所需要的。我相信,將有更多對思饑渴的人們,會感受到它的好玩,它的魅力。
讓我們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