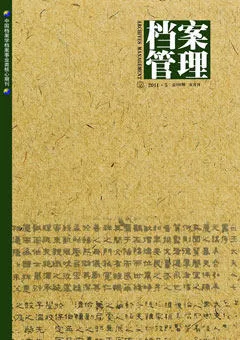我國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價值研究
摘要:古代“三農”檔案的記錄、保存、匯編,與文化的傳承、延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文章通過釋讀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內容,剖析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結構與文化價值,并以此為基礎,探討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開發利用。
關鍵詞:古代;“三農”檔案;直接遺存;間接遺存;文化價值;開發途徑
古代“三農”檔案遺存,是古代圍繞“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而形成的歷史記錄的總稱。依據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存在形式,可將其分為“直接遺存”和“間接遺存”兩類。古代“三農”檔案“直接遺存”,指以原始記錄形式流傳至今的檔案原件;古代“三農”檔案“間接遺存”,指經過輯佚、著錄、加工而載于農書、史傳、方志、譜牒等各類文獻中的間接記錄。
縱觀古代“三農”檔案遺存,它不僅記錄了農業、農村、農民歷史發展、演變的軌跡,而且,再現了歷朝對“三農”問題的解決方法,并折射出了歷代農民在生產、生活中的思維方式、行動準則和價值觀念。
1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內容與結構
1.1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內容。我國古代“三農”檔案遺存數量浩繁、內容豐富,無不體現出濃厚的農耕文化特色。現分類擇要簡述如下:
1.1.1關于農業生產的記載。如,竹簡《秦律十八種》的《倉律》,規定了每畝土地播種量:“麻畝用二斗大半斗,禾、麥一斗,黍……畝大半斗,菽畝半斗。”…另如,
《康熙御制耕織圖》(現藏北京故宮)以“殿版畫”形式描繪了谷物從浸種、播種到入倉和養蠶從育蠶、采桑到成衣的生產過程,每幅圖上,還有康熙所書的“耕織要領”詩文。
1.1.2關于農田水利的記載。如,我國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通濟堰(位于浙江麗水市蓮都區碧湖鎮堰頭村),建于南朝蕭梁天監四年(505年),自古留有堰史,并有自成系統而完整的管理方法,現存石刻《通濟堰圖碑》及水系圖碑,可以清晰看出該堰的灌溉功用。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處州太守范成大制定的《通濟堰規》共20條,科學而全面,沿用600多年。另據《清朝蘇州府水利表》統計,康熙十年至同治十三年,興修水利工程多達63項。
1.1.3關于土地賦役的記載。如,圍繞土地關系和賦稅征收,歷朝歷代都形成了大量的土地戶籍賦役檔案。現保存在浙江蘭溪市財稅局的746冊“魚鱗圖冊”,就記載著清代同治年間蘭溪城區及35個鄉鎮、159個村的田土、山林、地形、地貌等情況。
1.1.4關于農民習俗的記載。此類檔案遺存文化內容包括服飾、飲食、婚喪、節慶、娛樂等諸方面。如,浙江青田“俗尚簡樸,衣用大布,食飲不貴異物,貧富不相耀”(雍正《青田縣志》卷4《風俗志》)。另如,浙江云和縣沙鋪鄉,民間“做功德”習俗已逾200年,逐漸衍變為沙鋪山歌,有勞動號子、田歌、節令歌等,多為雙句、七字句式,現直接遺存有300余首。
1.1.5關于農民增收的記載。如,反映農民種植經濟作物而增收的情形。清同治年間,臨湘種茶“價乃三倍,……幾成樂園”(同治《臨湘縣志》卷4);清光緒年間,浙江余姚種棉“其息歲以百萬計,邑民資以為生者有十之六七”(光緒《余姚縣志》卷26)。另如,反映農家開展多種副業生產而增收的情形。清嘉慶時,浙江山陰縣造紙業興盛,“天樂鄉出紙尤盛,民家或賴以致饒”(嘉慶《山陰縣志》卷8)。
1.2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結構。檔案文化不僅包含物質層面,同時,包含精神層面,檔案文化結構是一個“多環形”結構。只有認清檔案遺存的文化結構,才能科學地解讀檔案遺存。筆者認為,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結構,由外到內包括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心態文化三個層面。
1.2.1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表層文化結構——“行為文化層”。此層由人們能直接感受到的檔案文化現象構成,其內容較易受社會文化影響,能直接展現檔案文化的功能,是檔案文化中較為活躍的部分。以約定俗成的禮俗、民俗、風俗等形態表現出來的行為模式為典型代表,如,浙江遂昌縣“班春勸農”開犁習俗、蓮都區“翻龍泉”表演程式等。
1.2.2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中層文化結構——“制度文化層”。此層是對檔案活動的抽象表現,并受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的雙重制約,同時,又實現著文化連結、文化控制的功能。最明顯地表現在農民生產勞動、娛樂活動中組建的各種行為規范。如,浙江松陽縣玉巖白沙崗高腔的口傳心授、慶元縣香菇栽培隱語等。
1.2.3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深層文化結構——“心態文化層”。此層所包含的內容多為觀念、心理、思維方式等,是人們難以察覺的部分,同時,電是檔案文化中最能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部分。古代“三農”檔案遺存中蘊含著農人的價值判斷、審美情趣等主觀意識和精神理念。如,浙江云和縣農村的以“和為貴”精神、縉云縣農村的“耕讀家風”理念等。
2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價值
2.1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價值類型
2.1.1從空間橫向看,古代“三農”檔案遺存具有本體價值和環境價值。承載著歷史信息的檔案遺存,其價值主要從本體價值中體現。但任何事物都有其產生的特定土壤,古代“三農”檔案遺存同樣離不開其產生的環境,帶有濃重的民族、地區等烙印。如浙江遂昌縣妙高鎮金溪樹,明代時,黃氏“門才稱盛,幾乎人人有集”(吳世涵《宜園筆記》)。同姓同地,家學相承,形成具有族群地域特色的作者群體,該村其他時段、其他村同時段卻無此類現象。因此,剖析檔案遺存的文化價值時,應結合當時歷史環境去解讀。
2.1.2從時間縱向看,古代“三農”檔案遺存具有初始價值和衍生價值。古代“三農”檔案自形成之日就被賦予某種特定價值,即為滿足當時人們某種需要的價值,此為“初始價值”。隨著歷史發展和情境變遷,不同時代的人們與檔案遺存之間,不停地構筑出新的價值關系,諸如,喚醒記憶、追隨信仰、啟迪心智等,這些屬于“衍生價值”。換言之,古代“三農”檔案遺存作為一種“己在”客體,潛移默化地對人類思想情感產生著持久的影響,塑造著人們的文化心理結構,同時,人類作為能動的認識與實踐主體,又不斷調整、更新著對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定位和闡釋。
2.1.3從三維結構看,古代“三農”檔案遺存具有核心價值和附屬價值。核心價值是一切其他價值存在的基礎,圍繞核心價值的外圍價值為其附屬價值。如,清水江文書中的山林契約,作為地權的法律憑證價值,是其在歷史上得以長期保存的主要原因,而這些山林契約所具有的社會學、經濟學、民俗學、人類學等方面的巨大價值,被專家稱為我國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代文獻”和“徽書”之后的“第三大珍貴歷史文獻”,從而成為“顯學”。
2.2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價值觀
2.2.1“天人合一”的樸素哲學觀。中華文化產生于以農業生產力為基礎的古代社會,風調雨順對生產和生活的巨大作用,使人們對天地自然有一種牢固的親近感。這種“天人合一”的觀念以檔案形式不斷傳承下來。現存浙江龍泉市安仁鎮花庵村,刻立于清道光十二年的《勒石示禁》碑,內容為“山林禁示”,強調“愛護森林,嚴禁濫砍濫伐”。這種哲學思想體現在當代,就是在社會建設中注重自然環境的保護,使生態與社會和諧發展。
2.2.2“政教合一”的規訓引導觀。傳統儒學無論是在政治體制還是日常觀念、心理結構等基本層面,均起著支配作用。如“厥或誥日: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侯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尚書·酒誥》),勸誡子民不要沉湎于酗酒。當時,上級針對一些不良習俗而對百姓的教正與禁止,至今,仍具有借鑒意義。
2.2.3“道德倫理”的本位人生觀。以道德倫理為本位的特質,促成中國傳統的人生價值觀,且深深凝刻在各種檔案中。歷代的族約、宗規、家訓,滿是家族祖先的恩榮善舉,并以此約束族人的思想觀念,對于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了一定作用。現藏于四川省檔案館的巴縣婚俗檔案里,存世稀少的清代“庚帖”、“喜課”,喜慶味十足,但背后婚姻生活大都帶有悲劇色彩。
2.2.4“以民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萬民百姓是國家的根本,治國應重視安民、得民。《周禮·地官司徒》載“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根據土地肥瘠分為九等并確定不同稅賦,同時,還制定“散利”、“薄征”等荒年賑災政策,即貸給農民糧食,減免賦稅、徭役等。
2.3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價值特征
2.3.1符號特征、感性特征、意義特征同時并存。古代“三農”檔案遺存,是農耕文明的“貯存器”,既體現在“感性”的實物載體上,又濃縮于“符號”的信息載體內,而且,又蘊含著一個意義世界。感性世界、符號世界、意義世界三者的完美統一,充分展示了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價值。例如,古代民間書信和簿冊中,有許多為了適應文字便捷化需求而出現的“俗文字”,涵蓋了文字發展的許多階段,有“篆隸楷行草”等多種字體,書法風格各有不同,為“俗文字”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
2.3.2積累特征、傳播特征、創新特征相依相隨。人類文化之所以能夠綿延不斷地發展,正是檔案長期積累和傳播的結果。古代“三農”檔案信息得以流傳,才使后人有幸目睹先人農業生產經驗和生活習俗。在傳承的同時,古代“三農”檔案文化也獲得了新發展,其創新特征尤為明顯地表現在農耕技術的改進上。
2.3.3顯性特征、隱性特征、利用特征互相促進。古代“三農”檔案遺存承載著多姿多彩的歷史故事,可將人們引入廣‘闊的、變化的跨時空交流,不斷滿足著人們求知和文化休閑的需要。然而,許多“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價值不是顯性的,只是在保存載體的同時保護了其文化價值,未能使價值得以具體體現,隨著近年人們研究、開發、利用幅度的加大、層次的加深,其文化價值才得以逐漸顯現。
3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價值開發途徑
3.1大力發掘,豐富寶庫。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古代“三農”檔案直接遺存跟其他檔案一樣,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存世量己不多。為了保護好古代“三農”檔案直接遺存,筆者認為,可通過普查、田野考察的形式進行發掘、考證,充分利用申遺、檔案記憶工程,將其轉化為文字或圖片保存下來,建立古代“三農”檔案直接遺存數據庫,為以后的“三農”文化研究奠定堅實的實體史料基礎。
3.2加強互動,廣泛征集。古代“三農”檔案遺存,大多活躍在基層群眾當中,遺存在老百姓的家門口。在征集時,應走“社會化”道路,面向民間大眾,特別需要處理好與社會公眾的互動問題,通過深入走訪、耐心細致的溝通,讓民眾主動獻“寶”。如,為了征集水書,貴州省荔波縣檔案館館長姚炳烈曾親自到老家的寨子里,用水族最隆重的禮節招待德高望重的寨佬們,用水話和他們拉家常、唱山歌,終于贏得信任,得到他們的捐贈。據筆者調查,現存浙江遂禺縣檔案館的清朝地契、田契、山契等6l件珍品,也是檔案工作人員在多次走訪、促膝長談的基礎上,從農戶家中征集到的。
3.3多方宣傳,擴大影響。占代“三農”檔案遺存既似“深巷佳釀”,又如“鄉野土產”,需要“叫賣”,需要“包裝”,以使人們更好地品味其魅力。如,“錦屏文書”,是苗侗少數民族混農林生態體系唯一記載較好的檔案遺存。貴州省錦屏縣高度重視宣傳工作,《錦屏文書文化底蘊外宣工作方案》獲“貴州宣傳思想工作創意獎”。《錦屏文書:塵封百余年的文化遺產》等被《中國文化報》、《中國綠色時報》頭版頭條刊登,社會反響良好。如今,“錦屏文書”百度搜索網頁多達25.8萬條。在宣傳形式上,要多管齊下,包括報道新聞、印制內部資料、出版圖書、制作光盤、在互聯網上發布多媒體產品等,充分吸引眼球,進而向更深層次開發古代“三農”檔案遺存價值進軍。
3.4開展編研,傳承創作。對古代“三農”檔案遺存進行編研時,選題應盡量與當今人們的衣食住行密切相關,如民間小吃、農村服飾、鄉村保健藥品、鄉問節令習俗等。編研產品也不必拘泥于文字這一種形式,可大膽嘗試圖片、短片等各種形式,逐步積累和豐富編研成果。
在對古代“三農”檔案遺存進行編研的同時,還應重視其傳承創作。如,浙江云和“包山花鼓戲”本是民問的“死檔案”,經過電視臺、藝術劇院創作組等“惠顧”而“活”了起來。在自成一體的本土唱腔里融入新人新事新風尚,推出了不少精品佳作。可見,長年累月密封牢鎖或者散落鄉問的古代“三農”檔案遺存,只耍在原有檔案基礎上融入新的構思,便會使傳統文化重新煥發生機。
3.5建設基地,舉辦活動。在古代“三農”檔案遺存較為集中的地區,設立教研基地,應是開發利用古代“三農”檔案文化的新途徑。如,安徽省績溪縣上莊鎮宅坦村保存著明嘉靖以來的宗族、村務文獻資料1800冊(份),目前,該村已成為多所國內外知名大學的多學科教學實習基地。
當然,要開發古代“三農”檔案遺存的文化價值,必須營造濃厚的文化氛圍。在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工作的情況下,配合黨和政府的宣傳任務、重大紀念活動等宣傳契機,適時舉辦豐富多彩的活動,讓古代“三農”檔案遺存走進千家萬戶,真正融入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