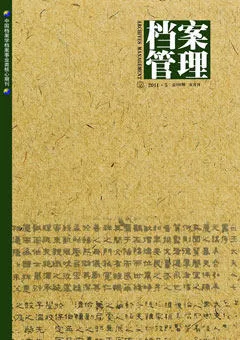“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與分析
摘要:本文通過對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的現(xiàn)狀及所面臨的問題、發(fā)展的趨勢等方面進行統(tǒng)計調(diào)查,旨在闡釋“城市記憶工程”的產(chǎn)生及其發(fā)展是與社會經(jīng)濟、檔案事業(yè)發(fā)展的大背景分不開的,它在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諸多特點既是它的優(yōu)勢又是它深入擴展的局限因素,全面了解和認(rèn)識這些因素,是具體分析“城市記憶工程”與我國檔案事業(yè)發(fā)展之間關(guān)系的重要基礎(chǔ)。
關(guān)鍵詞:城市記憶工程;現(xiàn)狀;調(diào)查;分析
“城市記憶工程”的提出,緣于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當(dāng)代著名作家和畫家馮驥才為“搶救天津老街”而發(fā)起的“歷史文化考察與保護”活動。2002年,青島市率先提出“城市記憶工程”,在其示范效應(yīng)的推動下,武漢、廣州、上海、大連等地也相繼推出“城市記憶工程”項目。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我國開展“城市記憶工程”的城市已有十幾個大中小城市,而且,不斷有新的地區(qū)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這一活動正呈現(xiàn)逐層推進的良好發(fā)展勢頭,“由自發(fā)走向自覺”,不斷豐富和發(fā)展“城市記憶工程”的內(nèi)涵,為完整地記錄和追尋城市發(fā)展的歷史軌跡作出自己的努力。本文主要是通過對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的時代背景及其開展現(xiàn)狀的一些情況進行調(diào)查和分析,為我們?nèi)嬲J(rèn)識和了解“城市記憶工程”與我國檔案事業(yè)發(fā)展之間的關(guān)系奠定基礎(chǔ)。
1“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的時代背景
1.1消失的城市記憶。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社會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城市的面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許多具有民族風(fēng)格和地域特色的老街區(qū)也毀于一旦,代之而來的是千篇一律的高樓大廈,少數(shù)保存較為完美的城市古街坊區(qū)也因城市規(guī)劃不科學(xué)而變得面目全非。近20年來,我國很多城市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舊區(qū)改造,采用的幾乎都是“拆除重建”的單一模式。其中,不少城市甚至發(fā)生大規(guī)模拆除歷史保護街區(qū)和優(yōu)秀保護建筑的嚴(yán)重情況。如福州發(fā)生拆毀三坊七巷和朱紫坊歷史街區(qū)事件;襄樊宋明城墻一夜之間被夷為平地;“遵義會議”會址周圍的歷史建筑被一拆而光;曾是明代抗倭前線、清代“鴉片戰(zhàn)爭”主戰(zhàn)場和近代民族工商和外貿(mào)史上名揚海內(nèi)外的寧波商幫發(fā)祥地——孕育和記載著昔日光榮的定海古城,近年卻在“舊城改造”的名義下被大規(guī)模破壞。城市的歷史文化在喪失,特色在消亡。正像《北京憲章》所指出的那樣,20世紀(jì)是一個“大發(fā)展”和“大破壞”的時代,城市中的“建設(shè)性破壞”始料未及,屢見不鮮。
1.2社會吶喊:“搶救老街”。當(dāng)代著名作家和畫家馮驥才先生非常關(guān)注歷史文化名城和歷史街區(qū)的保護。面對具有六個世紀(jì)的天津老城面臨被徹底拆除的命運,他痛心疾首,發(fā)出“手下留情”、“搶救老街”的吶喊。馮驥才先生的吶喊代表了社情民意,他是眾多關(guān)心城市歷史文化保護人士的杰出代表。更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城市歷史文化風(fēng)貌保護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這為檔案部門開展“城市記憶工程”提供了扎實的社會基礎(chǔ)。但社會對城市記憶的保存和傳承缺乏延續(xù)性,缺少一個有力的、權(quán)威的實施主體,這也為檔案部門開展“城市記憶工程”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1.3“檔案部門主動為城市留下記憶大有可為”。2002年3月起,青島市檔案部門正式啟動了“城市記憶工程”,計劃用4年左右的時間建立起一個全面反映青島市基本面貌的多媒體檔案信息數(shù)據(jù)庫,與互聯(lián)網(wǎng)互聯(lián),面向社會開放。2007年,“檔案與城市記憶”論壇在上海市檔案館舉行,來自十多個不同城市的檔案工作者互相交流了在城市記憶工程建設(shè)中的經(jīng)驗和體會,并進一步探討了檔案部門在構(gòu)建城市記憶中的作用,推動城市記憶工程更好地開展下去。國家檔案局副局長段東升在會議中指出,用“記憶”詮釋檔案起碼有三個現(xiàn)實意義。一是可以增強公眾保護檔案的自覺意識,且更容易拉近檔案與公眾的聯(lián)系;二是可以增強社會和公眾對保仝檔案文獻遺產(chǎn)的責(zé)任感;三是有助于檔案部門拓寬檔案資料收集工作的視野。檔案部門開展城市記憶工程,不僅是對檔案工作自身的一種創(chuàng)新,也是保護和傳承城市歷史文化的一種負(fù)責(zé)任的行為。
2“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現(xiàn)狀及其分析
2.1“城市記憶工程”的“生存”現(xiàn)狀。結(jié)合2007年在上海舉辦的“檔案與城市記憶”論壇的報道以及網(wǎng)絡(luò)搜索,據(jù)不完全統(tǒng)汁,目前,我國開展“城市記憶工程”的城市己有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武漢、廣州、沈陽、太原、長沙、福州、大連、青島、柳州、南通、蘇州、威海等50個大中小城市,而且,這一活動正在逐步地擴展,不斷有新的地區(qū)加入到“城市記憶工程”的行列中來。如,上海的黃浦區(qū)、閘北區(qū),遼寧的朝陽市,山東的榮成市,安徽的宣城,江西的彭澤縣,等等。在所調(diào)研的50個大中小城市中,“城市記憶工程”的實施主體為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的城市有47個,縣級市的城市有3個;“城市記憶工程”以綜合檔案館為實施主體的城市有43個;以城建檔案館為實施主體的城市有3個;以市政府、大學(xué)為實施主體的城市有2個:其他如澳門基金會、上海特奧執(zhí)委會為實施主體的共2個。可見,“城市記憶工程”目前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開展,在小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還有很大的發(fā)展?jié)摿Γ淮蠖鄶?shù)實施主體是綜合檔案館,部分是城建檔案館和社會其他主體,綜合檔案館與其他社會主體合作開展的城市有6個。因此,綜合檔案館在“城市記憶工程”的開展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但需要進一步加強與其他部門的合作能力和范圍。
從“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的地域分布上來分析,將其開展的地域范圍按照東部沿海、中部內(nèi)陸、西部邊遠地區(qū)、港澳臺來劃分(1987年,國家“七五”計劃首次提出“我國經(jīng)濟區(qū)域按東、中、西三大經(jīng)濟地帶或地區(qū)”的劃分方法,東部包括遼、京、冀、津、魯、蘇、滬、閩、浙、粵、桂、瓊12個省市區(qū):中部包括內(nèi)蒙古、晉、吉、黑、皖、贛、豫、鄂、湘9個省區(qū);西部包括川、黔、滇、藏、陜、甘、青、寧、新、渝10個省區(qū)。“七五”以來,國家基本上是依照這種劃分來制定相關(guān)政策措施的。在之后的全國“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biāo)綱要中,國家仍采用這種劃分方法)。其中,東部沿海地區(qū),包括遼寧、山東、河北、北京、天津、上海、江蘇、福建、廣西:中部內(nèi)陸地區(qū),包括湖北、安徽、湖南、河南、內(nèi)蒙古、江西、黑龍江;西部邊遠地區(qū),包括四川、寧夏、重慶。可以得出下圖(圖1)。

在港澳臺檔案部門的官方網(wǎng)站上,則很少有城市變遷發(fā)展方面的信息,他們更多是提供市民查閱利用的一些檔案信息。那么,他們又是如何看待在城市變遷的過程中,檔案部門的職責(zé)和作用的昵?本文就這一問題向香港歷史檔案館作過調(diào)查。香港政府檔案處相關(guān)負(fù)責(zé)人的答復(fù)是:“(香港)歷史檔案館的職能是鑒定和保存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和資料。我們現(xiàn)時管理超過100萬項歷史檔案及圖書資料,記錄政府不同方面的工作、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交流和溝通,以及推動香港轉(zhuǎn)變和發(fā)展的主要事件和活動。這些藏品來自300多個政府部門、民間團體和個別市民,涵蓋的內(nèi)容,包括金融、商業(yè)、教育、交通運輸、土地發(fā)展、法律和社會事務(wù)。此外,政府新聞每年都會出版《香港年報》記錄香港在各方面的發(fā)展。在政府新聞處的網(wǎng)頁內(nèi),還可以找到更多最新的香港發(fā)展記錄。歷史檔案館保存有政府刊物,圖書館亦保存了《香港年報》,以供市民查閱。”因此,由于港澳臺地區(qū)檔案部門的具體職責(zé)和政府部門的職責(zé)分工存在一定的差異,他們與內(nèi)地各省市檔案館在對待城市變遷的問題上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在所調(diào)研的50個大巾小城市中,其中,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城市有32個,中部地區(qū)的城市有14個,西部地區(qū)的城市有3個,澳門1個(澳門“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的情況,目前查閱到的信息量太少,因此,沒有展開論述)。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城市記憶工程”在東部地區(qū)開展的情況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時間的持續(xù)性都高于中部地區(qū),中部地區(qū)開展的情況高于西部地區(qū)。這種差異跟我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存在地域上的差異,及其社會公眾社會心理的變化等因素有一定的關(guān)系。首先,檔案部門開展“城市記憶工程”,無論是否得到一定的資金支持,檔案部門都需要調(diào)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資金去具體負(fù)責(zé)實施。其次,“城市記憶工程”的最終目標(biāo)是為了向社會公眾展示檔案反映、詮釋、表現(xiàn)社會變遷的真實性、權(quán)威性、形象性等,這就需要借助檔案展覽、論壇等一定靈活的方式來實現(xiàn)。這些活動開展精彩與否,往往跟檔案部門社會活動能力的強與弱有著直接關(guān)系。最后,“城市記憶工程”能夠繼續(xù)深入開展下去的最根本動力則是社會公眾的認(rèn)可和支持。改革開放30周年,我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公眾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著懷舊情緒和今昔社會生活對照的社會心理需求。只要檔案部門能夠充分利用好檔案館藏資源,能夠迎合和滿足這種社會需求,就一定能夠得到社會公眾的認(rèn)可和支持。目前,“城市記憶工程”的開展雖然還受制于社會、經(jīng)濟、文化等諸多要素的牽制,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無論一個城市經(jīng)濟發(fā)展如何,都需要追尋自己的“根”和“魂”,都需要擁有自己的記憶。只要“城市記憶工程”不斷地拓展自己的范圍,就能夠進入一個更加廣闊的領(lǐng)域。
2.2“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的內(nèi)容及其特點。根據(jù)調(diào)研,“城市記憶工程”的主要內(nèi)容是記錄城市面貌(包括城市的地名、風(fēng)俗文化、城市面貌對比等)的城市有33個;工程從檔案資源建設(shè)(包括檔案的收集、征集,檔案資源的開發(fā)利用等)著手的有33個;記錄城市發(fā)展中重大事件的有9個;從服務(wù)社區(qū)到服務(wù)社會的有1個。其中,城市記憶工程在城市面貌的記錄方面和檔案資源建設(shè)有多數(shù)是重合的。可見,“城市記憶工程”目前還處在記錄城市面貌這一初始階段,還只是以檔案資源建設(shè)的一個手段來影響檔案事業(yè)的發(fā)展。“城市記憶工程”的進一步發(fā)展還需更具前瞻性和權(quán)威性的理論作指導(dǎo),進一步向更深層發(fā)展。
在對“城市記憶工程”的認(rèn)識方面,共有35個城市采用“城市記憶工程”這一名稱;3個城市采用的是“社會記憶工程”;5個城市采用的是“記憶工程”;其他的名稱有“搶拍石家莊”、“特奧記憶墻”、“城市記憶影像工程”、“城市記憶開發(fā)工程”、“城市數(shù)字記憶工程”、“城市記憶”、“記憶經(jīng)典南通工程”等。由此可知,城市記憶已經(jīng)得到了大多數(shù)檔案部門的認(rèn)可,這為檔案記憶觀在實踐領(lǐng)域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了很好的實踐基礎(chǔ)。

從“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的時間及總量上來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上圖(圖2)。從圖上分析,
“城市記憶工程”自2002開展以來,經(jīng)歷了若干個峰谷,目前所處的情況不容樂觀,但總體是呈上升趨勢。在2008年,“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的情況達到了最高值。結(jié)合當(dāng)時社會發(fā)展的背景,我們可知,2008年,是“改革開放”3jxiCSxGlIukMUSXYvApAJUCjudzCJvL1M9QxFhb372M=0周年的紀(jì)念周年,全國各地都在開展各種形式的紀(jì)念活動。城市記憶中包含了豐富的圖片、資料,可以展示“改革開放”30周年的偉大成就,“城市記憶工程”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充分發(fā)揮了它的資源優(yōu)勢。這也是形成工程發(fā)展的最高峰,而之后又出現(xiàn)較大滑坡的一個重要原因。一方面,這說明“城市記憶工程”的發(fā)展情況跟社會發(fā)展的政治、文化需求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另一方面,這也表現(xiàn)了人們對工程的認(rèn)識還不深入,只是將它作為一個宣傳政績的獻禮工程或者作為提高檔案社會認(rèn)知度的一次性工程,還沒有認(rèn)識到城市記憶對檔案事業(yè)各方面長遠的影響。這也是工程發(fā)展中遇到的一個“瓶頸”,如何實現(xiàn)人們對工程認(rèn)識上的突破,還有待于檔案記憶觀的進一步普及和“城市記憶工程”的深入推廣。
2.3“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的政策支持。“城市記憶工程”是一項復(fù)雜的社會工程,檔案部門作為實施主體,只有得到社會的認(rèn)同和其他部門的支持才能出色地完成這項任務(wù)。從“城市記憶工程”的發(fā)展過程可以看出,“城市記憶工程”的實施得到了各地領(lǐng)導(dǎo)的重視和社會其他部門的協(xié)力配合。根據(jù)調(diào)研,可以得出以下表格。
下面的表格顯示的只是一部分城市的情況,其他城市如武漢市啟動“城市記憶工程”是由市長親自提出動議的;朝陽市則明確提出實施“城市記憶工程”需要聯(lián)動的單位,詳細列出資源信息采集工程、城市變遷記錄工程、重大事項采集工程、檔案資料征集工程、地域文化搶救工程、人物數(shù)據(jù)采集工程聯(lián)動單位的名單。南通市檔案局的朱江,在2007年“檔案與城市記憶”論壇中總結(jié)經(jīng)驗時說,要使“城市記憶工程”獲得滿意效果,檔案部門就要與社會形成多種互動。互動不僅可以引起社會更多的關(guān)注和支持,同時,還能深化“城市記憶工程”,將城市記憶活動的成果融入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中,在社會經(jīng)濟、文化等領(lǐng)域發(fā)揮檔案的獨特作用。
2.4“城市記憶工程”所帶來的社會效應(yīng)。在開展“城市記憶工程”的過程中,各個城市結(jié)合本地域范圍內(nèi)的歷史文化和人文積淀,以各自鮮明的主題開展了各具特色的活動。如北京市檔案館從胡同入手梳理城市記憶,在小胡同里做大文章:廣州市城建檔案館以城市各類景觀圖片和“鳥瞰廣州”航拍成果展展示不同時期廣州城市面貌的歷史變遷和發(fā)展歷程;上海市則在2005年的《上海市檔案事業(yè)發(fā)展“十一五”規(guī)劃》中,提出以檔案資源搶救、館藏檔案數(shù)字化、城市數(shù)字記憶、檔案開發(fā)服務(wù)等四個子項日,搶救性地收集有關(guān)上海城市發(fā)展的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各種形式的檔案資料,完整記錄上海城市發(fā)展的歷史軌跡,為構(gòu)筑和完善城市記憶、塑造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提供服務(wù)。
隨著“城市記憶工程”的不斷深入開展,“城市記憶工程”的目標(biāo)也從開始的主動記錄城市變遷,保存城市發(fā)展記憶,拓展到挖掘區(qū)域歷史底蘊,拓展檔案資源建設(shè),圍繞民生工作,提高服務(wù)能力等方面;“城市記憶工程”的內(nèi)容也從以城市歷史街區(qū)、遺跡和建筑原貌拍攝建檔為主,拓展到建立、搶救、征集、整合有關(guān)城市形成、建設(shè)、發(fā)展各方面的各種載體的檔案及其信息;“城市記憶工程”開展的方式也從傳統(tǒng)征集拓展到網(wǎng)絡(luò)征集,舉辦展覽、論壇、比賽等。如由青島市委宣傳部、市檔案局和青島人民廣播電臺主辦的“追尋城市的第一個腳印”活動,歷時一個月,57300多位市民通過青島電臺新聞頻道、青島傳媒網(wǎng)和青島廣播電視報參與推薦,后經(jīng)專家評定,最終投票選出60個“新青島記憶”。
3結(jié)語
通過對“城市記憶工程”實踐情況的具體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城市記憶工程”中檔案資源建設(shè)、開發(fā)利用方式的創(chuàng)新等,都對檔案部門和檔案工作者拓展工作思路、提高服務(wù)能力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工程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們更應(yīng)該看到它存在的問題。要突破工程發(fā)展存在的瓶頸,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對檔案記憶觀進行研究,用“檔案記憶觀”的理論來指導(dǎo)工程的深入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