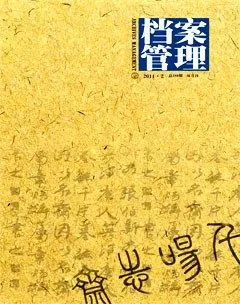論檔案記憶研究的學術坐標
2011-01-01 00:00:00丁華東
檔案管理 2011年2期

摘要:本文根據社會記憶的基本要素結構,重點對社會記憶研究的三種切入式傳統(主體一中介一客體)進行了剖解和闡釋,揭示出檔案記憶研究是以中介切入的方式來思考和探視社會記憶。這是檔案記憶研究在社會記憶理論研究框架中的立足點,是將檔案記憶放入社會記憶系統加以考察,既與社會記憶理論研究接軌,又能獨立展開的學術坐標。
關鍵詞:檔案記憶;社會記憶;學術坐標;記憶系統
一
檔案記憶研究是從社會記憶的理論立場出發,分析檔案在社會記憶傳承、建構和控制中的功能與機制,以推動檔案工作在社會記憶保護和建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構筑更加全面的社會記憶。其學術旨趣在于:一是充分認識和肯定檔案作為社會記憶的一種形態,理解檔案在國家和社會記憶中所具有的獨特地位和價值;二是充分認識和肯定檔案工作是社會記憶的保護與建構性工作,探尋在社會發展和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實現檔案專業的使命與價值;三是進行深度的理論發掘和理論創新,建構一個解釋性的理論框架,拓展檔案學理論體系,同時也為“世界記憶工程”、“城市記憶工程”、“數字記憶工程”等涉及檔案領域的記憶保存、保護活動尋求理論支撐。
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檔案界將“記憶”概念或觀念(筆者曾稱之為“檔案記憶觀”)引入學術研究和工作實踐以來,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視角和思考。不僅將我們所從事的傳統的檔案工作視為記憶保護性質的工作(如,數字記憶工程、城市記憶工程等),而且,還有意識地展開了檔案記憶方面的探討,如,《淺論照片檔案的歷史記憶與再現功能》(張彤)、《論檔案編纂與社會記憶的構建》(衛奕)、《檔案與社會記憶建構》(薛真真)、《權力因素在檔案構建社會記憶中的消極作用及其應對策略》(張林華等)、《基于社會記憶理論下的檔案與歷史的關系》(汪孔德)、《社會記憶視角下檔案記憶建構探析》(尹雪梅等)、《社會記憶與地方社會秩序一一以徽州歷史檔案為分析對象》(楊雪云等),以及筆者近幾年來發表的《社會記憶與檔案學研究的拓展》、《在社會記憶中思考檔案一一檔案學界之外有關檔案與社會記憶關系的學術考察》、《社會失憶、檔案與歷史再現》、《論檔案的社會記憶建構功能》、
《論檔案社會記憶建構功能的實現策略》等一些論文。這些論文運用社會記憶理論作為分析工具,吸收和借鑒社會學、人類學和歷史學等多學科的學術資源,力圖避開檔案文件觀、檔案信息觀、檔案知識觀等既有的研究路徑,在新的價值取向和意義范疇內展開對檔案、檔案工作的闡釋和分析,雖不敢說有多大的創新,但確實在以另一種方式看待檔案和檔案工作,以期獲得不同的解釋。
不過,從已有的成果來看,我們的研究視野尚嫌狹窄,受到社會記憶建構觀的過分影響,還只是在“檔案與社會記憶建構”這一主題下所開展的一些探討;另一方面,檔案作為一種社會記憶形態的觀念也未獲得充分的肯定和認同。所以,檔案界就存在一種互為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我們在高呼檔案是社會記憶、國家記憶的關鍵:“一個沒有檔案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國家,一個沒有智慧沒有身份的國家,一個患有記憶缺失癥的國家”;“沒有檔案的世界,是一個沒有記憶、沒有文化、沒有法律權利、沒有歷史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檔案只是社會記憶載體,是社會記憶建構的工具。“‘社會記憶’是社會情感、心理的重構,并不是記錄和史實本身,‘社會記憶不能和傳統的文獻記錄畫等號’”;“從嚴格的意義上講,盡管檔案與社會記憶的構建密不可分,但是‘檔案’不等于‘記憶’”。這樣一來,我們聲言檔案是一種珍貴的社會記憶,把檔案館視為記憶的殿堂、記憶庫,把電子文件稱為“擁有新記憶”,如此等等,都成了一種情感性的宣稱,檔案記憶觀失去了理論根基。
如何突破這種單純的載體論,如何超越檔案與社會記憶建構的單一主題,依筆者的淺見,我們需要在社會記憶的研究中尋求和把握檔案記憶研究的學術坐標,也就是檔案記憶研究是如何切入社會記憶的,我們在社會記憶理論研究框架中的立足點是什么,既找到與社會記憶理論研究的接口,又能獨立地、在新的方向上展開。總之,我們還是要把檔案放到社會記憶的系統中來進行思考,立得住,能接軌,有拓展。
二
為尋求檔案記憶研究的學術坐標,筆者在此借用武漢大學孫德忠博士對社會記憶基本要素結構的分析,來剖解檔案記憶研究在社會記憶理論研究框架中的位置。孫德忠在《社會記憶論》中指出:“從認識論角度看,一切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都包含著主體、客體和中介這三個基本要素。其中,主體和客體構成其骨架結構的兩極,工具手段等中介系統則是把主體和客體聯系起來的中介變量。社會記憶無論是被視為靜態的社會文化現象,還是被視為動態的社會認識活動,都具有這三個最基本的客觀要素結構。”循著這一結構,我們來反觀社會記憶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現有的研究成果在某種程度上與社會記憶的這一基本要素結構暗合。筆者將其稱為“三種切入方式的研究傳統”,具體來說:
(一) 基于主體切入式研究傳統。這種研究傳統是以特定人群為出發點或切入點,從群體主體的視野來分析特定的群體基于怎樣的現實需要、愿望和利益訴求等形塑社會記憶的。此傳統,源自社會記憶研究的開創者、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哈布瓦赫在《論集體記憶》等著作中,不僅承認集體記憶的重要性,而且,堅持有系統地關注其如何被社會所建構。他認為,集體記憶是一個社會建構概念,“過去是一種社會建構,這種社會建構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主要是由現在的關注所形塑的”,或者說,“過去是由社會機制存儲和解釋的”。他同時強調:“每一個集體記憶,都需要得到在時空被界定的群體的支持。” 他把這種被時空界定的群體稱為“記憶的社會框架”。“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從而我們的個體思想將自身置于這個框架內,并匯入到能夠進行回憶的記憶中去。”為此,他重點研究了家庭、宗教群體和社會階級傳統的集體記憶。
哈布瓦赫對集體記憶的“原創性”研究,不僅拉開了社會記憶研究的序幕,也形成了社會記憶研究的主導取向。這一取向,主要被社會學領域(也有部分社會史的學者)所遵循。在我國當前社會記憶研究中,如,王漢生、劉亞秋的《社會記憶及其建構——一項關于知青集體記憶的研究》、景軍的《神堂記憶》、方慧蓉的《“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劉朝暉的《社會記憶與認同建構:松坪歸僑社會地域認同的實證剖析》,以及應星的水庫移民記憶的研究,等等,都采用了這一切入傳統。在對“群體主體”的劃定上,既有特定時代背景下的人群(如知青、歸僑、土改時期的農民)、特定空間范圍內的人群(如村莊、社區、城市),也有正式或非正式組織的人群(如家庭、宗族、民族、宗教群體乃至國家),相關的探討都有所涉及。
正因為是從特定人群來分析群體對過去的回憶及其所具有的特點,因此,相關的研究常被稱為“集體記憶”的研究,雖然影響較大,但也遭到了一些批評。“集體記憶在中國的語境中,成為一種當代人共同經歷的過去的回憶,卻喪失了collective memory這個詞組在西方語言中具有超越當下的歷史感。中國的集體記憶研究逐漸淪為了‘當代群體記憶研究’,一個不甚準確的翻譯,讓我們自己束縛了自己的研究視野。”
(二) 基于客體切入式研究傳統。這種研究傳統是以特定的記憶對象為出發點或切入點,從客體的視野對記憶對象進行歷史考古和挖掘,分析不同時期、不同人群對特定記憶事實(如事件、活動、人物、觀念、規則、傳說、商幫、商號等)的理解和認知,以及所形成的對特定歷史事實的觀念。皮埃爾·讓內(Pierre Janet)在其《記憶的演變和時代觀》(1922年)中認為:“基本的記憶活動是‘復述行為’。其首要特征便是‘社會功能’,這是因為,該行為是與他人的一種信息交流,是在事件或客體缺位的情況下進行的,而這個事件或客體才是主題。”18]
客體切入式研究傳統起源于何時,我們暫難界定,但在西方的記憶研究中,能夠看到諸多的探討。如,社會學家施瓦茨對林肯形象的觀察,展示出林肯的形象在幾代美國人中所經歷的劇烈變化,由此得出,
“集體記憶既可以看做是對過去的一種累積性建構,也可以看做是對過去的一種穿插式的建構”lg]。此外,如,美國人關于越戰的記憶、歐洲人關于納粹大屠殺的記憶等研究,可以說是從記憶的對象介入對過去事件的重構之中。
正如帕特里夏·法拉、卡拉琳·帕特森所言,“人文科學的學者對記憶的結果感興趣”。在我國,我們不僅有“‘抗戰’記憶”、“‘南京大屠殺’記憶”、“‘九一八’記憶”、“‘七七盧溝橋事變’記憶”;還有關于岳飛記憶、曹操記憶、孟姜女記憶、徽商記憶,等等,這些記憶更多地被置于歷史學和文化學、民俗學的視野之下,在此情形下,記憶的主體被泛化,不再確指某一群體,而是有別于個體的“人們”或“大眾”,這種記憶常被稱為“歷史記憶”、“文化記憶”。或者,如,哈拉爾德·韋爾策所言的“一個大我群體的全體成員的社會經驗的總和”。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都可以被作為記憶研究的對象,而這些研究,我們并不格外注意是由哪個人群來持有的,也許,這正是客體切入式與主體切入式的不同。集體記憶不應只關注被當代人所共同經歷的過去,那些更遙遠的“過去”同樣,甚至更應該成為集體記憶研究的對象。比如,長城、孔子、龍等文化符號,甚至岳飛、關羽等歷史人物形象,我們今日對這些歷史形象和符號的敘述與建構,都是一種集體記憶的體現。
(三) 基于中介切入式研究傳統。這種研究傳統是以特定記憶媒介為出發點或切入點,從中介的視野來分析特定的媒介(紀念館、博物館、檔案館、圖書、圖片、照片、物品、建筑遺跡等)記錄了什么樣的過去,以及人們如何利用這些媒介來建構或傳承過去。此傳統雖非源自美國人類學家保羅·康納頓,但康納頓的研究肯定是最突出的。
在《社會如何記憶》一書中,康納頓分析了社會記憶是在儀式操演中保存和傳送的,“有關過去的形象和有關過去的回憶性知識,是在(或多或少是儀式的)操演中傳送和保持的”。儀式是社會記憶的承載體或中介,儀式活動的主體便是社會記憶的主體,儀式的內容便是社會記憶的客體,或記憶對象。康納頓所關注的是“尋求描述既在傳統中又作為傳統的一種非刻寫的實踐,如何得到傳輸”,以表明“社會結構中有一種慣性,沒有任何關于何謂社會結構的現行正統學說對它有確切解釋”。
現在的研究表明,社會記憶的承載形式不只是儀式,還有神話故事、口承歷史、文獻典籍及地面文物遺址,等等。康納頓也指出,“闡釋學已經把刻寫作為自己的優先對象”,“這種傳統的焦點在于:刻寫在文本或者至少被認為相當于文本,并且,可以說按照文本的類似形象構造的書面證據上的是什么”。只不過,他“把記憶問題的角度從歷史文獻轉換到了行為(儀式操演),事件記敘的時間性變得不重要,而事件內在的規則和象征性變得突出”。臺灣學者王明珂把社會記憶定義為“指所有在一個社會中借各種媒體保存、流傳的‘記憶’。如,圖書館中所有的收藏,一座山所蘊含的神話,一尊偉人塑像所保存與喚起的歷史記憶,以及民間口傳歌謠、故事與一般言談間的現在與過去”。
從中介切入社會記憶研究,在人類學、民俗學、文化學、圖書館學、博物館學,乃至影視、傳媒等方面都有涉及。如,英國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社會人類學教授杰克·古迪的《口頭傳統中的記憶》、英國小說家A,S,拜厄特的《記憶與小說的構成》[16];又如,我國學者的《關于“票證時代”的集體記憶》、《空間、儀式與社會記憶》,以及各種影評論述。在中國期刊網上搜索一下“社會記憶”或“集體記憶”,相關文獻隨處可見。
三
通過對社會記憶基本要素結構及其研究的切入式傳統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淺見:
其一,任何科學中的觀察都是“理論負載的”(theory laden),如,波普爾所說科學觀察都是置于特定的理論背景之下或曰“理論滲透”。更深一層說,科學觀察都更像海德格爾所說的“巡視”(Umsicht),而不僅僅是記錄所見之物。我們總是觀察我們所要觀察的東西,至少,是我們感到興趣或是引起我們注意的東西,而不能沒有任何傾向漫無目標地觀察。“當科學家進行觀察時,他們是有選擇地進行的,并且,他們的選擇受其理論的(有時是實踐的)興趣支配。”正是基于這種理論和興趣的不同,生成了不同的學科,也生成了不同的研究視野和解釋性框架,各學科都在自己的范圍內說著各自的話。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馬爾凱明確指出:“正是由于解釋框架的多樣性和變化發展,所以,意義在社會生活過程中‘制造并不斷再制造出來’,而且,過去的成果也會不斷得到重新解釋。” 這既是我們對上述分析的總結,也是為檔案記憶研究學術坐標的探討,提供了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根基和前提。
其二,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出,檔案記憶研究的學術坐標,即是從中介的角度切入社會記憶研究的,這就是檔案記憶研究在社會記憶理論研究框架中的立足點。社會學可以從主體的角度展開研究,歷史學、文化學可以從客體的角度展開研究,那么,檔案學就一定可以從中介的角度展開研究。這種研究不是檔案學的專利,而是“媒體研究”的共同點。正如坎斯特納所言:“有助于建構和傳達我們對過去的知識和感覺的記憶媒介,依賴于雜亂無章的、視覺的和空間的因素多樣的結合。因此,集體記憶是由多種媒體拼貼而成的大雜燴,它是由‘圖示的圖像和場景、標語、妙語和詩句片段、抽象的藝術品、圖表模式和話語的延伸,甚至是偽語言的混合’(Ferntress,wickham:《社會記憶》,第47頁)的一部分構成。它們還包括身份、記憶場景和建筑物。既然我們不能全面重新建構這些易變的事物,我們就不得不一次集中于一兩個層面。這些努力已經創造出集體記憶研究中的獨特分支。”
在近年國外的相關研究中,以中介切入式方式來考察社會記憶,似有漸增趨勢。在上海大學圖書館“2010年外文新書選書目錄(第二期)”中,筆者就看到多部關于這方面的專著或叢書,如,《文物動力學:歷史、記憶與高地間隙(叢書)》、《世紀的基奇納伯爵與黑格伯爵:記憶、文物與歷史的構建》、《中世紀英國記憶與紀念/會議錄(叢書)》、《米斯特克圖解手稿:古墨西哥時代、工具與記憶(叢書)》、《記憶與重復:(失樂園)中的圣經創世紀》、《東歐當代攝影:歷史記憶認同(叢書)》等,體現出研究者的一種分析視角。只是這些專著和叢書尚未翻譯,目前,要消化和吸收還存在困難,有待進一步關注。
其三,我們說基于切入方式的三種傳統,不是說對社會記憶進行三種孤立的研究,無論哪一種切入方式,都必須把社會記憶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具體來說,主體切入式以特定的群體為出發點,考察群體的記憶,但也必須考察記憶的內容或主題,要運用多種記憶中介來重塑這個群體的記憶;同樣,客體切入式以特定的記憶對象為出發點,考察對歷史事實的認知和理解,也必然要涉及記憶的主體,并以中介為依托,考察各種主體(不同時代或不同特征)對記憶事實的認知;中介切入式以特定的中介為對象,考察在記憶的中介中所承載的內容或記憶事實(客體)以及不同利用者或解讀者(主體)對這些內容或記憶事實的理解。只有在社會記憶的整體結構中來開展社會記憶研究,各種切入方式才有可能。
其四,“在社會記憶的主客體結構中,中介則除了是必不可少的過渡手段外,在對人類主體能力和本質力量的儲存和復活上,它與特定的主體和客體具有同樣的、更加顯著的效果,即,它是社會記憶的最直接、最典型的形式。”對于檔案作為社會記憶,我們還可有更多的闡釋,如,從檔案原初的“備忘”功能、從有文字與無文字社會的記憶方式,甚至我們還可發掘一些人類學的資料,來證明檔案就是社會記憶。社會學、人類學的一些學者往往關注口述記憶、儀式記憶,似乎這些才是鮮活的記憶,而檔案是“死的”,這種認識已經影響到檔案學研究中,對此,我們需要批判性認知。口述的、儀式的、文物的、文獻的敘述、表現、記錄都是社會記憶的體現,有的學者用“筆語”記憶來對應“口語”記憶;或用“刻寫記憶”來對應“非刻寫記憶”,如此等等,都明確肯定了檔案記錄的記憶性質。由此我們可以說,檔案是既在社會記憶之中,又作為社會記憶的一種形態而存在,有此認識,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檔案既參與社會記憶建構,同時,其自身就是社會記憶建構的結果;才能更深刻理解檔案工作自身是一項社會記憶的構筑性工作。
從社會記憶的理論立場來思考檔案,不是要顛覆、瓦解傳統的檔案學理論,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對傳統檔案學的反思和拓展,是在原有的基礎上的深化。這不僅關涉社會記憶研究的基本命題一一記憶建構,還關涉社會記憶的傳承、控制與保護。筆者曾預言檔案記憶研究是檔案學一種新的理論范式,能否形成新范式,需要大家共同參與。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IOBTQ040)和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項目“檔案與社會記憶建構研究”(09YS64)研究成果之一。
<img src="https://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agl/dagl201102/dagl20110204-1-l.jpg?auth_key=1736828683-1711244522-0-f783b221fdb469528086973487503ec7" hspace="15" vspace="5" 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