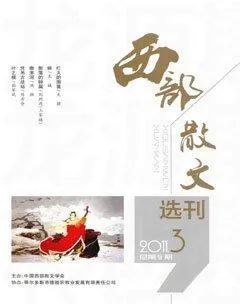獻曼達
問:你誦的是什么經?
答:地上開滿了花,
有藏香的香氣傳來,
頭頂上有四座山,
山上有牦牛和羚羊,
天空中有太陽和月亮,
所有這些,全都獻給你——
藏族大叔是在大昭寺門口遇到的。只是,他一直沉醉著,連抬頭看我們的工夫都沒有。他穿著米白色上衣,深棕色褲子,倚墻而坐,黃色的掛脖圍裙把他明晃晃地從一排誦經者和發呆者中拎了出來。他左手拿著銅色盤,右手從圍裙里抓起一把又一把的東西往銅色盤上擦過去,是青稞和五色石珠子。那青稞和五色石珠子掉落下來便有熱鬧的聲響,那熱鬧卻是低調的,平和的,襯著他口中裊裊縈縈的誦唱聲。
這是八月,拉薩像一片金色的海洋,氧氣稀薄,陽光濃厚。人在其中行走似乎是有浮力的,不是行路,是游弋,像魚或者像鬼,反正不大像人。干脆在藏族大叔身邊擠了一個位子坐下,掏出剛才在八廓街買下的小小轉經筒,轉了起來……
傳說中西藏的天空就在頭頂藍著,大昭寺的金頂就在眼前燦爛著,虔誠的朝拜者就在腳邊匍匐著……而我的心,為什么這么不安穩?自從進入西藏,便有一只神秘之眼,一直在跟著我。我抬頭遠眺的時候,那只眼在寬檐帽的邊沿上;我攤開手掌的時候,那只眼在我的手心里;我在八廓街轉悠的時候,那只眼便在琳瑯的藏飾中,在回首之際的轉彎處,在藏式碉房遠遠的帳帷里……它無處不在。
木輪架轉動起來,我且把自己的心靈清空了,讓經文帶著這具軀殼一起去超越吧。
我是一個來自潮汕平原的女子,從地圖上看,我的家在祖國最東南的地方。與拉薩相距將近4000公里,海拔相差3000多米。我們家鄉,用的是漢字,潮汕話通行。潮汕人喜歡吃海鮮和山貨,但烹煮的菜式一概都是清淡的。在那里,風是和煦的,雨也是有預見的。每年夏天,也有幾次臺風從大洋上飛旋過來,興風作浪儆示一下,很快也便與人達成和解。人對天的感覺松懈了,對神對佛的感覺也松懈了。母親她們那一輩人還有祭拜習慣,逢年過節鐵定供奉的是祖先神,平常還有各種各樣的非權威小神,我年輕時候,曾經相當不敬地調侃過。
拉薩的天真藍,藍得暴烈,藍得純粹,藍得縱逸凌厲。每次抬頭望去,它都直直地逼著我。我突然對溫吞的漢家生活產生了陌生感。哪里才是我靈魂的棲所?哪里才是我的生活?哪里才是我的愛?我不知道哪一種更接近我的意愿,哪一種更接近我的思維。
大昭寺內,因有釋迦牟尼12歲的等身像坐鎮,朝拜者云集。且對焦到一個信徒身上,只見她雙手合掌舉過頭頂,下跪,磕頭,然后五體投地……口中的咒語是聽不見的,只看到了她唇線的嚅動。而她的瞳仁兒呀,我站在與她近得可以用眼神交流的距離,可她根本就是無視,那兩汪略顯干澀混濁的湖泊,只是空冥一片。她正是我母親一般的年紀,頭發有些斑駁,發絲有些散亂,額上長磕出來的繭印有點厚有點暗。不知道為什么,她的朝拜暫時停了下來。她摸索著在身后的小卡墊旁尋到了自己的風衣,那件風衣卻是男式的,塵土差點兒遮蓋住了它的藏藍底色。她摸呀摸又摸了一陣,有什么東西四下拋撒出來,原來是風衣里裹著的五六顆糖果……看看找不到想要的東西,她停手了,索性坐著了。
她是長途朝拜者嗎?從千里之外而來,匍匐于砂礫之上,顛沛于冰雪之間,餐風宿露,輾轉經年。或者,她就是本地的藏民,每天像上班一樣來這里朝拜,在相同的地方,做著相同的動作?身邊的藏族大叔說,一個愿,或許就是磕頭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次。有的人,已經在這里整整磕了四年。
撲哧——神秘之眼對著我狠狠眨了一下。
那是一個什么愿,需要人以一種自虐式的信仰來回報?上天對離他最近的那個孩子,是不是必須賦予更多的磨練?
嶙嶙雪山,漫漫風雨,冰雹當頭,道路翻漿,泥石流隨時傾瀉而下……這是獵奇的我們想象得到的嗎?沒有耕種可以牛羊為主食,沒有咖啡可以喝青稞酒,可是醫院、學校、電話呢?女人潔凈柔軟的衛生巾呢?哪怕只是一條道路,門前的一條可以行走的通向遠方的路……
我們眼里的晴天麗日、藍天白云,在他們眼里,或許轉瞬之間,就是幽暗地獄、猙獰妖魔。當人類單薄地面對大自然,千萬年千萬年,恐懼也就如影隨形。為了掙脫恐懼,我猜,他們擠兌過、彈壓過,只是,在這個過程中,恐懼更加迅猛更加強大地反撲過來。再沒有一個詞像恐懼這樣在高原的山峰和草甸上扎根得如此之深了。萬能的信仰呀,你快來吧。
這就難怪了。在藏傳佛教中地位極高的蓮花生大士,可謂智悲雙運,威德普聞。可是,我見到的他面相蕭殺,劍眉怒張,手中的法器上竟然串著三個骷髏頭。在當代的懸疑驚悚小說中,他成為了一個斬妖除魔的英雄,我的一個“時尚達人”的朋友即是他的粉絲。這一次在布達拉宮,幾年前在香格里拉的松贊林寺,我瞻仰過眾多神佛的雕塑和壁畫,面相也大多威武而猙獰,而我們的漢傳佛教,我們的佛祖氣質,那是慈眉善眼、雍容儒雅的呀。
那只神秘之眼一直在天上,只有它能夠照見一切真相,和我們荒蕪膚淺的內心。在八廓街那間叫做瑪吉阿米的黃房子坐上一個小時,浮草地念一段倉央嘉措的情詩,在留言簿上抒發一下個人感慨,如果僅僅如此,雖然身在西藏,但其實離西藏還是老遠。
很想與身邊的藏族大叔好好聊聊,只是他說的是藏語,連比帶劃還是不知所云。是旁邊的一位藏族小伙子充當了我們的翻譯。問大叔:“你誦的是什么經?”他說道:“地上開滿了花,有藏香的香氣傳來,頭頂上有四座山,山上有牦牛和羚羊,天空中有太陽和月亮,所有這些,全都獻給你——”大叔手上的功課并沒有停,青稞和五色石珠子一次又一次淅淅瀝瀝地掉了下來。
這段經文,令人心喜,令人澄明。
后來,一位遠在美國的朋友在我的博客看到了這段文字。她告訴我,大叔是在做獻曼達,他手中的那個銅色盤即是曼達盤。這位朋友走過一段曲折的心路,后來她受到了藏傳仁波切的指引。
藏傳典籍《樓閣經》中說:“只要你以清凈圓滿建造一個宇宙曼達,你就能主宰實際的宇宙。”
我相信,大叔是一個有福之人。我的這位朋友也是。
選自《文藝報》2011年3月23日
原報責編 劉彥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