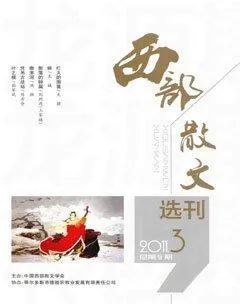海上夜
從未坐過海船,尤其夜航。
六點上船,七點,朋友所托的船上的人叫吃晚飯。飯簡單,主食兩樣,米飯、粥,一種不大的魚,問叫什么魚,回答的人說,叫什么什么,和岸上不一樣,這句話黏住了我,我竟沒有記住。海上的人,有點不屑于跟岸上的人同一種叫法,更民間和自然,所謂的俗名吧?習慣了某種叫法,一下官話,叫他們無所適從。雖然在所謂的公家的船上做了很多年,他們還是習慣先前的叫法。某些少數民族部落,連劃船的槳,上面刻制的花紋,都是永久不變。他們認為變了,就會打不到魚。我也是一樣,在土豆和洋芋之間,有時會不知道究竟叫什么的好,而它的學名馬鈴薯,幾乎忘了。
桌上,那種魚,燉和油炸的各上了一盤子。還有一大碗牡蠣?好像是,只是不大。貝殼上還染著綠苔,長在上面一樣。另有豬肉炒了一種青菜,還有一種,都不認識。這一桌,船長、輪機長、大副、服務部主任、乘警、大廚,都近乎沉默吃著。因這沉默,不好多問什么。
我在船長一邊。船長看我一眼,說,喝一點。我說,好。有人在紙杯子里倒了一些,嘗了一口,知道是二三十度的米酒。那人問,喝不慣吧?我說,沒問題。前一天在潿洲島上已經喝過這種酒了。去年,在廣州也喝過佛山產的這樣的酒。想起開船前那位朋友的話,北方人過來,喝不慣這種低度的酒,可是時間長了,都會習慣。這兒的水土,青菜和水產,也真是得喝這種酒。烈酒,下這清淡的青菜和魚蝦,有時候不著鹽和醬油,倒是奇怪的。
獨自喝,也跟桌上的人,碰一下杯子,又忽然想起來,在船上,工作時間,可以喝酒嗎?可是看到幾個人都坦然,覺得許是可以的吧。也許,就是這樣的習慣吧。這些人,父輩幾乎都是水上人,喝酒習以為常,無飯不酒。水上生活,生死一線間,生命是可以有一點適度的揮霍吧。
船長在一邊,悄悄觀察一下。大約五十歲,英俊健碩,微紅的臉膛,海上的陽光的緣故,卻是少見的光潤,幾乎見不到皺紋。船長吃魚,是搛起一條魚,放在碗里,再搛起來,先從魚尾吃起,再吃身子,幾乎就是牙齒一過,就把魚身上的肉帶了下來,沒任何停頓。他搛萊吃的時候,在一只他專用的清水碗里涮一下多余的油。
魚吃的很快,一會兒就又上來一盤,還是那種魚。看著他們吃魚,覺得,也許只有他們才真正有資格吃魚吧。天經地義。
船長幾乎不說話,幾個人話都不多,只是極其嫻熟地吃魚,喝酒。我對面那個大副一直在地用牙簽挑牡蠣吃。不看他的時候,聽見牡蠣殼一粒一粒,喀拉喀拉,落在桌面上的聲音。
船上的人,海上久了,性格兼具溫情和暴躁,極特別。這邊的朋友說,他才上船的時候,浪大,顛簸的七天粒米不進,不停地吐。老船長坐在他床邊,把一瓣一瓣的橘子捏出汁水來喂他。一個粗壯男人,如此溫情。而同樣是這個人,會忽然之間,對操作有誤的船員破口大罵,話極臟。可是下了船,就忘了,似乎另外一個人,跟沒發生過這樣事一樣。
船長接著吃魚,一些米飯青菜,給自己又倒了一些酒,大約喝到三兩多的時候,不喝了。
船長出去的時候,其他幾個人也都放下了筷子。陪著我的服務部主任,盛了半碗粥,慢慢陪著我。
幾個人都走的時候,還有半瓶酒,扔在那 里,不要了。這是奇怪的事情。去潿洲島的時候,也是這樣,陪我的那個人,下船的時候,也是把剛買的面包和水果,扔在桌上不要了。為什么呢?海上生活的人,就是這樣的嗎?
接我上船的主任,把房門鑰匙給我,交待有什么事給他打電話,也告訴我洗澡的地方,我裝著知道了那樣點頭,其實心里一片糊涂。并說若第二天早上船到了,見不到他,就把鑰匙擱在某處就行了。
船已經走遠了,很快手機信號中斷。這還是沿海的航行,若是遠洋呢?人真是隔絕的。幾個月下來會是什么樣呢?在京城讀書時候,某次一天沒有出門,寫倦了就在床上躺一會兒,到傍晚,有人敲門進來,我茫然著臉去開門,那人驚訝地看著我,問我怎么了?怎么了?沒有怎么呀?看你的臉?我的臉什么樣?我不知道,來人一定從我臉上看見了什么平素沒有看見的什么。可那是什么呢?
四顧茫茫,雖然沒有出去,但是知道四顧茫茫。夜幕慢慢降臨。想出去看看降臨的夜幕,還是沒有出去,只是透過舷窗,看看外面。若那個人在,會拉著她上前甲板看看吧。也許,就一直看到了深夜,看到了時間深處,忽然想起這句話。
翻幾頁書,喝茶,吃一小塊面包,夜就深了。也在筆記本上胡亂寫了幾行什么。
不能就這么睡了吧。還是出去。通往前甲板的通道沒有找到,船上迷宮一樣,只是找到了去后甲板的通道。這時候正好,沒有幾個人。可是后甲板上極亂,從甲板下面傳上來的機器的轟鳴聲,略略嗆人的柴油味兒,油污味兒。甲板上還有好多不清楚用做什么的設備,也滿是油污,個別處才露出原先刷的油漆。從這樣的夾縫里穿過,在船尾站了一會。夜幕已經很深,距岸很遠了,什么也看不見。看不見,也就不看了吧。也還有人站在甲板上看著,看那些看不見的。也許,人可以說是一種會向遠方遙望的動物。別的動物呢?據說,科學家偶然看見一只大猩猩,在向遠方遙望。可那是真的嗎?它在望些什么呢?
這是一艘三千噸的船。不大不小。白天上潿洲島的時候,是小船,有人帶著在駕駛室里待了一會。船小的緣故,站不穩,每次挪動都得抓住什么。一起去的人,是海員,挪動的時候,隨著船的晃動,步子似乎趔趄著,卻準確地挪動到另一處。
靜下來,才覺得,這真是一個人的旅行。真的。海上手機沒有信號,即便偶然有,剛要撥,瞬息間,又沒了。手機也快沒有電了。尤其充電器又丟在另一處。覺得很快將與世隔絕。忽然想起茨威格小說里,一位后來成為國際象棋大師的人,二戰時期,作為囚犯被納粹審訊的時候,偶然從審訊室里偷得一本棋譜。一個人單獨關在囚室里,孤獨,只能研讀棋譜。若是很久時間,我一個人在這船艙里,會認真研究些什么?會一直寫作嗎?不知道。也許,會有一種純然冥想的文學吧。藏傳佛教的“閉關”,近乎“囚禁”,經過“閉關”的僧人,心性會有特殊的“精進”。我能若干個月不出門嗎?不能。比起很多,文學畢竟是輕浮的。所謂文學,也不過是心性的一些痕跡,一些“紋”罷了,凡有痕跡之物,都不能超然的。
再一次想起日本古代的芭蕉。芭蕉不懼死亡,卻在離開時將他的草庵轉讓他人,寫下“寂寞草庵易新主,桃花三月列偶人”,并“將此句書于紙,掛在草庵的門柱上”。“征途三千里,渺渺在一心。人生如夢,感慨萬端,前程未卜,灑淚作別”,雖然已經上路,卻“然而依舊去意徘徊,且行且止”,大沒有劉伶酒醉后讓僮仆跟著,死便埋我那樣的灑脫。
這一夜航,不在計劃,只是忽然決定,算是所謂逆旅吧。一切未知。若和某個人,一起在船上,去哪兒都是好的。若真在的話,會在船舷邊站立很久吧。直到有夜涼的霜降了下來。七月的夜晚,站久了,心里也是會有霜的涼的。
船在行走,很穩,只隱隱覺得“忽悠”一下,又沉靜下來,很闊大的那種“忽悠”。
遠處,微微有幾星燈光,按照航海的常識,燈光的位置,大約在五公里左右。想想也是奇怪的,人在晚上,竟然能感覺了那么遠的。那么遠的人,能感覺到張望的人嗎?
原想,夜更深些的時候,起來,一個人起來,在甲板上走走。可是,再次醒來的時候,天已經蒙蒙亮了。也已經有人起來,在甲板上站著了。
已經可以遠遠看見岸了。忽然覺得悵然,夜航結束,要登岸了,而那個岸上,并未有一個可以相知的人。
知道船靠岸的時候,會鳴汽笛。這船的汽笛鳴了嗎?竟然沒有注意到。船上人們已經有些亂了,匆忙等著下船了。
咯啦啦,咯啦啦,聲音澀澀的,金屬摩擦的聲音,粗礪,沉悶,重滯,知道是下錨了。碗口粗的鐵鏈,膩著黑色的油,隨著一個巨大絞盤的轉動,緩緩沉下去。
收拾好行李,把鑰匙放在約好的那個地方,下船去。
走遠了,回頭看一眼那船。
再遠,疑問自己,真的是在船上,在海上,走了一夜嗎?竟然覺得有點不真實。雖然知道那是真的。
人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啊。
選自《隴東文學》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