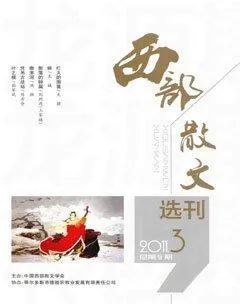屯子里的風與樹(節選)
風會吸干一棵樹
風刮進屯子,一些風就悄悄地留了下來,它躲開了人的視線,在屯子里偷偷地做了一件壞事。風把屯西邊劉老大家的一棵柳樹吸干了,柳樹只把干枯的手伸向了藍色的天空。
風會吸干一棵樹,屯人都沒在意。這不像一樹蟲子吃光了樹葉,一棵樹無奈地死去,人會記住樹上的蟲子,讓一棵樹斷送了生路;也不像一陣狂風,吹斷了樹干,一棵樹無法維持生計,在掙扎中死去,人會怪那陣大風,讓一棵樹沒了退路;更不像一個拿斧頭或鋸子的人,偷偷結束了一棵樹的生命,另一些人會怪那個偷樹的人不厚道,讓屯子無故少了一棵樹。風躲在暗處慢慢吸干一棵樹,人無法察覺。風在一個屯子里廝混得久了,肯定會做一些事兒。屯子里沒有誰可以不做任何事情的終結一生,即便最卑微的草也會努力完成生長的壯舉。
風的一生都在奔跑的嬉戲中。風在奔跑的嬉戲中完成了一場風一生中所有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一場風跟在一個人的后面,還是一場風奔跑在了一個人的前面,風一定比一個屯人更了解一片土地,它換著腔調唱著歌在一個屯子里。一個嬰兒的啼哭,一片莊稼的成熟,一條蟲子的鳴叫,一條河流的奔跑,一朵花開,一聲嘆息……風悄無聲息或雷鳴電閃地趕到。風肯定看見了一棵樹在漫長歲月里生長的足跡,它想留住一棵樹的腳步。人總喜歡留住一些事情,比如感情,比如歲月。只是人很少能留住自己想要的東西,更多的人把自己留在了歲月的嘆息里。風或許看中了一棵樹的某個美麗瞬間,它也想留住一些美好的記憶。風看慣了樹下乘涼那個孩子吮吸母親乳汁的動作,風也想找回母愛,它像一個孩子吮吸母親膨脹的乳房一樣,吮吸一棵樹的美麗時光,風壓根不知道,它會吸干一棵樹鮮活的生命。風毫無知情的做了一件壞事。
柳樹是在一年的春天沒能抽出綠葉的。柳樹的主人劉老大在上地送糞時,用腳踹踹粗壯的柳樹,樹發出“嘭嘭”的幾聲空響,那聲音肯定沒有一棵活著的樹瓷實。樹的身體里面肯定缺少了啥東西。劉老大用懶散的目光細細端詳著柳樹:這樹真是的,到現在還沒冒出一片綠葉,再過幾天,地里的苗恐怕都該出齊了,今年這柳樹咋比我還懶啊。柳樹在劉老大懷疑的目光中,實實在在的失去了生命的光澤。柳樹不知道哪一根神經出了毛病,身體里一下沒有了水分,失去水的柳樹是大自然放在大地上的一株木乃伊。我去屯西時,路過柳樹旁,用鐮刀敲敲柳樹,柳樹沒有活著的樹聲音沉實。風是不是把柳樹的什么東西也吸掉了,我是用心聽出這聲音的。不像啄木鳥在樹干上敲,上年紀的人一聽就知道,梆梆聲的樹干沒事,咣咣聲的樹干空了,大半是枯枝、枯干。啄木鳥肯定也敲劉老大家的柳樹了,柳樹在劉老大家院外,離路近,路上走的人多,雜音重,劉老大留心走路人的腳步,忽略了柳樹被敲出啥聲了。柳樹被風吸干了,他也不知道,還蒙在鼓里。劉老大忽略了一棵樹,更確切的是忽略了風。
風會吸干一棵樹,尤其吸干劉老大家的一棵柳樹,劉老大也沒啥好辦法。風比劉老大更早的來到了屯子,盡管劉老大在屯子里生活了幾十年,像個老人兒,他揮揮鐮刀就決定了一株草的命運,動動鐵鍬就改變了一塊土地的將來,可劉老大改變不了一場風。風說在就在了,它一直住在屯子里,我們不清楚,風才是屯子的另一位主人。或許,風吸干了一棵樹,就像我們用掉了一株苞米,一碗米飯,誰說風輕輕拉動我們的衣襟,猛然搖晃我們的身體,不是在動我們的主意,只是現在它還沒得手,它用了數千年,也許是數萬年才摸清了一棵樹的來路,它準備再用若干年摸清人的來路。
在風的世界里,我們會不會是另一種世界。風會吸干一棵樹,當風接近我們,我們聽到了風聲。當我們接近一場風時,風聽見了什么!
樹的距離
屯子的樹和樹之間是有距離的。樹和樹之間也不想靠得太近,他們不想實實在在地擋住一場風,那一定需要許多的力氣,樹在擋風這事上一直想偷一把懶,省一份心機。
屯子里的樹一直都稀稀拉拉的不密實。像堂叔的頭發,稀稀疏疏的,蓋不嚴頭頂。堂嬸就數落堂叔,看你那幾根毛,比屯子里的樹也密實不到哪兒,你那要是莊稼,可省著間苗了啊。堂叔摩挲摩挲頭發,然后堂叔堂嬸都樂。屯子里的樹不樂,樹們沒聽見,也許聽見了,不愛吱聲兒。樹和樹之間長得太密了,大概不會是件好事。父親帶我鋤地時,我時常貪多地留雙棵苗,我一直認為這樣可以在秋天里多收入一穗苞米或一穗高粱,可父親還是上去一鋤,幫我砍掉了多余的一棵。父親沒讓我留。這莊稼和屯子里的樹一樣,距離太近,伸不開筋骨,互相欺身,啥也長不好,父親一直這樣告誡我。我只能聽父親的,他是個好莊稼把式,懂得多。他肯定也不想少收入一穗苞米或一穗高粱,他活了那么大的一把年紀,或許早些年曾懷著和我一樣的想法。后來父親想明白了,也許是之前爺爺也這樣告誡過他了。我們身上的很多經驗都是老輩人言傳身教得來的,那些經驗也許是我們的祖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我們一輩兒一輩兒的繼承。
我回到家時,院里院外地找過,每一棵樹與另一棵樹之間,都有很大的距離,這是我經過認真考察,證實的。可院外的杏樹不聽這,兩棵樹長在了一起,像一個人的手掌上突然伸出了兩根手指頭。在沒發現杏樹的秘密之前,我一度認為兩棵杏樹是一個根,它們同時長出地面,才被迫分道揚鑣的成了兩棵樹。它們生長了好幾年之后,樹上的杏暴露了杏樹的秘密。原來,一棵杏樹的杏大,一棵樹的杏小,結的杏也一棵甜,一棵酸。我又仔細看了看根,才了解了這個秘密。兩棵杏樹緊挨著一起生長了二十多年,連碗口粗都沒超過,每年結的杏兩個人吃一頓都不夠,讓人看著著急。父親前兩年砍掉了其中的一棵。現在,還沒過兩年,剩下的那棵杏樹突然放開了手腳,明顯長大,結的杏也明顯多了。
在很多年月里,房后的一棵棗樹長著長著,把枝杈伸展到房上。房山子的一棵梨樹也順利超過房頂,把枝杈從另一側伸向房頂。我在登上房頂之后,可以毫不費力氣地摘到棗和梨,這是我童年和樹最近的距離。我肯定爬不上高大的棗樹和梨樹,我不擅長爬樹,樹自己把自己拉近了和我的距離。我對樹默不作聲,卻滿心歡喜。樹或許想明白了,它在獨自生長的歲月里看懂了一個孩子的簡單渴望。
樹在確立距離時,一定不會是逃避一場風的責任,草長得再高,也不會在一場風到來之時,發出一棵樹的呼喊。我站在風中,發出再大的喊聲,也擋不住一場風的行程。樹故意留下些距離,慢慢削弱一場風,樹不想激怒一場風的暴力。樹比我們這些屯人更能駕馭一場場風,南風、北風,也許是東風、西風。這是樹和風之間的事,我看了許多年,也讀不懂它們之間的默契。我在屯子里生活了許多年,認為足夠了解一個屯子了,可我沒能更多的拉近一棵樹的距離。
多年前,我順手把一頭驢拴在一棵榆樹上,榆樹不粗,我把它當木樁用了。可那頭驢沒有嘴上留德,它把榆樹足足啃了一圈皮,讓一棵榆樹露出鮮嫩的木質,在數個月后,孤獨的死去。我忘記了一頭驢的辨別能力,它大概把一棵樹當成了一棵草,它習慣了啃食青草、樹葉。它抬頭看看樹葉在自己頭頂,仰再高的頭也夠不著,它想先把這棵大草從下面咬斷,那它就能吃到樹葉了。我毫無防備地拉近了一頭驢和樹的距離,讓一棵榆樹無辜地死去。以至于在若干年后,看到和它同齡的另幾棵樹長成了好檁木,我都懊悔不已。
我確信我不懂一棵樹。我在屯子里認識了楊樹、柳樹、梨樹……只要在屯子里生長的,我現在都認識了,無論大樹、小樹,就像屯人,我認識他們,和他們打招呼,辦事情,可我們保持一個微妙的距離。樹會這樣嗎?誰知道,樹在一場風中,嘩啦嘩啦地幾聲里,不是在和我們說事情,打招呼,可我們沒把那當回事,這讓我們沒能進入另一些事物的內心,拉近一些距離。
或許,一棵樹壓根不愿接近我們。它知道,你背著的雙手里緊握著一把斧頭,它害怕這。樹在這上,不虛頭,不像人。樹的內心和人想的會一樣嗎?
選自《海燕》2010年11期
原刊責編 張明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