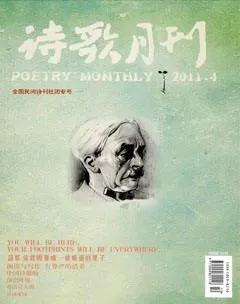孫磊(2首)
存在之難
那是不容分說的勇敢,
愚蠢的僻靜,是一張紙
迎向它的供詞。迎著
筆的尖刻。
和呼吸中上漲的河。
始終有一個力在暗處。
霧不重。它就要求更多的迷惘。
它需要沿岸。需要罪。
需要更多的生活,從具體的出發點,
釋放出喋血斑斕的另一面。
在望京。時光被鎖在
眾人的肺里。顯然它有更多哮喘的燈,
很多卡槽。而且
在于迷途長久的對立中
它有額外痙攣。
生活就是從這里
釋放出鎂。它看上去多像
一個單數世界的閃耀。
孤立也近似一種權力,
猛烈。曖昧。瘋。
就素食而言。
我所在的崩潰,
還不能克服瞬間的傍晚。
我所努力勸阻的消費
仍是固執的、薄霧的、反芻的。
今天。我決定去散步。
它常常提供壁壘、縫隙、隱身衣……
它讓我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
“高聲寫作”。雖然
我只同意其中的減法。
在的。無名的在。
求的。無所求的欲念。
一直用推論將我推向一面鏡子,
推向它的深處,
更激進,
并帶著更多的拒絕。
在簽證處
一座橋。允許它出逃。
允許它與雪和睦一致地落進護城河。
允許它沉默
沉默在水上就是沉默在異國。
就是離開冬天像離開謊言。
在滴水的單身女人身上
消費的力和冰持續了一整年。
而謊言是昨天剩給我們的那條街道。
和一張失真的單曲碟片。
突然有一陣低迷。在簽證上。
有一陣國家的蒸汽。黑到惱火。軟弱到安全。
大使館像冰柜。
它呼喚密閉的容器、噩耗和迷途。
它在被宣布的禁止外有一種團結。
比我們說得更多。比突然孤單的表。
思想也混淆了被說出的黃昏。
風掃向垃圾堆,
并推開一扇朝向落日的窗。
橋是有視野的,而視野會要求一種毀壞。
一種厭倦,成為陰郁的浪。
潮起于天邊。
暮落在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