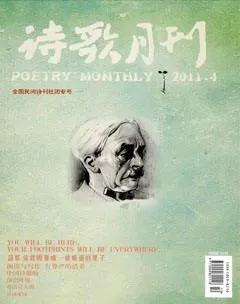胡桑(2首)
從書隱樓到梓園
在天燈弄,可以看見黑暗。被賦予的
形狀鎖閉著,大門面對迷失自己的人。
這些建筑,偶爾會被臭氧驚醒,
以另一種聲音呼吸,一邊堆積,
一邊喪失,猶如體內傾斜的痛苦。
這是一段空曠的距離,無人執守。
在南市區,“沒有一個位置是純粹的。”
秋天已被推遲,無人洞悉磚石的季節。
書籍,借用虛無的形式,在眺望人群。
我那么陌生,猶如一個錯別字。
城市的腹部,超功利的建筑,
猶如暗疾,束縛在自身的命運里。
我無法進入它們銹蝕的后院,
也許,一棵梓樹的鬼魂正在游蕩,
于光陰的裂隙中,糾正鋼鐵的恐高癥。
被翻刻的往事,在風雨中變成
一個災難。我聽見建筑失敗的聲音。
從此以后,聚斂與逃亡的技術
一蹶不振。所有權在融化。
偽造的名譽幾經易手,接近透明。
在放棄謀反之際,事物抵達了本質,
那虛無的緯度。我一無所獲,除了幻象。
一條敏感的弄堂在變形,如烈日下的豆莢。
門口榖樹的果實,沒有任何鋒芒,
祖先的江山,獲得了異常的寧靜。
拂曉登昆山玉峰
十月像一張票根,被用舊,逃離國家。
旅游尚未醒來,亭林路上,
我用一個句子攔住市場經濟,
讓孤獨的女人安全地走入出租車,
家庭暫存在公寓里,難以被糾正的
少女歲月,已經與拆遷房一起失蹤。
早晨的公園,清潔工用自來水擦去
欄桿上的夜晚,白天在傳授種植空白的秘訣。
老人們以閑聊注滿一個新日子的腹部,
茶和+94iQytHXjsJSEsy4yqQug==戲曲構成了時間的主要成分。
人們誠實猶如工資,在未來一般含混的清晨,
彎腰,勞動,區別于僵硬的植物。
半山腰,一位晨練的婦女,潮水一樣
抖動腰身,她的動作增加了山里的寧靜。
突然的一聲鳥鳴,收攏了中年男人恍惚的目光,
灰色上衣倒映出我的外地人身份,
他用熟練的伸展動作,鞏固與這座城市的
合約關系。我就像一個比喻,
來到這些仿古建筑邊,搜查它們的喻體。
張大復或者歸有光的手杖,逐漸融化,
像一場遙遠的雪。遺忘猶如被潑掉的茶葉。
這樣的清晨,我看見自己的童年,
它像山下的城市一樣鋪展在大地上。
街道那么靜,似乎工業是十八世紀的流感。
“生活,就像反扣的玻璃杯,波瀾不驚”。
人群稀疏,我庸俗而平靜,猶如山上
失去刻度的腳印。從東麓走到并蒂蓮池,
老人們談論著光陰的叛亂者,
他們流亡的語言洗濯了林蔭道上殘余的顧慮,
讓我清醒如海霧,卑微如塵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