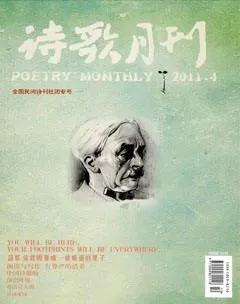張衛(wèi)東(1首)/桑克(1首)/森子(2首)
張衛(wèi)東(1首)
堅(jiān)守,秉燭而歌的櫓聲
她在流動(dòng),在這個(gè)沉寂的夜晚,在我體內(nèi)
每一根搏動(dòng)的血管。
一個(gè)人走進(jìn)來(lái),
為她感動(dòng)。有一個(gè)人為她感動(dòng)就足夠了。
她歌唱,
在內(nèi)心的上方、山野和身旁的大街小巷,
沿著自己的曲調(diào)和流向。
她邊走邊唱。
在某個(gè)路口或岔道,可能會(huì)遇見(jiàn)一些別的河,
別的河可能發(fā)出一些別的聲響。
而彼此的契合或抵觸
是無(wú)關(guān)緊要的。
獨(dú)處的日子,她相信,
惟有寂寞的崩潰才能裝下孤獨(dú)。此刻,
她點(diǎn)起一支燭,把寒冷逼到了夜的深處。
讓歌聲溫暖了起來(lái),
并把暗夜里的流水照亮。
于是,她看見(jiàn)一條小船搖離了河岸,
船上也有燭火點(diǎn)燃。
他閃爍,為著她
為著少數(shù)想象的內(nèi)心;
她照耀,
為了秉燭者凡俗的肉身,他的永恒的靈魂。
我的河就這樣承載著,
兩岸是輕蔑,迎面是風(fēng),背后是櫓聲。
在我初學(xué)上路的時(shí)候,
當(dāng)我決定劃進(jìn)那片葦叢,
那片黑色的時(shí)空——水網(wǎng)中的森林。
一些樹(shù)葉進(jìn)入了視野;
一些花瓣飄了過(guò)來(lái);
還有一些落木,發(fā)出了哀鳴。
青春啊,青春
一開(kāi)始就是結(jié)束,像塵封的歷史
那荒誕的世界,虛無(wú)的人生。
而火在燃燒,
為了與身的歌唱,去燃燒中化為灰燼。
這是自己的真,像一把刀,
斬去了障目的雜草。
櫓聲劃過(guò),一曲終了。
人事不省的船上,
他再次放緩了速度,壓低了嗓音。
陣地(河南,2010年總第10期)
桑克(1首)
雨還在下
雨還在下。我突然有些高興:
它和我有什么關(guān)系?不理它,它就和
死者沒(méi)什么區(qū)別。冷風(fēng)吹進(jìn)來(lái)。
我喜歡它們?yōu)槲医禍兀也辉敢?br/> 表現(xiàn)我的喜歡。我漠然地享受著,
虛偽地享受著。而雨聲果然就聽(tīng)不見(jiàn)了,
卡車(chē)的聲音卻精細(xì)地闖進(jìn)來(lái)。
后輪的氣不多,紋路也有一些模糊。
發(fā)動(dòng)機(jī)的嗓門(mén)倒是大的,只是不夠均勻。
和巴赫的平均律相比,還是粗糙的,
嘈切的。可是,現(xiàn)在的聽(tīng)眾有誰(shuí)這么耐心?
有誰(shuí)守著收音機(jī),聽(tīng)那些已經(jīng)消逝的人聲?
卡彭特是誰(shuí)?我不解釋。風(fēng)也不會(huì)解釋
它在盛夏之夜如何保持涼爽的氣節(jié)。
對(duì)巴赫我是放心的。我不想問(wèn)他
他的里拉琴放在哪里,他的沙槌是否
塞在壁櫥背面的灰色的口袋之中?
我稀里糊涂地,懵懂地在他的勸誘之中,
忘記雨聲的冷餐之宴。我的一個(gè)靈魂
在交叉的花園之中游蕩,有時(shí)掏出手機(jī)
說(shuō)些什么。聲音那么大,仿佛告訴每一扇
敞開(kāi)的窗口,但是他說(shuō)的什么卻沒(méi)有
一個(gè)人能夠聽(tīng)清,連我這個(gè)拜把兄弟也不能。
雨聲出現(xiàn)了,一滴一滴的。剛才這一滴
約有一克重,敲在空調(diào)的外掛機(jī)上。
火車(chē)聲從遠(yuǎn)處走近,仿佛貼在我的耳朵邊上。
我用雙手搓著臉,忘記鼻梁的眼鏡并非
面部的一部分。不是我的,永遠(yuǎn)不是我的。
森子(2首)
湖畔獨(dú)坐
11月7日,與眾友游鳳凰島,離隊(duì)獨(dú)坐得此詩(shī)。
岸——沒(méi)有對(duì)錯(cuò)。
你我,有一個(gè)不在,這不巧合正應(yīng)了
腹動(dòng)的水和水的廣博。
橡葉旋落,有如放生筏,不小心落水的昆蟲(chóng)
劃動(dòng)幾下就到了魚(yú)家。
沒(méi)有對(duì)錯(cuò),只有起伏,坐,躺下,彎腰,駝背,
靜脈曲張,暴跳,幾個(gè)看見(jiàn)
看不見(jiàn)的動(dòng)作。
只有舒緩的鳥(niǎo)語(yǔ)因聽(tīng)不懂而婉約,
此種深刻返哺于寂靜,
不解,誠(chéng)懇的,
正如賣(mài)弄是熱情的。
你邀落葉來(lái)幾支你不會(huì)跳的曲子,
你會(huì)了,
并不是偷師,你只是打開(kāi)身體,關(guān)閉了欲望的
幾個(gè)小閥門(mén),
水就從你的頭頂瀉下,言辭的光斑
在橡樹(shù)間滑落。
難以言說(shuō)的美,菖蒲早于你領(lǐng)會(huì)。
咀嚼青草的甘苦,你理解了自身應(yīng)有的氣息,
不該是群體性的麻痹的油膩,
連自我都嫌棄的腥臭。
這一刻,對(duì)通過(guò)錯(cuò)——現(xiàn)代性的扭結(jié)釋放你,
他終于歸來(lái),你信嗎?
在李商隱墓前
這墓地多少有些心虛,
考究的話語(yǔ)雖分歧,但有村莊
舉泡桐和楊樹(shù)的手臂。
這里即千里,
野花入典,一朵務(wù)虛的浮云
停在麥田的賬表中。
相聚不深,別也淺顯,
電時(shí)代,詩(shī)的交往如噴氣式。
比這更驚心的小浪底,
波峰的每一時(shí)段已被嚴(yán)格監(jiān)控。
我向你虛擬的死拜了拜,
即承認(rèn)情愿是有機(jī)的重復(fù)
和艷體詩(shī)的挪用。
我一直在想,除了書(shū)籍
沒(méi)有更好的封土能安頓詩(shī)人的魂魄,
除非這墓地會(huì)喘氣,
唇齒如兩扇閉開(kāi)的門(mén),你像月影
一般來(lái)去。在商場(chǎng),飯局
或夢(mèng)的新廟宇,剛剛結(jié)識(shí)一個(gè)人,
而我并不能斷定,他是不是
可以做一分鐘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