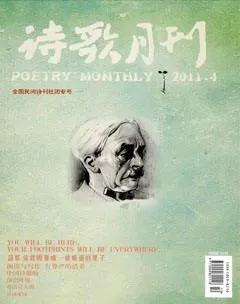陳先發(fā)(1首)/翩然落梅(1首)/邱啟軒(2首)
陳先發(fā)(1首)
殘簡(節(jié)選)
(3)
秋天的斬首行動開始了:
一群無頭的人提燈過江,穿過亂石堆砌的堤岸。
無頭的豈止農(nóng)民?官吏也一樣
他們掀翻了案牘,干血般的印璽滾出袖口。
工人在輸電鐵架上登高,越來越高,到云中就不見了。
初冬時他們會回來,帶著新長出的頭顱,和
大把無法確認的碎骨頭。圍攏在嗞嗞蒸騰的鐵爐旁
搓著雙手,說的全是順從和屈服的話語
(12)
下午,遙遠的電話來自群島,某個有鯊魚
和鵜鶘環(huán)繞的國度。顯然,她的亢奮沒保持好節(jié)奏
夾著印第安土語的調(diào)子,時斷時續(xù)。
在發(fā)抖的微電流中我建議她,去死吧,
死在你哺乳期的母語里,死在你一撇一捺的
卷舌音上。“哦這個”!這個喪失了戒心的下午,
隔著太平洋和無比遲緩的江淮丘陵,
她說她訂婚了。跟一個一百八十磅的土著,
“哦訂婚了”,無非是訂婚了,我猜她的亢奮
有著偽裝的色彩。而偽裝對女人,到底是資源
還是舍不掉的特權?就像小時候,在深夜的田野
她總要把全村唯一的手電筒,攥在自己的手里。
她也問起合肥,而我已倦于作答。我在時光中
練成的遁世術,已遠非她所能理解――
哦此刻,稀有的一刻,我小學的女同學訂婚了。
我該說些什么呢?下午三點鐘,我猜她的腰
有些酸了,玻璃窗外的鯊魚正游回深海
而攪動咖啡的手指,隔著海,正陷于麻木
翩然落梅(1首)
舊照
背景中的白鷺踮起一只腳站在水里
再后面的蘆葦叢 彌漫起十七年的煙靄
那時我喜歡《詩經(jīng)》中的句子,喜歡把蘆葦叫做蒹葭
照片中的我穿著白色百褶裙
眼睛稍微瞇起來。一副不諳世事的模樣。身后的北湖尚未
被夸大政績的官員馴服。野葦漫天
荷葉如蓋。只在最邊上,看到陰森的采血站
很多冤魂進進出出,有的死去了,有的還
活著。隱藏在記憶中的落日之中
給我拍下這張照片的人
忘了是哪個。她拋下相機
上岸走了。岸上還有那么多的人
活著,吃飯,老去。剩下我一個,和白鷺
湖水。死去的蒹葭和冤魂
彼此相安。在方寸之地,一直活下去。
只是一年暗淡一點點。
12號(北京,2010年第3輯)
邱啟軒(2首)
藤草
藤草伸向巖縫中的黑暗與冰冷
緩慢舒展關節(jié)和身體
在窒息的縫隙
在靈魂的痛苦和壓抑中
用指甲扣開巖石之門
用牙齒啃掉黑暗中的恐懼
悶頭不語,最后葉片爛掉
只剩下一根根骨頭似的藤蔓
一直插進石頭的心臟
這些神秘的力量相互纏繞,扭結
在星辰和雨水之外
在遠方蒼鷹悲憤的嘶吼之外
用力緊抱著孤獨,抱著微苦的空氣
像死人抱著生前所有的謊言
這些藤草在疼痛的源頭,隱姓埋名地活著
只有一個死亡是
小酒館幌子迎風飄蕩,門口是家畜的糞便
有人摔破瓷碗,有人大罵或囈語
故去的人撲打著腥臭的翅膀,坐在房頂上
每一個死亡都在此找到它的主人
但是只有一個死亡是具體的,單獨的
有一次,我就看到了這種死亡
當祭祀提著畜生,準備砍下頭
那頭無知的畜生對明晃晃的刀感到好奇
努力伸長了脖子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