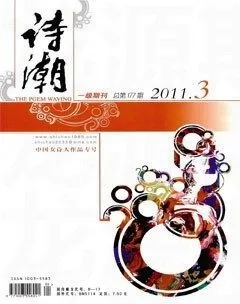采采卷耳(組詩)
朱巧玲:
四川樂山人,出生于1974年,1995年畢業于四川農業大學。現居樂山。已在《詩刊》《星星》《詩選刊》《詩潮》《詩歌月刊》《新京報》等各種報刊發表詩歌六百余首,作品入選十余種年度詩選。
創作談:詩歌是一種非常美妙的文體。它表達上的自由和無拘無束令人著迷,它看似簡單其實深奧,它看似無形其實棱角分明。我想每個人的內心都棲息在詩意之上。如果你去發掘、去研究,你會覺得這世界上真的是一個詩意的世界。你可以用你的語言盡情地描述。我這里“詩意”并不只是優美事物的“詩意”,它也包括對苦難的體驗,對未知世界的恐懼等。
沒有哪一件事物可以像詩歌一樣讓人對生命的洞察如此之深刻和細微。詩人的人格力量和審美取向在詩歌里會得以完美體現,我希望在詩歌里直面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回避或反叛。因為詩歌具備生的喜悅和死的悲憫,所以我最終想要在詩歌里保持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和保持詩歌的藝術品格和品質。
有時候我在想,詩歌寫到現在我已經不在乎它的外形和表象了。它就是我的呼吸,帶著我血液的氣息和我個人的品質。我有理由淺薄地相信我的詩歌和我自己是獨特的,不可重復的。
天亮了
露水搖晃。風走上屋頂
闊葉林又大又美
它們叩擊著我的窗欞
——天快要亮了,像剛出生的
嬰兒,睜著無邪的眼睛
這一天從澄澈開始,又會隨
落日緩緩下沉
在河流的拐彎處,水聲如同天籟
這甘洌的清晨,仿佛神
已降臨
推開窗戶,涼風中的青桂山
靜謐、安詳
光線斜穿過來,影子斑駁
我按捺住內心的喜悅,因為你即將
到來,在這一瞬間
天已經亮了,我所有的秘密
都已成真
銅,或者黎明
銅在消失。聽,它在黎明前發出最后一聲
嘆息。岷江空闊,明月已隨江水
下沉。請埋葬我的體溫,
“滴答”請藏好一滴水,請取走一粒鹽。
天快要亮了,魚群擊出水花
像銅,撞擊出天籟,那些
潔白的骨骼,已荒廢。銅
露出它的銹和傷。這一夜,我聽見
銅老去的聲音,走向敞開的
黎明。
與一棵樹交談
與一棵樹交談,你動用“沙沙”的風聲和正在來臨的雨水
你會剔除準備好的序言和抒情
鳥雀曾在樹上筑巢
又怎樣離去
一棵樹,像一盞燈
它緩慢地行走,我們的鞋子
也放慢了速度
我們用樹木染綠大地,我們把糧食
舉過頭頂
一棵樹,默默地注視著我們
而我們不懂得沉默
有一種鹽,低于塵土
有一種鹽,浮在時間的巖石上
幸福的人早已入睡。鹽,背負著
黃河和唐朝。我看見
它的傷,像黃金一樣,閃亮的東西
有一種鹽,落在仰望的眼。就像有一種
生存,低于塵土,我們活著
把那些饑餓的莊稼,和黃皮膚的人
朗誦成鹽
命運如此安排,我們多么卑微
而鹽,如此美好
翼
——致女兒
陽光照在紫色的盆地,照在樂山城
柏楊路和長青路之間,照在實驗小學
××年級二班,一群小鳥
“嘰嘰”“喳喳”地鬧開了
其中的一只,我把這首詩
獻給她。
她黑色的瞳仁閃啊閃,上面落滿了
不知名的花朵、樹木和昆蟲
風一吹,她就在這堆亂七八糟的事物中
打開翅膀
她有一片領空,在她的足下
她還有一尺平方的小小的領土
聽濤記
去清音閣聽濤聲,你在我身邊
(或者你依然遠在)
我們聽了很久,我們聽到了什么?
我抱著自己的雙臂
沿著黑暗的臺階走回去
人有其土,其鹽,其知,其畏
我們有一段山水時光
我問你這是不是最后一日
我還問有什么勝過宗教
不計其數的人從眼前走過
云煙一般
我們隨人群消失
直到另外一群人涌上來
他們也無法和濤聲吻合
植物的速度
植物是有速度的,當風穿過峽谷
植物開始奔跑
山上的石頭和天上的太陽
跟著它一起奔跑
它要到哪里去?
植物以閃電的速度
從一個省份跑到另一個省份
在甘肅,它比風沙快了一秒
到了吉林,它迎著風雪穿過了
自樺林
進入四川,它靜下心來,與我并肩前進
它朗誦著
它對領土有自己的看法
植物保持著持久的耐力
它不會輕易受到挫折
在夜晚
萬物都進入了夢鄉
植物停了下來,一小片月光
使它靜靜地面對天堂
天就那么空著
流云只藏在我們的心臟。天空
已經空曠
菊花即將來臨,水慢慢結晶
它們不懂得節制。雁鳴
太美
天空被星辰注解
最高的地方,在我們的語言之上
天,就那么空著
像遼闊的祖國,需要用鮮血來填充
像我們自己
被遼闊擊中,又被天空靜靜地
俯視著
采采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置彼周行
——《詩經·周南·謄耳》
用群山、河流和鐵軌衡量我們之間的距離
三千詩句,算不算長?
我相信愛的遼闊一如采采卷耳
覆蓋每一寸肌膚細微的感覺
每當老虎從白雪里躍出
我會獲得釋放,像蒲公英
散落四方
用地理和祖國容納我們之間的落差
每一棵樹木都是升起的太陽
每一只小獸都成為可愛的孩子
走在蒼穹下
是什么在呼喚我的名字?
我相信愛的自由一如采采卷耳
當我抬頭,那些潔白的云朵聚攏而來
擋住了傾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