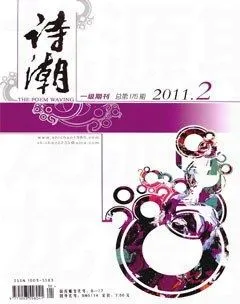對低處的光照
曾經以20OO行長詩《幻河》,抒寫中華民族的苦難史和詩人自己的心靈史,震撼讀者,征服評委,一舉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的馬新朝,于2009年12月出版了一本詩集《低處的光》,從對高大題材的把握轉向對低處存在的光照,顯示了銳意求新的姿態和可貴的探索精神。詩人說得好:“不管自己過去的心靈飛得多高,多狂野,我的身體,我的存在,始終都在低處。低處才是我的靈魂的安居之所。”“人不能太狂妄.虛妄,人要回到大地上,詩也要回到大地上。大地才是所有生命寄存的地方,它是一個實在,是及物。回到大地,就是回到平民和平民意識。回到生命的根部,存在的根部,并愛它們,用詩撫摸它們。”
低處,可以看得具體、細微,不至于浮華、夸飾或理念偏枯;低處,可以寫得直接、即時,不放過當下狀態與任何變化;但低處,也容易瑣碎、隨意、平面、缺少深度。光照的作用,就在這里凸出來了。它是一種聚焦,將日常生活集合在一起,加以比較和分析,作出排列和呈現;它是一種透視,透過表層的具象,深入隱秘和未知的領域,看清那些被潛藏、被遮蔽的部分。馬新朝的本領就在于此,這使他既得益于后現代詩的技巧,又避免了后現代詩的弊端。
《去了一趟作家協會》一詩,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去掉了曾經有過的如“作家的搖籃”、“精神的高地”等光環,還作家協會這個群眾團體以本來的、應有的面目。它和其他群眾團體、其他單位一樣,不在天上,而在地上,都處于市場經濟商品大潮的沖擊中。“還在萎縮”,“受到質疑”,被“使勁地擠壓”,文學遭到邊緣化,這都是不爭的事實,與物欲橫流、精神滑坡、價值失衡的社會傾向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也是詩人憂患意識之所在。
然而,他摒棄了高高在上的道德評價,也摒棄了振振有詞的大聲疾呼,不是俯視,而是平視作家協會的日常生活:遭到世俗社會冷落的“寂靜”,受到“知識無用”、“知識貶值”論威脅的“書摞”,關注“人們普遍的疼痛”、堅持文學創作如蜜蜂釀蜜不止的“老作家”,以及捅陰溝(“下水道”)的“作協秘書長”……讓這一切在透明中呈現出來,竭力捕捉對象的最直接的即時狀態,就像美國詩人金斯伯格所主張的:“必須簡單直接地寫出我們的感覺。假使對事物的確感覺夠強烈,夠真確,寫出來的就會是詩。”
在接受琳子的專訪時,馬新朝說過這樣一段話:“只有具有現代感的詩人,才具有洞穿事物的能力,才具有解除自身枷鎖的能力。”他所謂的“現代感”,就是哲學和感悟,就是他心靈的光。用這種光,他照到了上述的事物與人,看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發現了平常人發現不了可又認同的東西,而且寫得是這樣妙趣橫生:“一個老作家從一本書的扉頁坐起來/打著哈欠問我/幾點了”給人一種“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之感,時代的變化真是太快了!
令人叫絕的,是最后一節:
又要下雨了
作協秘書長從烏黑的下水道里鉆出來
他說這里太擠
連一個座也沒有
不僅受到擠壓,還被冷落、邊緣化,這樣的單位按理是不會有人來了。事實卻恰恰相反,人滿為患,爭搶座位,以至于鬧得下水道不通。這一悖論,不僅幽默,還能引起多種聯想,其內涵是相當深刻的。
詩中還有一節,雖然只有兩行,我們卻不能輕易放過:“有人說,我的老師前些年帶著他的兒女們/回鄉下去了”是一反蜻蜒點水“賓館寫作”的風氣、長期深入基層扎扎實實地體驗生活,還是心灰意冷分流別向改弦更張?都有可能,起碼是給我們提供了文學界的另一種路向……總之,寂靜與喧囂,堅守與困惑,沉潛與浮躁,分流與內斗,構成了作家協會的樣相,這又豈止是一家的樣相,分明是復雜、紛紜、冷暖有別、矛盾交錯的當代社會的縮影!
有人將當代詩分為隱喻寫作與口語寫作兩類,本文不想探討這種分法是否科學,只想說就是按照這種分法也很難界定馬新朝的這首詩。他用的多是口語,這是由其低處決定的。如“高高低低的書摞,像一些逃荒的人”,讓人擔心這些摞在一起的書籍的命運。“那些蜜蜂一樣嗡嗡的漢字”,既是明喻,又是通感(以聽覺代視覺),還有形態,可謂美也。但是,你能說“瘋長的樓群和喧囂”對作家協會的“擠壓”不是一種隱喻嗎?作家協會的秘書長不抓文學創作,而去捅陰溝、通下水道,你難道不覺得這話中有話,充滿了隱喻的暗示性嗎?高標桿的詩人有能力消化各種字、詞,恢復漢語的命名功能;也有能力運用各種寫法,打破教條、門派和類別的界限。
馬新朝還有幾首純粹寫物的短詩,在發揮想象力和運用細節上,像《去了一趟作家協會》一樣精彩,如《草蛉蟲》《一朵南瓜花》《看河》《夜晚,熊耳河幽暗的水》。他說,這均得之于“低處”所賜;我則對他補充道,還有“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