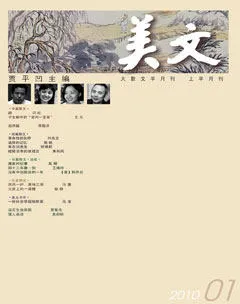比觀念和技術更重要的
何平
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末,現執教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1990年代后期開始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當代文化批評。做規矩的學術論文,也做不規矩的文藝評論和媒體書評。近年在《當代作家評論》《上海文學》等發表文學批評40余篇,曾獲《當代作家評論》獎。
話說東北人高暉“編”了本小冊子《康家村紀事》。說是“編”,不是“寫”,一點沒有鄙薄高暉精神勞動的意思。按我看,他也樂得承認是在“很好玩兒”地“編”,如其所說:“寫這些東西的時候,還沒有規劃,后來——2003年冬天才發現:怎么寫了這些關于童年和康家村的作品,為什么不單獨編出一本呢?今年有了成段兒的時間才開編。”編著編著還上了癮,據說康家村的事“紀”過了后還有兩本康家村“人”與“物”的東西待編。
《康家村紀事》既出,自然由人評頭論足。我留意了林林總總的說道,說得多的是技術。說技術是因為《康家村紀事》片段(1-8)、正文(1-6)、序言、附錄和文本導讀(1-5)這些雜七雜八的東西“編”出來的大框子。其中最醒目的是游走于紀實和虛構,散文和小說之間的“片段”和“正文”。高暉說《康家村紀事》是“關于一個村莊的非結構主義文本”。應該說,高暉是嘗到了“炫技”的甜頭。幾乎所有的專業和非專業的讀者都覺得“此中有真意”。要知道,今天的文學早已是一個“非技術”的“淺”寫“輕”讀的時代。說“技術”,那是先鋒文學好時代的事情。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小說的馬原、蘇童、格非、余華、孫甘露,散文的馮秋子、杜麗、鐘鳴、張銳鋒等等一干人馬。現在去之十數年,想來好遙遠,談起來,大有“白發宮女說前朝舊事”的唏噓不已。《康家村紀事》的“炫技”或是滿足了過來之人憑吊一個逝去的先鋒時代的幻覺。
但我說,《康家村紀事》的好處只是技術嗎?就說技術,以我有限的閱讀,只舉一個例子,《康家村紀事》的這些招數至少納博科夫的《說吧,記憶》都曾經用過。當然這樣說,我并不認為文學的慣例和程式不可以重復使用,相反的是如果高暉挪用這些慣例和程式且卓有成效,也許正證明這些所謂技術層面的慣例和程式也許就是人類面向自己記憶的本能和常態。當我們踏上記憶的返鄉之路,我們所能打撈出的、記錄下來的也許只能是這些“片段”之碎片和“正文”之虛構。如此說來,如果我們將對童年往事的書寫不是處理成對曖昧、幽暗的世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近乎絕望的追索,而是條分縷析、絲絲入扣、沒有迷途也沒有分叉,恰恰是有悖常識的虛假的寫作。《康家村紀事》的技術只不過是尊重文學,甚至是記憶術的常識。在這方面,較之前輩納博科夫所做的,《康家村紀事》“片段”之碎片和“正文”之虛構還不能算“碎”和“虛”得徹底。
不是技術,那是什么?觀念?我也注意到,一些人將高暉的《康家村紀事》和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和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拉的《蒙塔尤》進行比附。比附前者,還算在文學道上向大師致敬。比附后者,如果高暉的《康家村紀事》真的是這樣的一本著作,如果我們認為高暉只是按照自己的觀念在建構一個正史不載村莊“小歷史”,且把這作為高暉寫作意義的全部和結果,那么高暉至多是一個有著田野調查癖好的地方志寫作愛好者。事實上,《康家村紀事》這種只關心“我知道的”和“對我心靈有影響的”,遠不能算稱職的歷史態度。因而,高暉的康家村村史至多只能是一個漏洞百出支離破碎的“一個人的康家村”而已。
是的,寫一城一村一族一家一草民的成長史是近年的一種寫作時尚。而我要說的,當下中國文學的“歷史癖”正在傷害到某些文學本質的東西。批評界對這些作品關注的熱點往往集中在和“宏大歷史”敘述的意識形態對抗。問題是文學的任務僅僅是提供一種不同于國家正史的“小歷史”嗎?必須警惕,“小歷史”的敘述正在日漸成為一種對抗的文學政治學。當代中國文學往往在一些常識性的問題上屢教不改。我認為當下以村莊“小歷史”或者“個人記憶”為視角的文學書寫,動輒就牽扯到對“大歷史”或者“集體記憶”的祛蔽和反抗,正在陷入了另一種形式的“觀念先行”和“政治正確”。而事實上,從新世紀中國的文學現實看,誰在壓抑?誰在反抗?已經是一個新的問題。即使存在所謂的對抗性書寫,除了持政治異見的文學書寫依然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對抗性,文學的壓抑和反抗也更多應該從這些非文學領域回到文學自身,回到審美慣例和審美創造之間的對抗性書寫。所以,對于這些寫“小歷史”文學如果我們還只是將其全部意義設定在歷史的真偽之辨上,顯然是一個背離文學常識的偽命題。而且寫小歷史、生態史、生活史、文化史、底層史以及庶民日常生活也并不必然保證通向的就是文學之路。必須意識到:歷史如何被敘述和歷史如何被文學敘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因而必須重新回過頭來研究這些作品,看看其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小歷史”和“個人記憶”書寫的文學性。也就是如果不從意識形態對抗的角度,這些“個人記憶”或者“小歷史”書寫有沒有自足的文學意義。
文學不只是一種“史余”一類的歷史下腳料,但我不否認“個人記憶”可以獲得一種見證意義,特別在我們這個習慣遺忘的國度。2009年臺灣天下文化出版了齊邦媛的回憶錄《巨流河》,且用了一個詞“記憶文學”。可以順便說說《巨流河》,這本書大陸的三聯書店最近出了刪節版。《巨流河》無論是寫作者自己,還是書中涉及到的政治人物、知名文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都有相當的公眾認知度。在一個名人隱私成為大眾文化消費品的時代,《巨流河》在大眾傳媒的渲染下肯定會引起普通讀者的關注。但我認為《巨流河》引起關注的深層原因,特別是被知識界關注,首先是因為它對何為歷史,歷史如何被敘述,個人記憶如何在宏大的歷史敘述中獲得意義等問題所作的思考這些“非文學”因素。布塔利亞·烏瓦什在其《沉默的另一面》說:“詹姆斯·揚格在寫到大屠殺的回憶和證言時,曾指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不通過大屠殺得以流傳下來的那許多方式,我們怎么可能對它有所了解呢?他的回答是建議我們不僅通過‘歷史’了解大屠殺,而且還要通過它的文學的、虛構的、歷史的、政治的描述,通過它的個人的、證明性的陳述來了解它,因為對任何事件來說,重要的不僅是‘事實’,同樣重要的還有人們如何回憶這些事實以及如何陳述它們。……”中國近現代史是“家”與“國”纏繞的,但在我們的敘述中常常卻是“國史”淹沒“家史”。我們說歷史是誰創造的時候往往會說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但事實上人民群眾參與的歷史創造在宏大的歷史敘述中卻是沉默不語的。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但人民群眾卻很難參與到歷史的敘述,就像有學者指出的:“對真正的印度歷史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