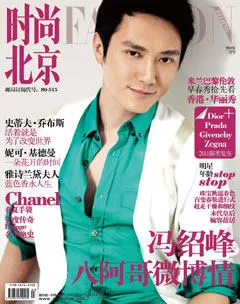凌健 順其自然當了畫家
蒼白的肌膚、消瘦的身體、精致的短發、閃閃發光的珠寶、紅唇吸吮著的櫻桃,畫中女子充滿期待誘惑的凝望……這位藝術家想告訴我們什么,我想若你定要思考出一些意義或價值來,那上帝該發笑了,任憑你去想象吧。
曾經窮途陌路的藝術家
大概藝術家都應該是從窮困潦倒到一夜成名,似乎這樣更符合對藝術界的邏輯,我也無一例外地走了個過場,深知其中艱辛。我是86年大學畢業后出的國,當時年輕氣盛不愿意服從分配,總想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還記得那時出國的情景,父親極力反對,他是一名新四軍老兵,本身對兒子選擇藝術道路就很不理解,更別說背井離鄉去歐洲,而我很清楚自己選擇的道路,當時就想就算沒錢睡著大橋底下我也要堅持畫畫。
曾有人問凌健:“哪怕貧困潦倒,窮途末路,您還能信仰藝術嗎?”也有人問,“你在22歲剛到歐洲的時候就已經覺得自己是藝術家了嗎?”他的回答都是毫不遲疑的“是”。自信,是他認為成為藝術家的必需。這份自信支撐他走到了現在。不管是乘公交車沒有足夠的錢而走在漫長的上班路上,還是在餐館打工時因拒絕剪掉藝術家標志的長發辭職,連著幾天餓肚子;抑或是為了生存不得不暫時放棄創作,身邊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個個和藝術漸行漸遠時,他身體里的那個聲音也從未消失:“一定要畫畫”。
“大概我只能畫畫了”
“人一生總有一份職業適合自己,很多人在藝術道路上因為艱難而選擇離開,我也有一氣之下把畫筆扔出去說算了再也不干了的時候,但最終還是放不了手,第二天早晨起來再把畫筆撿回來接著畫。我大概只能畫畫了。”他笑說:“最享受的生活就是深夜一個人在畫室聽著喜歡的音樂,畫著畫。拿起我的畫筆時心里突然就開始平靜,不拿筆的時候反而有點緊張。”
凌健在維也納待了三年時間,然后開始了他的歐洲游歷,“就這樣三到四年間我什么也沒做。后來我開始做一些行為藝術。當時的過程是尋找自我的一種獨立性的東西,跑了很多小的劇場、小的畫廊。做了一段時間又重新回到繪畫上,那差不多是92年、93年,從那時候到現在一直在做繪畫。”
被拋在空中的海歸
八十年代西方人不認為中國有現代藝術,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國外的藝術圈也只能游蕩在文化圈的邊緣,而凌健回國之后發現很多東西都跟當時走的時候不一樣了,中國的藝術也在發展而且非常迅速,而他們在很多東西上都脫節了,對事物的一些看法也不一樣了。“就像我的作品中《身份》里一樣,我們的身份很尷尬,回到中國后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懸在空中。中國的策展人也不會找我們,因為我們在國外,他們認為我們代表不了中國的當代藝術;國外的策展人也不會找我們,因為你也代表不了中國的藝術,所以我們就被仍在空中,不東不西,不左不右。”
具象的繪畫讓我更充實
“起初中國的八十年代是不讓畫抽象畫的,抽象畫代表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