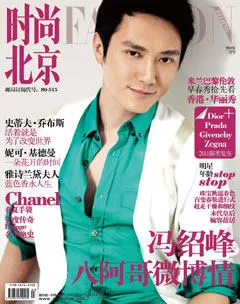不得不知的時尚攝影大師
“知識分子熱衷于討論攝影的意義,于是攝影師按下快門的手越來越猶疑,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可能導致攝影兩極分化,到最后只剩下兩種人:新聞攝影師和哲學家。”
如果你自稱時尚攝影師或者時尚攝影的愛好者,但卻不知道紐頓的名字,那顯然是一種缺憾。紐頓以美國和歐洲為舞臺,在《Vogue》、《皇后(Queen)》、《NOVA》、《ELLE》、《花花公子》等時尚雜志發表自己的作品,給人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同時也成為上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時尚攝影師之一。他的時裝攝影作品大膽加入了裸體、政治以及性的元素,在時尚攝影界引起了一場認識革命。
紈绔子弟
德國富裕猶太家庭出生的紐頓從小就被送入昂貴的美國學校,但他的學業糟糕,卻經常逃課去給兩個美國攝影記者打下手。16歲時的紐頓已經對攝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母親也終于同意安排他跟一個柏林著名女攝影家做學徒。
好景不長,上世紀30年代末德國納粹主義盛行,反猶太風日益高漲,不到20歲的紐頓離開雙親,獨子登上了開往天津的輪船。行李箱中除了相機之外,剩下的都是他漂亮的衣服。雖然納粹只允許猶太人攜帶5美元現金,但紐頓的母親給了他足夠的輪船代用卷,輪船上,他不斷的和已婚女性調情,這是他憑攝影成名前最后一段風光的日子。
被女富人包養
當輪船駛進新加坡時,一個為新加坡挑選可用人才的委員會登船,紐頓因為會攝影并懂得英語而被委員會挑中,留在了新加坡為一家報社工作,這是紐頓人生中第一次靠攝影為生。但不久后,他便因為攝影技術實在欠佳而被辭退。有一段時間,他每天都坐在碼頭,對著歐洲過來的輪船哭到天黑。
但年輕的紐頓長的帥氣,他被委員會一位30歲法國女性看中,成為情人。此段時間實際是被這位闊太太包養,無事可做的持續了2年之久,使得紐頓感覺忍無可忍。直至新加坡政局變動,留在新加坡的猶太人要被送入澳大利亞集中營,紐頓便義無反顧的走入了猶太集中營生活。
戰后事業騰飛
二戰結束后紐頓自己創立了工作室,以便完成他之前的夢想——成為一名《vogue》的攝影師。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紐頓引起了澳大利亞版《vogue》的注意,開始與之合作,并籍此回到歐洲,為英國版《vogue》工作。但歐洲的人才太多,紐頓發現自己甚至不如一名實習攝影師受歡迎。過幾年,他終于發現,一名好的時尚攝影師只有在巴黎或紐約才能成功,那是上世紀60年代,紐頓的事業在這個時候開始起飛。
在自傳中,紐頓覺得這是他經歷過的一個最偉大的年代,時尚攝影變得富有創造性,攝影師的地位和待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半裸的保姆
紐頓的第一場記憶是在他4歲的一個夜晚,他的保姆半裸著身子坐在鏡子前化妝,他也難忘7歲時哥哥把站在街角的柏林最紅妓女指給他看。裸體的女人、夜,這些記憶在日后構成了他攝影作品的一種風格,他非常成功的一組時裝攝影作品就是讓模特扮成妓女站在夜晚的街道上。
柏林墻剛建起來的時候,紐頓帶著一個模特去拍照,他讓模特裝扮成蘇聯間諜站在墻頭瞭望,卻沒有注意到墻角一個小小的十字架,那是為紀念一個被東德士兵擊斃的東德青年——他不過是想翻過墻到西德來。這組照片給《vogue》雜志引來國際性政治丑聞。德國所有的廣告客戶拿掉了下半年預定的廣告,那個模特再也沒能在德國找到工作,而雜志主編卻對他沒有任何微辭,紐頓從這些事中學習到做人的道理。
現實的鏡子
紐頓在眾多時尚攝影師中脫穎而出并被人們紀念,自有他的道理。他工作起來很愛動腦筋,總是隨身攜帶一個筆記本,把隨時想到的想法記在上面。60年代末世界風云突變,也反映在紐頓的照片中,他的時裝照片中,模特躺在窗戶下面,窗外是正在飛過的戰斗機和導彈;他有時候從日報上尋找拍攝靈感,看了費里尼的《甜蜜的生活》,知道在意大利有種職業叫狗仔隊(當然現在他們遍布世界各地了),就找來一幫狗仔隊成員圍著他的模特拍照,而他把穿著當季新衣的模特和這種場景用他的鏡頭記錄下來。
紐頓的心臟不好,從小就有愛暈倒的毛病,家人對此都習以為常,紐頓吃飯時掉到桌子底下,過一會兒就看他自己爬起來了。1971年在紐約街頭拍照的時候,他暈倒過一次,沒能很快爬起來,被送到了醫院,倒下的時候,還有意地做了一個保護相機的動作。
2004年紐頓駕駛車從好萊塢酒店出發,在高速路上因車失去控制從車上摔出。車禍發生后,紐頓立刻被送往救護中心,但隨后去世,享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