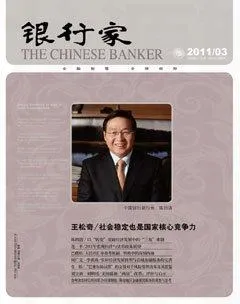新春漫筆——說說春節\\春運\\禁放和春晚
春節
春節變得越來越無趣。
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的重要節日都是宗教信仰的產物,唯獨中國人的春節例外。形成中國人春節文化的基石是傳統的家族文化,這可以從春節時最重要的儀式——合家團圓、吃餃子、守夜、大年初一相互拜年——看出。而有點宗教意味的活動——祭灶、到寺廟許愿燒香拜佛,卻僅僅被安排在居于次要地位的節前和節后的時間段,且這樣的活動也是“信仰者”為了自身的眼前實利而以類似欺騙神靈的手法自欺欺人,如上供時要用糖瓜把灶王爺的嘴抹甜一點,等等。
卻看圣誕節、古爾邦節,它們流傳了上千年,可有類似我們民族節日這樣的劇烈變化么?人家的節日是所有人的精神回合到一起,而我們過年,則是各有各的過法,各有各的內容。
一個民族的節日,如果不與這個民族的宗教信仰相結合,就會被生活中的流俗所左右,變來變去,誰也不知道它會成為什么樣子。不少年長者對80后、90后熱衷于過“洋節”頗有微詞,依我看,那是趨勢,誰讓我們的節日徒有形式、內容干癟甚至沒有內容?
我歷來對過年這個習俗不很看重,因為它太“俗”。我認為,在以往中國有能力拒絕西方文化入侵的時候,這個習俗還有存在的價值,它是農人社會的文化產物,寄托著農人們的期望。它興盛于舊的傳統社會,因而它能服務舊的傳統文化。現在,社會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它早就不適合當代了。之所以這幾年它又為中國人所倚重,我以為這只是暫時的現象,不會持續太久。
在過去的60年,春節受政治運動的沖擊,幾次興衰起伏,尤其是文革期間,在“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名義下,幾乎把它當成“四舊”給廢除了。近來30年,雖然貌似找回了往昔的盛況,但我仍然只把它看作是一個“回光返照”的過程,在中國社會形態劇烈變化的今天,這個習俗正經歷著最后的“輝煌”。我預言:再過二三十年,中國人的“年味”肯定淡漠于今天,而五六十年以后,又會更淡漠幾成,依照這樣的趨勢,它必將逐步走向式微,而根本原因是它已經不是寄予中國人夢想的宿主。這樣說會招來那些民粹主義者的“板磚”,但我為什么還要堅持這樣說?——現在這個時期的中國,將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莫過于中國人身份的轉變,這是兩千年來中國人向現代社會“進化”過程中最具歷史意義的事件——原來占總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向著準公民身份轉變。這個過程雖然已經進行了30年,但由于人口基數太大,到現在也僅僅進行了不到一半的一半。也就是說,從總體上看,僅僅不到一半的農人剛剛把自己的身份轉變了不到公民的一半,或者說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農人大體上實現了向現代社會中準公民角色的轉變,還有四分之一的農人(農民工)正在轉變的過程中。
春運
“春運”近年來越來越讓人感到無奈。“春運”是現在最具“春節”特色的“節目”,所有人都受到它的影響。
對農民工整體來講,他們正承受著這場文化蛻變帶給他們的巨大痛苦,這就是產生所謂“春運”背后的原因——那些已經生活在城市里的新市民,他們已經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城市已經離不開他們了,但是一到春節,他們就不得不自我轉化為農民的身份,回歸鄉村。他們不愿意這樣做,但是沒轍,城市現在還沒有那么寬闊的“胸懷”接納他們,城市只給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沉重的擔子和僅僅可以容身的“蝸居”,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拒絕接納他們農民家庭的其他成員——父母和大部分子女。他們是很可同情、很值得關心的群體。而在美國,同樣身份的人會找政府要面包、要工作崗位,要不到的話,就會上街“鬧事”,而中國的農民工卻是自己找工作。盡管他們干的活很累,有的還很臟,也沒有充分的勞動保護,報酬還很低,但他們都會默默地承受。
每到春節臨近,他們就成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流”,就這樣在中原大地、大江南北現身了。春運是民族之痛,沒有經歷春運的人難以感受到春運之苦,春運已經是現在中國春節最富有代表意義的活動,是我們社會劇烈變革的一個集中體現。盡管人們都不知道這樣大規模的“春運”將在哪一年結束,但它肯定只是一個過程,如果有誰以為春運將永遠這樣持續下去,就太沒有歷史的眼光了。
現在,大城市如果沒有了這數量龐大的“農民工”,便沒法運轉了,本來已經對春節有些淡漠的城市人不得不把春節的檔次予以提升——由原來的三天假變成了“小長假”。
作為對策,有不少“資深”的市民(我這里說的是在城市里居住三代以上的城市人)已經把春節改為游歷歐美澳的旅游節。七八天過來,這過的還是傳統意義上的春節嗎?
禁放
說到春節,總有一個沒有結論的爭論,那就是“禁放”。
每逢春節,僅僅是北京,總有多人,其中不少是青少年,因為燃放鞭炮受傷,有的手指被截去,有的被破了相,而最為嚴重的是被摘除眼球。我常常想,如果是我,因為這種無聊的活動而失去了一只眼睛,我將會多么后悔和痛苦,要知道,這樣的痛苦將伴隨一個人的終生。但是,年年有這樣的悲劇發生,年年有這樣的后繼者替補上來,所謂“前仆后繼”。而今年更有北京的報章說,僅僅根據北京的醫療單位報告,就有兩個人因為燃放鞭炮而失去了生命、一個人被摘除眼球。聊以寬慰的是,摘除眼球的數量是歷年來最少的,希望明年再減少一個。
我們的政府曾有過禁放的考慮,為什么又改變了主意?我分析,一個是沒有頂住這個陋習所代表的勢力的壓力,另一個大概就是GDP發生了作用,畢竟這也是政府稅收的一個進項,再有就是可能政府在“討好”,希望能制造一種親民的氣氛。
這燃放煙花爆竹還有可能造成火災。2009年中央電視臺的大火和2011年東北第一高的首家白金五星級酒店——沈陽皇朝萬鑫酒店——的大火,都是因為燃放煙花爆竹不慎引發的。我總想,那外在的一種危險的活動,怎么就一定能把這些人的內心郁悶發泄出來呢?難道一個理性的人就沒有其他方式取代這樣一種可能危害他人、一定不利環境的陋習嗎?
四十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一個農村作坊制作傳統鞭炮的工藝流程。那時,由于科技手段“落后”,做出來的鞭炮,數量小、威力小、價格相對昂貴,人們的環境意識差,小孩子放幾個小鞭炮,不會造成像今天這么大威力鞭炮的破壞力,但即使這樣,也是沒有比有好。那時制造鞭炮的主要成分是“一硝二硫磺三木炭”,即用一份芒硝、兩份硫磺,再把三份的木炭碾成粉末,混在一起,制成所謂的黑色火藥,這是從宋朝開始就使用的配方,爆炸力有限。而現在,那些鞭炮制造商不會像當初那樣,到房前屋后的墻角旮旯去搜集因為土壤鹽堿化而泛上來的芒硝了,直接就購買開礦用的黃色炸藥充填體積越來越大的鞭炮,那么對燃放者、旁觀者和路過的人必然就會有更大的危險了。
現在都在吵嚷減少“碳排放”,這每年一度的大規模燃放鞭炮,會不會用去我們國家的“碳指標”,進而影響我們正常的工業生產呢?——我不知道該去問誰。
關于“禁放”還是堅持“解禁”,年年都會引發一場爭論。大部分學者是理性的代表,當然認為應當恢復“禁放”。但也有例外,一位明叫“秋風”的學者站在“解禁派”一方,他說:“一種慣例,一種習俗,如果它已經存在了數百年,被人們普遍地遵守,那么它的存在權利就是無可置疑的。”
這怎能是一個學者說出來的話?我們漢民族的女人從小就纏足的慣例或習俗可存在了上千年了,是不是更有存在或者恢復的必要?
說的只管說,干的照樣干,不知怎樣才能恢復對燃放煙花爆竹的禁令。只是從公開的信息看,今年僅僅北京就有三百多起火災是因為燃放而發生,又有數十人因為燃放煙花爆竹而受傷,應當讓這些當事人成為審議這項法令聽政會的參與者才對。春節已經過去,我只能放個馬后炮:失去的就讓他失去吧,沒有辦法,但愿來年沒有人再因為燃放煙花爆竹而失去手指或眼球。
春晚
春晚這幾年變得越來越低俗、越來越無聊了。
但是,這個中國人的節日現在已經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國人的眼球。不少中國記者很為此感到自豪,說什么“春晚中國人必看,外國人愛看”。我不看春晚已有幾個年頭了。偶爾看到一個趙本山耍貧嘴的節目——《賣拐》,這樣低俗的東西,后來知道是上了春晚的,不知道挑選這節目的導演是什么樣的美學欣賞水平?
春晚之紅火,是因為現在的春節實在沒什么意思。干什么好呢?不少家庭在團聚以后也沒有多少話說,老兩口、小兩口之間除了問候以外,問的多了也不合適,那就守在電視前看節目吧。這就正中中央電視臺那些編導們的下懷,于是,這最吸引中國人眼球的時間段就成了他們最佳的搖錢樹。
同時發春晚財的還有那些因為上了春晚以后而一夜成名的暴發戶,他們給那些也幻想成為富翁、富婆的人趟出了一條路。騙子們看到了這里的行情,于是就有自稱是“春晚編導團”的人借機騙財騙色。按照“潛規則”,上春晚光有錢不行,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行。一個春晚,央視能收到多少廣告費、贊助費和其他名目的紅包?它們又是怎樣被再分配出去的?——現行制度是保護這些“國家機密”的,怕的是節外生枝的事情多了而影響安定團結。
春晚已經變成我們民族的一個文化招牌。但是這么大民族的文化招牌卻無法與一個小小民族——奧地利——的新年音樂會相比。人家那些留下來的音像檔案,一百年以后拿出來也不過時,讓人欣賞起來總是常看常新,不會讓后人臉紅。而我們那些像“二人轉”一樣的低俗節目能讓我們的后人引以為豪嗎?我懷疑。我不是想讓那些低俗藝人下崗沒飯吃,他們應當在“劉老根大舞臺”那樣的場合演出,還要向社會打出“少兒不宜”的提醒。春晚這么大的一個舞臺,提供給那些就會耍娘娘腔的藝人們,實在是糟踐了中國人的時間,讓“三俗”擠掉了傳播高雅文化的好時機。
唉!就這樣的春晚,真真地讓中國人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