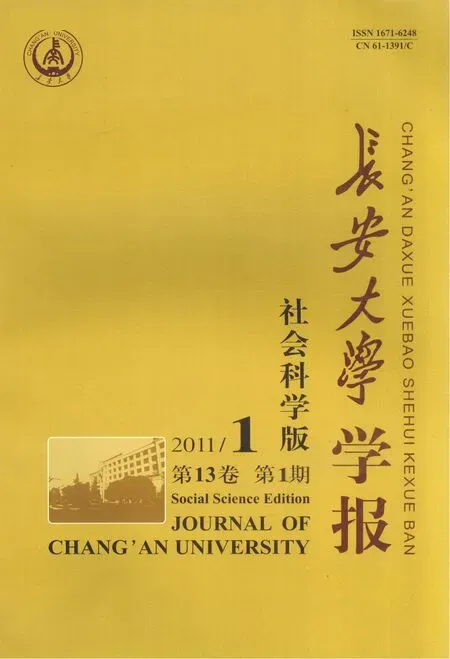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
——以《新語》半月刊為核心的史料考辨
韓 晗
(武漢大學文學院,武漢 湖北 430000)
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
——以《新語》半月刊為核心的史料考辨
韓 晗
(武漢大學文學院,武漢 湖北 430000)
運用文獻分析法,分析《新語》半月刊的創刊原因、辦刊方式與歷史價值,進而探析抗戰后知識分子對于政治、國家的態度。分析認為,《新語》半月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國家意識,并對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新語》;國家意識;知識分子;文學敘事
由傅雷、周煦良創辦的半月刊《新語》是20世紀40年代頗有研究價值的一份社會刊物。從時間上看,創刊于1945年10月1日、持續5期的《新語》本身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解讀性(當時正值抗戰方畢,國共談判又破裂,《新語》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創刊,可以說是當時知識分子在特定時期內的心理狀態投射);從內容上看,該刊的撰稿陣容不可謂不強大,除了主編傅雷、周煦良之外,郭紹虞、錢鐘書、楊絳、夏丏尊、王辛笛、馬敘倫、黃宗江與孫大雨等名家,均為該刊的撰稿人。
但是,就是這樣一份刊物甚少被研究界所關注,甚至在對該刊期數的表述上還存在著矛盾。傅國涌曾撰文稱“1945年冬天,他(傅雷,引者注)曾與朋友創辦綜合性的《新語》半月刊,一共辦了8期”[1],然而《深圳商報》、《新華月報》等報刊紛紛轉載,結果是以訛傳訛。而根據筆者在萬方、CNKI等論文檢索系統查詢情況來看,有關《新語》的專題論文一篇未見,僅有近10篇關于傅雷的學術論文提到了該刊名。
這樣一份頗為重要的刊物實在不應該“被遺忘”,因為從《新語》所刊載的文章以及其辦刊方式、存在意義來看,對該刊進行研究有助于對抗戰結束后國內知識分子的國家意識進行探討,其使用的政治話語有著較強的分析價值。筆者重讀《新語》半月刊這一珍稀史料入手,力圖從歷史地位、文本內涵與社會影響的三重視角追尋該刊的研究價值。
一、學者、知識分子與國家意識
“綜合性學術文藝半月刊”是《新語》的自我定位。這個定位意味著辦刊者的導向:綜合、學術與文藝的結合。這樣的結合在中國現代期刊史上并不算多泛。實際上“三合一”的多元化集中性在本質上不難看透,《新語》力圖完成一種多層級的責任,即社會、學術與文學。但是從倫理上講,上述三者是無法達到統一的,因為社會批評的公信度、學術研究的求真務實與文學創作的美學追求本身指涉3種不同的范疇。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語》本身陷入了一個無法解決的悖論。
恰恰是這種悖論,透視了1945年前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國家觀。因為《新語》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產物,而是有著其文化歷史語境。在《新語》創刊號里有一篇未曾署名的“發刊旨趣”,全文照錄如下:“暴風雨過去了,瘡痍滿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復的河山等著建設。飽經憂患之際,我們謹以這本小小的刊物獻給復興的隊伍。自身的力量雖然微弱,但八年來我們認識了不少幽潛韜晦的同志,始終不懈地在艱苦困苦中努力于本位的工作。編者謹以本刊的園地,請他們把長年窮搜冥索的結果,陸續公諸社會,也許對建國大業不無裨益。凡對本刊不吝指導、批評、扶掖的人士,我們預致深切的謝意。”
這個百余字的“發刊旨趣”,若是仔細分析,定然會有頗為有趣的見解。首先是開篇的開場白,“暴風雨過去了”——這份刊物的時效性可見一斑,而且甚至要高于當時的政論刊物;其次,“光復的河山”與“建國大業”等措辭證明:《新語》絕對不是一份左翼期刊,更不是一份陷入黨派紛爭的期刊,而是一份從“國家意識”入手的時評期刊,因為就在該刊創刊前不久,中共領袖毛澤東與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重慶舉行了和談,并于當年10月10日簽署了《雙十協定》,這是一件讓當時國內知識分子非常興奮的大事。可以這樣說,《新語》是在“抗戰勝利、國共和談”的背景下創刊的。這個特定時期,國內創辦的刊物并不算太多,因此這是解讀該刊的一個較為重要的突破口——在“綜合”、“文藝”與“學術”三者之間,作為該刊意圖執行的功能當是名稱較為隱諱的“綜合”,即政治性的代言,而“文藝”與“學術”無非是充實其“綜合”功能的指代罷了。

表1 《新語》刊發的文章題目及其分類
筆者之所以借表1羅列其發表的文章,乃是因為后文依然會用到這張表格,而且僅憑所羅列的3項內容分類來看,5期累計文章總發表量為76篇,占到總發表量的67.11%,無疑為絕大多數。就“綜合”一項來看,涉及面之廣博(國際關系、地緣政治、中國內政、教育問題等時局問題均為其報道范圍),實在無愧創刊者所言之“綜合”,如此全面且獨到,堪稱當時時評之翹楚。當然,我們若是再回到“發刊旨趣”中應亦可窺得端倪:這份刊物的撰稿者應為“幽潛韜晦的同志”,主要內容則是“長年窮搜冥索的結果”,目的在于“對建國大業不無裨益”。
問題提出很容易,若是深思則會發現這其中之問題——傅雷與周煦良并非熱衷于政治之人,該刊的主要撰稿者也并非羅隆基、張東蓀或劉王立明等政論高手,而是如夏丏尊、周煦良(曾用筆名賀若璧,實際上為其原名)、馬敘倫與王伯祥等純粹的文學專家,他們基本上是以傅雷為核心的知識分子團體。在這樣頗為純粹的學者中,能夠產生出這樣強烈的“國家意識”,并使得他們對政治時局感興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值得認真反思的問題。那么,“國家意識”究竟在他們的意識以及敘事中是如何生成的呢?
從政論的文稿可以看出,這類文字決非是“長年窮搜冥索的結果”。如果說《新語》的學術論文是多年累積的研究心得,這是可以服眾的,而占總發稿量絕大多數的政論稿件,絕非是“長年窮搜冥索的結果”,因為這些政論的撰稿者都不是政治活動家,也不是在抗戰期間興辦政論期刊的報刊人,而是在英美文學、古典文學界有著較高造詣且都遠離政治的學者。
弗朗西斯·福山曾如是厘清“知識分子”與“學者”的本質區別:雖然兩者都善于運用理性,但前者注重公共領域的理性,使其成為意見的生成者;而后者注重學術領域的理性,扮演的是知識的生成者。兩者轉換的可能便是自身權力(包含話語權力、學術權力、政治權力)的更迭。用中國的傳統語言來說,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知識分子),窮則獨善其身(學者)”,“達”與“窮”便是一個權力更迭、轉換的關系。
在這樣的理論下,對于《新語》作者群的分析也就有了新的含義。前文所述的問題便很容易轉換為:這些學者是如何(為何)轉換為知識分子的?
在周煦良的《歐洲往哪里去?》中有這樣一段:“難道歷史永遠要重演嗎?難道歷史如馬克斯主義者所述,只是盲目經濟里的推動?難道經濟力永遠沒法加以人為的控制?難道人類永遠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我們要問。誰是戰爭的犯罪者?今日舉世的目光都射在,舉世的手指都指向納粹主義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身上。日本還可以說,它原是戰前五強之一。德國是戰敗國,怎么會有作戰能力。如果在慕尼黑會議時,德國軍備已超越別國使張伯倫不得不讓步,那么希特勒吞并奧地利時,怎么不注意到?納粹軍進占萊茵時,怎么不注意到?是誰容忍德國有逃避國際眼光的秘密軍火庫?是誰直接、間接扶掖了納粹政權在德國的抬頭?是誰默許了一個有神經質、有犯罪傾向的獨身漢向德國人民號令一切?歐洲政治家這么多年管的什么事?”
如此義正詞嚴的斥責加反詰,很難讓人想到是那個內斂溫和、謹慎小心的英美文學專家周煦良。當然,周煦良還有一篇名為《內戰中我們應有的認識和行動》文章,在這里不妨對比一看:“自從毛澤東先生自重慶飛返延安之后,我們就一直懷著鬼胎,覺得他莫要一去不返。現在這鬼胎不幸而證實:國共兩黨經過兩個月長時期的會談,除掉成立一些表面的妥協外,對國是并沒有達到具體結果,終于各自行動,而以兵刃相見了。這表示人民的愿望已無足重輕,我們這些人等于遺棄掉;還有什么話說!”
兩相對比一看,意圖不言自明。周煦良的不同心志在本質上反映了當時大部分學者的聲音,他們渴望以一種積極的姿態進入到“建國大業”的洪流當中,甚至以一種普世價值、人道主義的胸懷參與國際事務。連年的戰爭、禁錮的政治,使得他們壓抑的太久,知識分子骨子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心態,結合歐美民主、人權的理念,使得他們對于和平的等待變成了對于實現自我機遇的期盼。在日寇投降、國共合作的1945年10月,這種期盼是很容易催化為激情的,但是一旦內戰爆發,他們就很容易繼續陷入低沉,書桌又成為了他們的最后陣地,這也是《新語》停刊的直接原因。
本項目通過應用BIM技術提高了信息化管理水平,在施工過程中實現了“四節一環保”的預期目的,且已順利通過住建部綠色施工科技示范工程的中期檢查。
值得關注的是,由于傅雷、周煦良的留歐背景,導致了該刊所呈現的“自由主義”傾向,這也是該刊不得不停刊的根本原因。作為二戰之后席卷中國甚至世界的自由主義思潮①1944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所頒布的國情咨文中提到了“四個自由”,遂構成了“當代自由主義”的精神淵藪,時稱“美國第二個《權利法案》”。1946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國“雙十國慶日”發表了自己的政治演說(羅夢冊等,《讓我們來促成一個新的革命運動》,《新自由》,1946年第1卷,第4期),使得代表美國政治意識形態(即“普世價值”)的當代自由主義在戰后中國形成了較大的政治影響。,對于中國知識界尤其是當時的期刊界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抗戰結束前后國內雖然沒有太多的期刊、雜志創刊,但是就在這少數期刊中多半是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的刊物,如上海的《觀察》、《時與文》,南京的《世紀評論》以及北京的《新自由》等等。在自由主義思潮下,思想界遂開始爭論“中國在戰后應該建立怎樣一種社會文化秩序”[2]這一主要問題。《新語》也積極地介入了關于自由主義的宣傳當中,譬如要求廢止書報檢查制度,對“國民的意義”的呼吁等等,使其成為了具備自由主義傾向的刊物。
而且,自由主義所主張“論政而不從政”的參政主張以及在政治上對于個人主義、理性主義、非暴力的漸進、寬容、民主由于自由的推崇,在文化上要求新聞、學術與教育三大領域走向自由的呼吁,因而既與國民政府當時所推行的“以黨代政”、“黨化教育”的政策發生著嚴重的意識形態沖突,也與中國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反帝國主義思潮有著強烈的抵觸,遂引起了國民政府當局與中國共產黨、左翼政治黨派的雙重批判,宣傳自由主義理念的《新語》雜志日子自然也不會好過了。
單從歷史地位上講,對《新語》的解讀確實有助于對當時學者轉向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激情心態的重新認識。短暫的和平假象使得他們都暫時放棄了自己的主業,投身到“建國大業”之中。而對于這種心態的解讀,實際上也是對于現代知識分子面對政治、面對社會變革時的意識的解讀——在他們看來,黨派之爭是低于國家、人民利益的,這也是秉承“自由主義”英美派知識分子共同的政治觀。
二、政治話語中的文學敘事倫理
政論一直是中國近現代期刊的重要文體,但是目前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始終未曾將政論列入其中,這也就是為何“新月派沒有羅隆基”[3]的原因之一。
公允地說,《新語》雜志雖然以政論為主,但其撰稿者并非是政客或政治理論研究者,而是當時非常重要的翻譯家、作家與文學學者,其文筆的流暢程度、敘事技巧的純熟與多樣化,使得《新語》所刊發的政論有了一定的文學價值。
若只是從文藝、學術角度來窺探《新語》的文學性,那么可研究性的范疇是極其有限的。但是從時評來看,作為政論的文學敘事頗具新意和文學性。除卻上述周煦良的論著之外,其余的時評文章讀起來也頗為有趣,一改當時報章的時評風格,使得政治話語呈現出被文學敘事所表達的征兆。圖1是《新語》刊登的時評,其中有簡陋修改過的痕跡。
前蘇聯語言學家米·赫拉普欽科認為,文學敘事語言的特征是通過以下基本功能所表現出來的,一是“與日常生活語言區分開來”,此為文學語言的“交際功能”,另一個是“文章意境中詞匯會有‘含義增加’的情況”,這是文學語言的“審美功能”。這2種功能為文學敘事語言所特有,也是有別于其他敘事語言的特點[4]。在《新語》所刊發的時評中,卻充分體現了文學語言的特點,其與日常生活話語是截然不同的語言系統,以及其所使用詞匯的“含義增加”,使得時評性的政治話語開始有了文學敘事語言的特征。
譬如傅雷(署名迻山)的《所謂人道》一文,便是一篇文筆曉暢、具有散文韻味和文學價值的時評,這是一次政治話語與文學敘事頗為完美的結合:“假使殺人行為的應否譴責,當以被害者人數多寡而定,那么多寡的標準如何?傷五命十命的兇手,該處以怎樣不同的死刑?假使殺傷非戰斗員才是戰時人道主義的起點,那末,從古以來,有一次或大或小的戰爭不曾傷及過貧民?這一次的戰爭先后已歷八年,血流成河,尸橫遍野,還不足以形容它的慘酷,正義之士為何緘口不言?”

圖1 《新語》刊登的時評
若論質疑之語氣,當不如之前周煦良的語氣來得猛烈,但是傅雷激動起來的“雷火靈魂”、“江聲浩蕩”并不比周煦良溫柔絲毫,拋卻行文的感性因素不談,僅從該文的敘事方式來看,兩段以“假使”開頭的自然段,不但邏輯嚴密,而且有著特有的文學敘事風格,2個以條件關系開頭的從句引出4個環環相扣的系列性質問,從而深入到問題的本質之中。這樣不放空炮、有著文學敘事式的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的時評創作中頗為少見,因為當時英美派政論家已經不太熱衷于“魯式雜文”的創作,而是試圖讓政論恢復到自然與理性,學術化的政論無形削弱了其應具備的文學性。
在《新語》第三期中還有一篇《糙米運動》的時評,作者秉志是中國近代生物學的奠基人,曾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除了科學家的身份之外,曾經考中晚清舉人的他還是一位頗有影響的散文家。在《糙米運動》里,有這樣一段文字:“原夫米之本身,乃一重要食品。其淡紅色之外層,為乙種維生素之所在,最富于營養價值,特國人喜求精白,養成習慣,務將此層磨去,以求美觀而適目。新米登場,農民碾去其硬皮;此時所謂糙米者,乃營養之珍品也,而必須經磨房一番研磨,嶄然潔白,以求所謂“大米”者,社會始愛嗜之,此時米粒所具營養之美質,所謂乙種維生素者,已完全失去。本身所存者,大部分為淀粉。其他為營養所需之各質,幾等于零。國人窮年累月生活于淀粉中。其體力之發育,尚能望其健全乎?”
按常理說來,如此遣詞造句出現在政論文字中幾乎不可想象,從其內涵看當是科技說明文無疑,若從其結構看又是一篇頗有文學審美價值的駢體散文。其措句之典雅,結構之全面,用語之含蓄,修辭之優美,有理有據,一問一答,篇末點題更洞見作者古文功底,這決非當時滿腔激情一般性的政治話語所能踐行。
像這樣以文學敘事倫理來實現政治話語的篇章,在《新語》作者群中并不罕見。與《新月》、《觀察》等刊物的時評作者群不同,《新語》的作者都不是專業的社會活動家與政治時評家,他們都沒有政治學的專業背景,而且之前基本也沒有時評的寫作經驗,他們都是一流的文學家與翻譯家,是特定時代下知識分子的國家意識與責任心促使他們以滿腔的熱血為墨,并以“業余時評家”的姿態出現在20世紀40年代中國的時評界。這讓他們的文字或多或少地缺乏了專業的政治學知識,也未必有強大的號召力。縱觀這50余篇時評,更多的是書生氣的文學性,然而這一特點并不是缺點而是同時代其他時評恰恰不具備的文學敘事倫理。恰恰是這一點,《新語》的時評作者群亦是當時最為杰出、最有特點的時評作者隊伍。
三、政治、文學與知識分子
《新語》從創刊至休刊僅僅數月,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為風云突變的幾個月,也是大轉折的幾個月。如果說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是20世紀30年代意識形態主潮的話,那么“革命壓倒救亡”就是20世紀40年代后期的意識形態主潮。
這里所說的“革命壓倒救亡”并非是革命取代了救亡。在這里,“革命”是一種代表黨派之爭,即誰的槍桿子硬、誰得民心,誰便可以問鼎中原的“權威主義”,而“救亡”是一種喚醒全民族意識,并且為“建國大業”而形成共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主義”,兩者的側重點雖然都是關于政權的意義認同及其重構,但是前者側重于一種內部權力場的解構,使得權力被重新分配,而后者側重于一種外部權力場的爭奪,使得權力被重新獲得。
從“救亡”到“革命”的急轉突變,非但周煦良不習慣,發出了自己被“遺棄掉”的怨詞,而且一批知識分子都對中國的前途產生了懷疑。尤其是一些費邊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學者始終認為,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國共兩黨正好可以如英美等國一樣及早實現多黨制①如張東蓀、羅隆基等人都贊同這個觀點,羅隆基甚至還希望更多的黨派參政議政。。
周煦良的《戰后英國政治瞻望》就是一篇表露出自己政治想法的論文,認為英國龐大的工商業“尾大不掉”,可以考慮實現“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又不是慈善事業”,于是只好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之間折中,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曾一度在“第三黨”中流傳,在當時知識分子中影響深遠;而林子政的《刺刀與教育》分析了戰勝國如何對待其他弱國“革命運動”的關系,認同于戰勝國的刺刀實際上是為了害怕別國的“革命”蔓延而打著“保護”的旗號,這對于當時的中蘇關系、美日關系無疑有著現實性意義的。
知識分子參政、議政并對國家前途各抒己見,是《新語》的最大特點,除卻寥寥幾篇純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政治主題幾乎貫穿了該刊所有文章。《新語》雖然存在時間極短,但是有著值得深究的社會影響,筆者在這里權且拋磚引玉,留待諸方家賜教。筆者以為,《新語》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大概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對當時的學者起到了一定的鼓動作用,為他們從“學者”向“知識分子”的轉化在一定意義上起到了催化作用,并且為學者參政探索了一條路徑。《新語》的最大特點就是學者云集,除卻以文學學者為主體的作者群之外,還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生物學家秉志,這對于當時的學者應該有著積極的意義。因為傳統的職業時評家與學者本身從屬不同陣營,兩者較少產生接觸。畢竟《新語》在當時的影響力已然無法考證,但是我們唯一可以知曉的是該刊是當時唯一一本由純學者在特定時期創刊的時評刊物,雖然他們還拿出藝術、文學為遮羞布并將時評更名為“綜合”,但是這并不能掩蓋他們從江湖走向廟堂的天然理想。至少,《新語》為學者參政探索出一條路徑,雖然這是一次并不徹底的失敗,我們并不能把該刊的停辦歸結于學者們對于時局的失望,畢竟《新語》第三期還刊登了“漲價啟事”,因為該刊面對當時飛漲的物價已經難以為繼,甚至不得不靠增加廣告(第一期1個廣告,第四期4個廣告)來平衡開支。從學者向知識分子過渡,無法進入政壇核心,只好利用大眾傳媒以及自己對于時局的看法,形成公共性的觀點,這是現代中國學者向知識分子變遷的范式。《新語》是這種范式的最好實現方式。自我話語、公共話語與政治話語的三重轉換,從而實現知識分子迫切參政的理想,但是在專制的政體下,這其實是一種徒勞。
第二,《新語》生成了一種新的、介于文學與政治之間的話語機制。文學與政治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兩者話語機制的關系長期以來被認同為“文學從屬政治”或是“文學與政治無關”,兩者如何尋找到突破口?同為意識形態,文學可以和哲學、歷史、經濟、宗教等等不同的話語機制發生關系,惟獨在政治面前無法理直氣壯?從更廣闊的歷史維度與意識形態角度來看,《新語》的意義正在于此,如何從政治話語的角度來實現文學的敘事倫理?作為時評的政治話語,是應該從政治本身出發還是應該從文學敘事倫理來切入,正如前文所述,《新語》已經給了我們頗為詳盡的答案。
四、結 語
“一切政治都是把戲,唯獨文學不是,但是它可以在知識分子的帶動下參與這把戲,并且成為整場把戲的魔術師。”海登·懷特如是解構政治、文學與知識分子三者之間的微妙關系,如果我們投以更遠的視野,那么這句話仿佛也可以用來闡釋《新語》的社會影響以及在今天它帶給我們的全新啟示。
[1] 傅國涌.傅雷的另一面[N].大河報,2005-01-12(5).
[2] 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3] 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4] 米·赫拉普欽科.作家的創作個性和文學的發展[M].佚 名,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National consciousness,literature narrative and scholar's suffrage——study of historical data and literature value for the semimonthlymagazineXinyu
HAN H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00,Hubei,China)
This paper,based on documental analysis method,evaluates the reasons of magazine's beginning,management style and the historical values for the semimonthlymagazineX inyufrom the views of the modes in whichintellectuals considered to be national and political.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gazine manifested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intellectuals to a certain extent,and that the magazine influenced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in a large degree.
X inyu;national consciousness;intellectual;literature narrative
G219.29
A
1671-6248(2011)01-0073-06
2010-10-15
韓 晗(1985-),男,湖北黃石人,文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