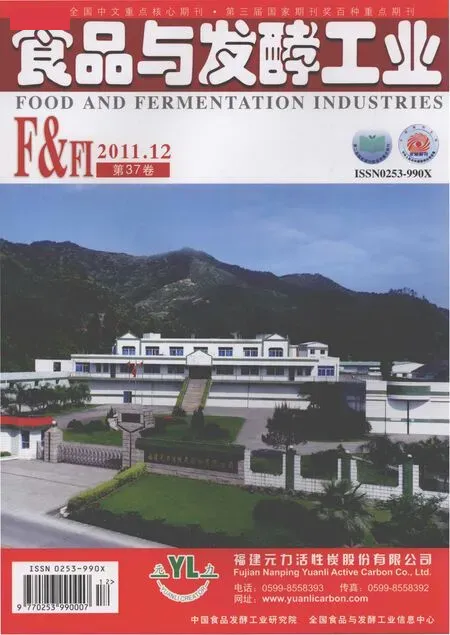“紫娟”綠茶發酵過程中茶褐素理化性質及微生物變化*
譚超,龔加順,保麗萍
(云南農業大學食品科學技術學院,云南昆明,650201)
普洱茶是中國歷史名茶,是云南最具特色的名茶,距今已有1 700多年歷史[1]。普洱茶通過潮水固態發酵,蒸壓成型,沖泡湯色紅濃明亮,香氣獨特陳香,滋味醇厚回甘。茶葉中的色素化合物包括存在于鮮茶葉中的天然色素以及加工過程中形成的色素。這些色素是茶葉色澤、湯色及葉底色澤的基礎[2]。普洱茶茶色素屬于天然色素,是從普洱茶中提取的一類水溶性酚性色素,包括茶黃素(TF)、茶紅素(TR)、茶褐素(TB)。而茶褐素系非透析性高聚物,主要組分是多酚類、多糖、蛋白質和核酸等。非透析性多酚含量會隨茶湯發熱而增加[3]。傳統普洱茶發酵過程中,因水熱的作用會促使茶黃素和茶紅素含量減少,而茶褐素含量增加。一般普洱茶中茶褐素含量為4% ~9%[4]。
“紫娟”茶屬于茶樹變種 (C.var.assamica),是云南大葉群體茶樹品種中的一種特異品種,具有紫莖、紫葉、紫芽的特征,含較高的花青素。關于它的基本化學組成,特別是茶褐素目前的研究鮮見報道。在“紫娟”普洱茶發酵過程中,微生物如何變化,對茶褐素、茶紅素等主體色素物質形成有何影響等研究報道極少。本課題以“紫娟”曬青綠茶為原料,通過茶葉適度潮水后固態發酵,制成“紫娟”普洱茶。通過分析在不同發酵時間段,其中主要微生物含量變化和茶褐素的基本組成、理化性質,闡明微生物與“紫娟”茶褐素形成的關系,明確“紫娟”茶褐素的理化性質與光譜學性質。為進一步研究“紫娟”普洱茶茶褐素與普通普洱茶茶褐素的差異奠定基礎。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與試劑
“紫娟”茶曬青綠茶(云南省茶葉研究所)。試劑:無水乙醇、乙酸乙酯、正丁醇、氯仿、葡聚糖(分子量10 000)、硫酸、蒽酮、考馬斯亮藍、硫酸亞鐵、酒石酸鉀鈉、磷酸氫二鈉、磷酸二氫鉀,所有試劑均為分析純。
1.2 儀器與設備
101-3ABS恒溫恒濕發酵箱,寧波東南儀器有限公司制造;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日本島津UV1700;紅外光譜儀,BIO-RAD FTS–40;氨基酸自動分析儀,Hitachi L-8900;等離子體發射光譜儀,島津ICPS-7510;BCD-208K冰箱,青島海爾。
1.3 試驗方法
1.3.1 “紫娟”普洱茶發酵
以“紫娟”曬青綠茶為原料(10 kg),潮蒸餾水至茶葉含水量30%,靜止3 h讓水分充分被茶葉吸收,隨后將潮水后的“紫娟”茶原料放入45℃,相對濕度75%的恒溫恒濕發酵箱中發酵。發酵5 d取樣作為一翻樣;發酵10 d取樣作為二翻樣;發酵20 d取樣作為三翻樣;發酵30d取樣作為四翻樣。同時,分析各翻堆樣的微生物以及理化性質。
1.3.2 茶褐素的提取流程
將茶樣加入70%乙醇溶液中浸泡4 h(去除醇溶性色素),將浸泡后的茶渣再用85℃熱水浸泡2 h,過濾后取濾液并濃縮。濃縮液逐次用乙酸乙酯、氯仿、正丁醇萃取,剩余水層加入無水乙醇至80%,沉淀茶褐素,收集沉淀,冷凍干燥。茶褐素含量分析方法參照文獻[5-6]。
1.3.3 茶褐素理化性質的研究
(1)微生物分析:菌落總數測定參照 GB/T 4789.2-2008。霉菌與酵母菌檢測計數與菌落總數測定相似。樣品稀釋液的制備:稱取茶樣10.00 g于250 mL錐形瓶并加入90 mL無菌水,置于靜音振蕩器上振蕩20 min,此液為1×10-1g/mL濃度的茶樣懸浮液,用無菌紗布在超凈臺上過濾并吸取1 mL的濾液于預先裝好9 mL無菌水的(18×18)mm的試管中,此液為1×10-2的茶樣稀釋液。以此類推,制成 1 ×10-3、1 × 10-4、1 ×10-5、1 ×10-6、1 × 10-7g/mL等一系列稀釋濃度液,供平板接種用。本試驗分離霉菌、酵母采用 10-4、10-5、10-6三個稀釋度;菌落采用10-2、10-3、10-4三個稀釋度。接種:將樣品稀釋液用1 mL的無菌吸管吸取1 mL放入到配制好、已滅菌的相應培養基中,用接種刷把樣品液抹勻,放到(28±1)℃下培養4~5 d即可觀察鑒定及計數。每個樣品采用3個稀釋度,每個稀釋度采取3重復。微生物的分離計數:采用混合平板計數法。同一稀釋度各處理重復的菌落相差不能太大,霉菌以每皿10~100為宜,酵母、細菌以每皿30~300為宜。計算結果時,常按從接種后的3個稀釋度,選擇一個合適的稀釋度,計算出每毫升菌劑中的含菌量。計數公式:每毫升樣品的菌數=同一稀釋度幾次重復的菌落平均數×稀釋倍數。
(2)多糖含量的測定[7]:蒽酮-硫酸法,以葡聚糖(分子質量10 000)為標準品。
(3)蛋白質含量的測定[7]:考馬斯亮藍法,牛血清白蛋白作標準蛋白。
(4)茶色素含量的測定[7]:萃取比色法。
(5)茶褐素總酸性基團、總羥基、總羧基的測定[8]:茶褐素和氫氧化鋇反應生成茶褐素的鋇鹽,用過量的標準酸中和氫氧化鋇,然后用標準的氫氧化鈉溶液回滴過量的酸測定總酸性基團。茶褐素與醋酸鈣反應生成茶褐素鈣和醋酸,然后用標準氫氧化鈉溶液滴定生成的醋酸,測定羧基。紅外光譜分析表明,茶褐素中的酸性基團主要是羧基和酚羥基。因此,只要測出總酸性基團的含量減去羧基含量即為酚羥基含量。
(6)氨基酸含量分析:采用酸水解法,利用氨基酸自動分析儀測定樣品中水解氨基酸含量。取100 mg樣品于水解管內,加入15 mL濃度為6 mol/L的HCl,抽真空并封管,置于(110±1)℃恒溫干燥箱內,水解22 h后,將管內水解液過濾,取1 mL干燥并用1 mL pH 2.2的檸檬酸鈉緩沖液溶解,供儀器測定用。
(7)礦物質元素分析:等離子體發射光譜儀。
1.3.4 茶褐素光譜學性質分析
(1)樣品的UV-vis分析:將“紫娟”茶褐素配成溶液,于190~1 100 nm波長范圍內掃描。
(2)IR分析:將“紫娟”茶褐素經KBr壓片,于紅外光譜上掃描分析,掃描范圍500~4 000 cm-1,分辨率為8 cm-1,掃描次數為16。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葉中的茶褐素含量變化
茶褐素系指一類能溶于水而不溶于乙酸乙酯、正丁醇和乙醇等有機溶劑的褐色色素。在普洱茶加工過程中,茶褐素的含量,對茶的品質形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9]。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葉中茶褐素含量結果見表1。由表1可看出,在發酵的前20天,樣品中的茶褐素含量隨發酵時間的延長而不斷增加,第三翻樣品中的茶褐素含量達到最高(18.36%),第四翻樣茶褐素含量又減少。這可能與微生物的變化密切相關,微生物數量在第三翻達到最高,而后數量急劇減少(見表2)。

表1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中茶褐素含量變化

表2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中微生物含量
劉勤晉等研究表明,普洱茶渥堆過程中黑曲霉(Asp.niger)生長最為旺盛,其次是青霉、根霉和酵母[10]。通過對普洱茶發酵過程中的氧化酶(多酚氧化酶、過氧化物酶、抗壞血酸氧化酶)的活性進行檢測,發現在發酵過程中有強烈的多酚氧化酶和抗壞血酸氧化酶的活性。此前,我們對接種外源優勢菌酵母菌發酵普洱茶過程中各種酶活性的結果變化顯示[11],發酵10d后多酚氧化酶和纖維素酶活性達最高,分別從原料中的9.29 u/g和0.377u/g增加到34.2u/g和1.27 u/g;發酵20 d后,糖化酶活性由原料的8.23 u/mL增加到58.42 u/mL;發酵30d后,淀粉酶活性由原料的164.28 u/g增加到239.19 u/g;發酵40 d后,果膠酶活性由原料的0.08 u/mL增加到2.8 u/mL,過氧化氫酶活性由原料的5.6 u/mL增加到58.9 u/mL。
由此可見,在普洱茶發酵過程中,生物分泌的多種酶協同作用于茶葉,使茶葉內含成分與酶分子間以及成分與成分間的相互接觸,特別是多酚氧化酶(PPO)酶促作用更為激烈,從而促進了普洱茶品質特征的形成,特別是茶褐素的大量形成。
2.2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褐素中的多糖、蛋白質、茶色素及酸性基團含量變化
“紫娟”茶褐素在發酵過程中多糖、蛋白質、茶色素等組成會隨發酵時間延長而變化,從表3可以得出,隨著發酵時間的延長,茶褐素中的多糖、蛋白質不斷增加,但到第四翻時,含量有一些下降,這可能是與微生物有很大關系,因為這一階段的微生物減少了很多,從而影響了多糖、蛋白質的含量。不同茶樣提取的茶褐素中的茶色素含量也有明顯變化,從整體變化趨勢看,茶黃素和茶紅素的含量是隨著發酵時間的延長而不斷地減少的,茶褐素的含量則不斷地增加。然而,茶黃素和茶紅素的減少量并不等于茶褐素的增加量,均小于茶褐素的增加量。這種量的差別可能顯示茶褐素的形成并不只是通過茶黃素和茶紅素轉化而來,還可能有多糖、蛋白質的參與。活性基團總羥基及總羧基的變化復雜,僅總羧基的變化與微生物、茶褐素的變化規律一致,這顯示普洱茶的發酵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化學變化過程。

表3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褐素中多糖、蛋白質、茶色素及酸性基團含量
2.3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褐素中主要氨基酸含量
從表4得出,單體氨基酸如天門冬氨酸、谷氨酸、胱氨酸的含量隨著發酵時間的延長,含量不斷減少;而蘇氨酸、絲氨酸、甘氨酸、丙氨酸、纈氨酸、蛋氨酸、異亮氨酸、亮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脯氨酸以及水解氨基酸總量等均隨著發酵時間的延長,含量不斷增加。賴氨酸、組氨酸、精氨酸這3種氨基酸的含量先是不斷增加,發酵10d后含量達到最高,而后逐漸下降。單體氨基酸含量的變化反映了與茶褐素結合的蛋白質隨發酵時間也在變化。

表4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褐素中主要氨基酸的含量

續表4
2.4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褐素的礦物質含量
測定茶褐素中礦物質元素的含量,可反映茶褐素結合基團的變化,特別是羧基、羥基的變化。由表5可知,隨發酵時間的延長,“紫娟”茶褐素中礦物質元素的含量呈下降趨勢。硫、磷、鉀、鎂、鋅、錳元素的含量,總趨勢是隨發酵時間延長而下降,而鈣、鐵、銅元素的含量,總趨勢是隨發酵時間延長,先逐漸減小,到發酵30d時(第四翻)又逐漸增加。鉀元素的含量最高。對比檢測發現,普洱茶速溶茶粉中鉀元素的含量可達7%。這些礦物質元素的變化可能與微生物的滋生、繁殖有密切的關系。

表5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褐素中礦物質含量/(mg/kg)
2.5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褐素UV-vis性質
不同發酵時間的“紫娟”茶褐素樣品在280 nm左右處均有一個吸收峰,此處是蛋白質和核酸的最大吸收峰。因此,不論經過多長時間的發酵,“紫娟”普洱茶提取的茶褐素中都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質和核酸。樣品在200 nm左右有最大吸收峰,有研究表明,植物多糖糖苷的最大吸收峰在200nm左右,說明在茶湯中可能含有小分子糖形成的糖苷或多糖復合產物存在。

圖2 不同發酵時間“紫娟”茶褐素的UV-vis
2.6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褐素IR性質
由圖3得出,“紫娟”普洱茶不同發酵階段茶褐素提取物的紅外光譜圖差異不大;茶褐素提取物在3 410 cm-1處的強寬吸收峰為 O—H伸縮振動;在3 600~3 000 cm-1范圍內出現的寬峰還可能包含N—H伸縮振動;2 929 cm-1處為亞甲基的C-H伸縮振動峰,1 626 cm-1處為C=O的伸縮振動峰,結合1 531 cm-1處的吸收峰可以判斷該處可能還含有芳環骨架振動引起的吸收,1 409 cm-1處為COO-的對稱伸縮振動峰;1 313 cm-1處為芳香族的C—N伸縮振動峰,1 242 cm-1處為酚的 C—O的伸縮振動峰,1 098、1 050 cm-1兩處為 C—O—C的伸縮振動峰,787、701 cm-1兩處為苯環的C—H面外曲振動。“紫娟”茶褐素為多羥基酚類物質,并含有羧基,結合有蛋白質和多糖,更確切的基團情況尚需進一步做其他的相關分析來確定。

圖3 不同發酵階段“紫娟”茶褐素紅外光譜圖
3 討論
微生物在普洱茶的發酵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2-13]。測定不同發酵階段(不同翻堆)樣“紫娟”普洱茶的微生物指標,從表2可以得出,樣品中的菌落總數、霉菌、酵母菌數量隨著發酵的時間的延長,呈上升趨勢。在“紫娟”原樣中,含有一些本身就攜帶的微生物,這對不接種任何微生物,只是控制發酵溫度和濕度的普洱茶發酵過程是非常有利的。這些微生物在恒溫恒濕的條件下迅速滋生、繁殖,表現出來的就是一翻樣中的微生物數量都增長了很多。隨著發酵時間的延長,微生物的數量繼續增多,在三翻,即發酵20d的時候達到微生物數量的最高點,隨后,微生物的數量急劇的減少,這可能是因為隨著發酵到達一定的時期,普洱茶中能供給這些微生物生長繁殖的營養物質差不多耗盡,微生物的數量就會減少很多。
“紫娟”普洱茶在發酵前后變化明顯,從掃描電鏡圖片(圖4)可以看出。茶原樣中微生物含量較少,而四翻中則存在大量微生物。發酵前,茶葉表面比較完整光滑,細胞結構、纖維素、木質素等沒有被破壞。而曬青綠茶經發酵后,茶葉表面長滿微生物,并且茶葉結構已經被破壞。兩組電鏡圖的直觀對比,說明微生物一方面生長需要碳源,同時,又可分泌一些酶將茶葉細胞結構破壞,組成成分纖維素、半纖維素、原果膠等物質被降解。可見微生物在普洱茶發酵中起了重要作用。

圖4 “紫娟”茶葉一翻樣和四翻樣掃描電鏡圖(“紫娟”原樣(a);“紫娟”四翻樣(b))
“紫娟”普洱茶中的成分在發酵的中后期呈現明顯的增減變化。關于微生物的變化。何國藩、林月禪、徐福祥等人[14]的研究表明,渥堆早期霉菌最先發展起來,酵母菌早渥堆開始幾天數量甚少,到中后期大量發展起來,成了優勢菌種。這是因為霉菌能利用各種多糖作為碳源,代謝的結果產生了大量的雙糖和單糖,使酵母有了足夠的營養。普洱茶以曬青毛茶作為原料,經發水、渥堆陳化及干燥工序精制而成的后發酵茶。渥堆陳化實際上是在酶促作用、濕熱作用和微生物的作用下共同完成的,但微生物起最主要的作用。試驗中發現茶褐素中含有多糖和蛋白質。要對茶褐素的化學結構作進一步的分析,就需要將茶褐素進行分離純化,才能得到更加準確的分析結果,而如何將茶褐素分離純化,在以后的研究中是重點需要攻克的地方。
4 結論
(1)“紫娟”茶葉中菌落總數、霉菌、酵母菌數量以及茶褐素提取量變化隨發酵時間的延長呈現先增后降的變化;茶褐素組成中的多糖、蛋白質殘基等含量不斷增加,茶色素含量、總羥基及總羧基的含量變化明顯,天門冬氨酸、谷氨酸等含量不斷減少;而蘇氨酸、絲氨酸等含量不斷增加。賴氨酸、組氨酸、精氨酸的含量先增加后下降。礦物質元素硫、磷、鉀、鎂、鋅、錳元素的含量下降,鈣、鐵、銅元素的含量先逐漸減小后逐漸增加。
(2)UV-vis表明,不同發酵時間“紫娟”茶褐素在200nm處有一個最大吸收峰,280nm左右有一個特征吸收峰。IR表明,“紫娟”普洱茶茶褐素為多羥基酚類物質,并含有羧基,結合有蛋白質、多糖。
(3)霉菌和酵母菌對“紫娟”茶褐素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影響了茶褐素的理化性質,特別是化學組成。
[1] 周紅杰.云南普洱茶[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
[2] 王漢生.茶葉色香味的化學基礎[J].廣東茶葉,2005(1):39-41.
[3] 陳宗道.茶葉化學工程學[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4] 洪德臣,范兆義,李楠.茶色素及其化學成分[J].現代診斷與治療,1995(6):32-33.
[5] Edwin H.Thoughts on theatubigins[J].Phytochemistry,2003,64(1):61-73.
[6] 安徽農學院.茶葉生物化學[M].2版.北京:農業出版社,1994.
[7] 黃意歡.茶學實驗技術[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
[8] 李建武.生物化學試驗原理和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9] 易戀,黃建安,劉仲華.普洱茶多酚與茶褐素研究進展[J].中國食物與營養,2009(12):29-31.
[10] 劉勤晉.普洱茶之科學讀本[M].廣州:廣東旅游出版社,2005.
[11] 朱春華.云南普洱茶加工和貯藏過程中酶活性及成分變化研究[D].昆明:云南農業大學,2008.
[12] 趙龍飛,周紅杰.云南普洱茶渥堆過程中的主要微生物初探[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5,21(2):129-133.
[13] 趙龍飛,徐亞軍,周紅杰.黑曲霉在云南普洱茶發酵過程中生長特性的研究[J].食品研究與開發,2007,28(10):1-3.
[14] 何國藩.廣東普洱茶渥堆過程中咖啡堿和茶多酚含量變化及飲效[J].中國茶葉,1986(5):8-9.